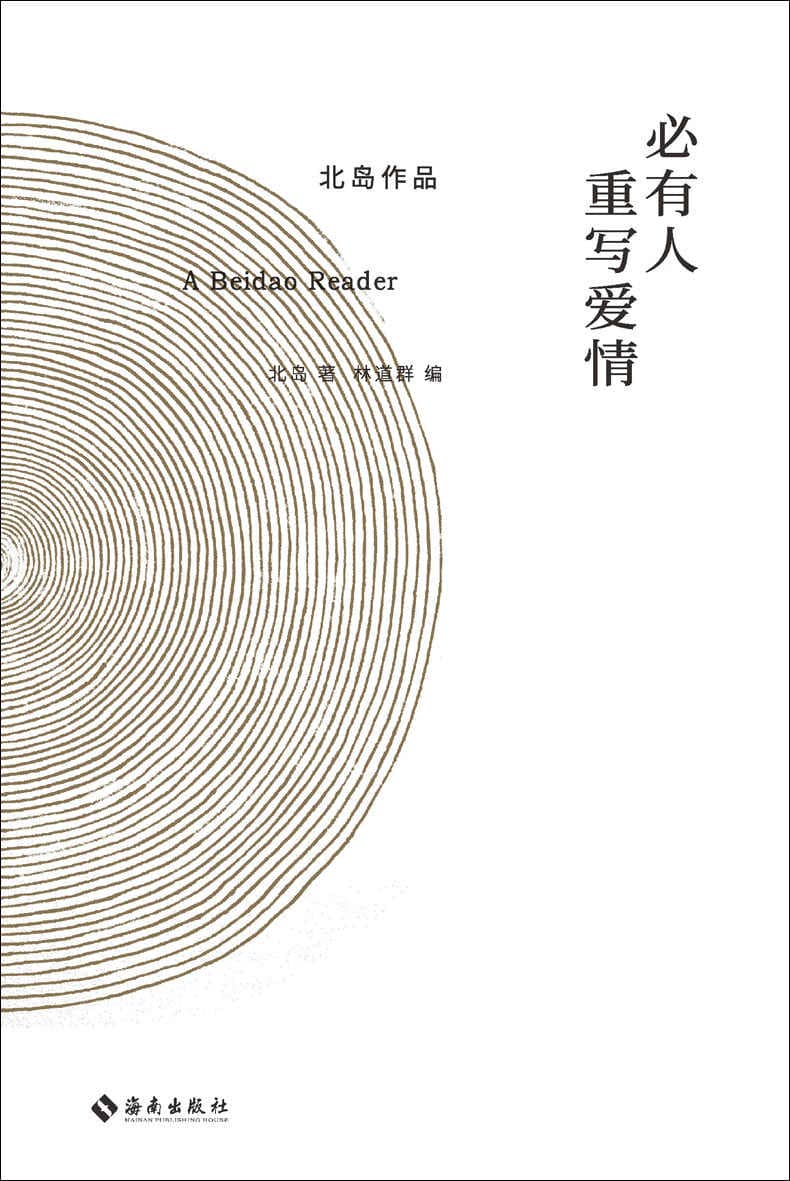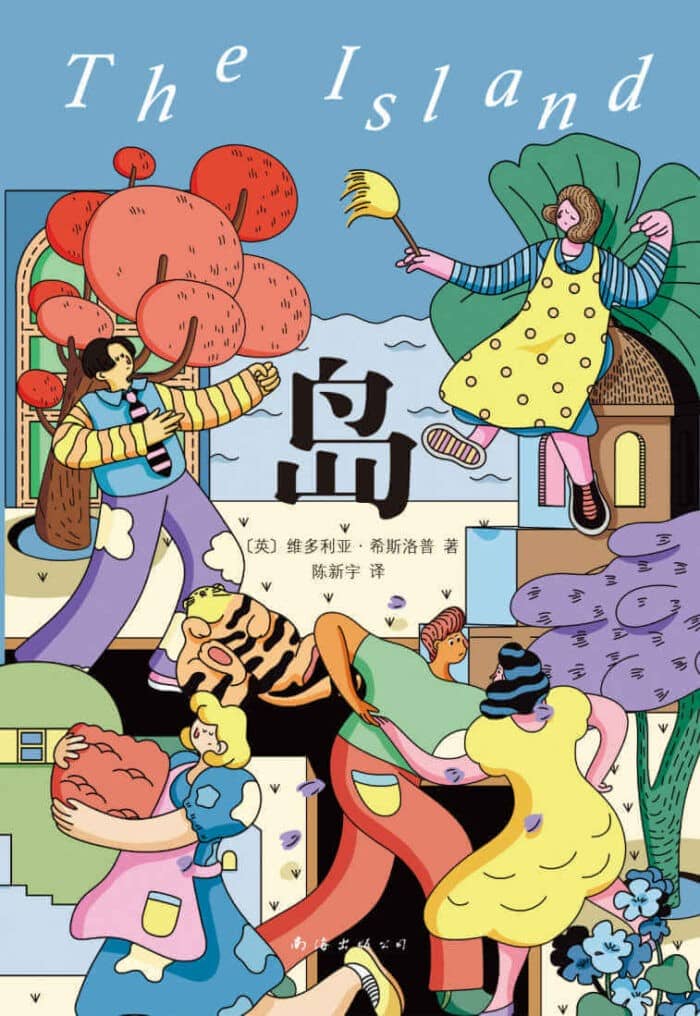内容简介:
“瞭望员马克洛尔”的史诗人生,七部曲组成的英雄传奇。
★我们都是马克洛尔。——马尔克斯
★马克洛尔是我已成为、未成为和未坦白的一切。是我想成为、应成为但不曾成为的一切。马克洛尔是我的一个写照:是我的荣耀。——阿尔瓦罗·穆蒂斯
他是没有身份的人,从未在世上有过真正的居所;
他是瞭望员,在桅杆上,在飞鸟中,面对浩瀚而绝对的孤独;
他并非喜欢历险,却总在厄运中前行;
他和人交往,无论朋友、情人,不谈承诺,也没有亏欠;
他很少与人对质,相信命运会给他们教训;
他身上总是带着书,从阅读中把握生命现实的一面;
他渴望幸福,却一次又一次溃败;
……
身为穆蒂斯系列小说世界中的冒险家与主角,马克洛尔是纵横于陆地和海洋的英雄,他身上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是一个“生存在史诗世界的个体”。他总是忍不住远离繁忙的港口,远离安稳的生活。运输木料、开酒吧、开妓院、走私军火、挖矿淘金……他做过无数在法律边缘游走的荒唐工作,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拨开索然无味的缕缕时光,不让他滑向那即将战胜他的虚无。
这位永远流浪的瞭望员是穆蒂斯的“另一个自我”。马尔克斯说“我们都是马克洛尔”,马克洛尔也是我们每一个当代人的原型。“我们都是被我们的童年、被我们自己的生命放逐的人。”他的命运就是每一个在现实中挣扎的人的命运。他永远在漂泊,在流浪,“既没有地方可以归去,也不想归去任何地方”。
在这部由七个部分组成的“小说群”里,穆蒂斯赋予了叙事以非同寻常的现代方式——让小说里的时间与人生像海浪一样奔涌往复,最后,七部曲叠错激荡成为壮观的个人史诗。
作者简介:
阿尔瓦罗·穆蒂斯(Álvaro Mutis,1923-2013),哥伦比亚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他是外交官之子,从小乘坐半载货半载人的小船往返于欧洲和哥伦比亚;
他在标准石油、泛美航空、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做公关,做过记者,当过电台主播,主持过电视购物;
他信口胡说,引得观众提枪在街角埋伏;
他挪用公司慈善款项支持文化上的“堂吉诃德”事业,逃亡国外,又被抓捕入狱;
他是马尔克斯的挚友,总是马尔克斯作品手稿的第一位读者……
他早年写诗,在1953年创作的诗集《灾祸的元素》(Los elementos del desastre)中首次出现了“瞭望员马克洛尔”这一人物:不幸的航行,荒唐的工作,美景的消亡……1986年起,他开始创作以马克洛尔为核心的小说,塑造出20世纪西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形象之一。
1974年获哥伦比亚国家文学奖,1997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和西班牙伊比利亚美洲索菲亚女王诗歌奖,2001年获塞万提斯奖。
试读:
阿尔瓦罗·穆蒂斯跟我说好,绝不在公共场合谈论对方,好也不说,坏也不说,免得互相吹捧。然而,整整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就因为不喜欢我给他推荐的理发师,这好好的有益社会健康的约定生生被他撕毁。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伺机报复,今天这机会再好不过。
当时,阿尔瓦罗说起一九四九年,贡萨洛·马利亚里诺是怎样在恬静宜人的卡塔赫纳介绍我们俩相识的。我也一直以为那确实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直到三四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听他随口聊了几句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让我猛然回想起大学时光。
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没钱去咖啡馆学习,只好逃到波哥大国家图书馆鲜有人光顾的音乐厅。在下午那些屈指可数的听众里,我特别讨厌一个长着传令官的鼻子、土耳其人的眉毛、像水牛比尔一样身大脚小的人。他总是四点来,也总爱点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十年后,直到那天下午,在他墨西哥城的家中,我才突然认出他那洪亮的嗓门、孩子般的小脚、抖抖索索连斗大的针眼都穿不过去的双手。“真见鬼,”我垂头丧气地说,“那人居然是你!”
我唯一遗憾的是,旧恨难平,却不能秋后算账。时光无法倒流,毕竟,我们一起欣赏过那么多乐曲。因此,尽管学识渊博的他居然对波莱罗[1]没有丝毫感觉,我们也没有分道扬镳,还是朋友。
阿尔瓦罗干过各种各样奇怪的行当,遇险无数。十八岁那年,他在国家电台当主播,节目中随口胡诌了几句,被一个爱吃醋的丈夫听成给他妻子打暗号,提着枪在街角埋伏。后来,总统府一次正式活动,两位耶拉斯总统的名字被他弄混了,颠来倒去地叫了半天。再后来,身为公共关系专家,他却在慈善会上放错了电影。原本应向社会上广发善心的太太们播放一部反映孤儿生活的纪录片,却被他放成一部修女与士兵乱搞一气,还有个漂亮名字叫《种植橙树》的色情片。此外,他还在航空公司做过公关部主管,后来那家公司在最后一架飞机坠毁后关门大吉。他工作的时间都花在认尸、通报死者家属、接待媒体上。家属毫无思想准备,本以为喜事临头,开门一见是他,惨叫一声倒地。
后来的工作稍好了一些,为了从巴兰基亚的一家酒店搬出世界首富的华美遗体,他在街角的殡仪馆紧急采购了一具棺材,装好后立在员工电梯里运下楼。侍应生问棺材里装的是谁,他说是“主教大人”。他在墨西哥的一家餐馆大声说话,邻桌的以为他是电视剧《铁面无私》里的沃尔特·温切尔[2](阿尔瓦罗给他配过音),就扑上去要揍他。他在拉美推销了二十三年电影,行程加起来绕地球转了十七圈,依然本性不改。
而我最欣赏他的,是他教师般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一心想做教师,却因为热衷台球这个不良嗜好,从未如愿。我所认识的作家中,没有谁像他那样关心他人,尤其乐于提携后辈。他煽动年轻人违背父命,投身诗歌,用禁书毒害他们,用巧舌迷惑他们,鼓励他们闯荡世界,坚信在这世上做一个诗人还不至于饿死。
这么难能可贵的品质,最大的受益人是我。我说过,是阿尔瓦罗带给我第一本《佩德罗·巴拉莫》[3],还对我说:“拿着,好好学学。”他没想到,这么做等于自掘坟墓。读完胡安·鲁尔福,我不仅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写作,还总备个故事,专用来搪塞别人。写《百年孤独》的时候,我的这种自救方式,绝对的受害人恰恰又是阿尔瓦罗·穆蒂斯。那十八个月里,他几乎夜夜登门,让我跟他说写了什么。尽管我说的是另一个故事,但依然能从他的反应中获得启发。他兴致勃勃地听,添油加醋地四处宣扬。之后,他的朋友们又把他讲的故事讲回给我听,我从中又汲取了不少养分。初稿完成后,我送到他家。第二天,他怒气冲冲地给我打电话。
“您让我在朋友面前没法儿做人,”他冲我嚷嚷,“这玩意儿跟您讲的不是一回事。”
从那以后,他总是我作品原稿的第一个读者,见解犀利,忠言逆耳。因为他,我最起码将三个短篇束之高阁。我也说不清我的作品里究竟有多少他的成分,但一定不少。
别人常问我,这年头,人心叵测,我们俩的友谊为何能天长地久。原因很简单:阿尔瓦罗和我为了做朋友,很少见面。尽管我们在墨西哥城一起住了三十多年,几乎算得上是邻居,但在那儿我们很少见面。我想见他,或他想见我的时候,得先电话联系,确定彼此都有见面的意愿。只有一次,我违背了这条基本原则,而阿尔瓦罗当时的表现,足以说明他是个什么样的朋友。
事情是这样:那天晚上龙舌兰酒喝多了,我和另一位好友凌晨四点去敲阿尔瓦罗独居的公寓大门。他睡眼惺忪地把门打开,我们俩二话不说,从墙上取下一幅珍贵的一点二米长、一米宽的博特罗[4]油画,抬了就走,然后胡乱糟蹋一通。对这次入室抢劫,阿尔瓦罗事后只字未提,也从未打听过那幅画的下落。而我也直到他今天迈入古稀之年,才说出内心的愧疚。
维系友谊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一起时,多半在旅行,大部分时间都忙着应酬别人、处理其他事,不到万不得已,顾不上对方。对我而言,在欧洲公路上与他共度的无数时光相当于在大学补念了人文艺术专业。在巴塞罗那到普罗旺斯艾克斯三百多公里的路上,我学到了有关阿维尼翁教皇与清洁派教徒的知识。去亚历山大、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贝鲁特、埃及、巴黎,也都有同样的收获。
然而,疯狂旅行中,我也上过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堂课。当时,我们正穿越比利时的田野。十月里,雾蒙蒙的,刚被弃置的露营地里散发着人的粪便味。阿尔瓦罗开了三个多小时车,破天荒地一句话没说。突然,他冒出一句:“孕育伟大的自行车手与猎手的国度。”他从未解释过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但承认他体内有个毛茸茸、流口水的大傻子,正式会见也好,总统官邸也罢,一不留神就溜出来说几句。写作时也得管着,这傻子疯得厉害,又踢又跳,总想篡改书稿。
但这所流动学校留给我最美好的回忆还不是课堂,而是课间。在巴黎等候夫人们购物时,阿尔瓦罗就往远近驰名的咖啡馆门前台阶上一坐,仰面朝天,翻出白眼,大手一伸,作乞讨状。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用地道的法国方式尖刻地对他说:“穿羊绒衫讨饭,脸皮真厚。”可他还是给了一法郎。不到一刻钟,阿尔瓦罗就净挣四十法郎。
在罗马的弗朗西斯科·罗西[5]家,他用自创的意大利语,其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意大利语单词,滔滔不绝地描述了自己在金迪奥的恐怖遭遇,迷住了意大利影视文化精英费里尼、莫妮卡·维蒂[6]、阿莉达·瓦莉[7]和阿尔贝托·莫拉维亚[8],让他们津津有味地听了好几个小时。在巴塞罗那的一家酒吧,他用巴勃罗·聂鲁达灰心丧气的语调朗诵了一首诗,有个听过聂鲁达声音的人以为他就是聂鲁达本人,居然向他索要签名。
他写过一句诗:“我知道,我永远去不了伊斯坦布尔。”读得我心惊肉跳。这首诗对于一个无可救药的君主制国家来说相当怪异,人家不叫伊斯坦布尔,只叫拜占庭,好比早在被历史证明其正确性之前,我们就一直只叫圣彼得堡,不叫列宁格勒一样。我也不懂为什么老觉得应该把诗里提到的去伊斯坦布尔变为现实。终于,我说动了他,一起坐船去,坐的是慢船,挑战命运时,得不慌不忙。在那儿待了三天,我老担心那诗句成谶,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直至今日,阿尔瓦罗已是年届七十的老人,而我还是六十五岁的孩子的这一天,我才敢说:当年去伊斯坦布尔,我不是为了打败诗歌,而是为了挑战死神。
我以为自己就要一命呜呼的那次旅途,阿尔瓦罗也在身旁。当时,我们正驾车在明丽的普罗旺斯疾驰,突然,一位司机逆向行驶,发疯似的冲了过来。我只好往右猛打方向盘,根本来不及去看我们会摔在什么地方。刹那间,我有种奇妙的感觉,方向盘飞在空中,完全不听我使唤。一向坐在后排的卡门和梅塞德斯屏住呼吸,直到车子像孩子一般摔进春季葡萄园旁的排水沟。那一刻,我唯一记得的是副驾驶座上阿尔瓦罗的神情。摔落前,他看了我一会儿,满脸同情,似乎在说:“瞧这傻瓜,干吗呢?”
在我们这些认识他母亲并深受其害的人眼里,阿尔瓦罗的所作所为还算不上惊世骇俗。卡洛琳娜·哈拉米略人长得漂亮,脑子却不好使。她从二十岁起就不再照镜子,因为觉得镜子里的人不是自己。老太太年纪一大把,天天骑着自行车,穿件夹克,去草原给庄园里的工人义务打针。在纽约的一个晚上,我们出门看电影,拜托她照看我和妻子十四个月大的儿子。她一本正经地劝我们三思,说她在马尼萨莱斯也帮忙照看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哭个没完,她只好喂他一块有毒的桑葚糖,让他闭嘴。但即便如此,去梅西百货公司那天,我们还是把孩子托付给她,回来时只见她独自一人。保安四处找孩子的时候,她就跟她儿子一样沉得住气,还安慰我们:“别着急,阿尔瓦罗七岁那年,也在布鲁塞尔走丢了,瞧他现在不是挺好!”阿尔瓦罗就是她的升级版,还比她有学问,当然更了不得!他名震寰宇,不仅诗写得好,人也特别好。所到之处,胡吃海喝,夸张怪异,胡说八道,令人难忘。只有我们这些了解他、热爱他的人才知道,他只是咋咋呼呼,虚张声势罢了。
阿尔瓦罗·穆蒂斯不幸是个太过和善的老好人,谁也想象不到他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我见过他在黑暗中,忧伤地躺在书房的沙发上。那模样,不会让前一晚任何一位幸福的听众羡慕。幸好,那无法治愈的孤独也孕育出他广博的学识、非凡的阅读能力、无尽的好奇心和忧伤凄美的诗歌。
我见过他沉浸在布鲁克纳[9]气势恢宏的交响乐里,像在欣赏斯卡拉蒂[10]的嬉游曲。我见过他躲在奎尔纳瓦卡花园僻静的角落,趁着悠长假期远离尘嚣,徜徉在巴尔扎克全集奇妙的文字森林里。有些人隔些日子会看部牛仔片,而他隔些日子会把《追忆似水年华》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他的择书标准是不少于一千两百页。他蹲过墨西哥监狱,所犯的罪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犯过,可只有他蹲过监狱。他说,那十六个月,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我一直以为,他写书慢,是因为工作忙,再加上他字写得不好,像鹅亲自抓着鹅毛笔写出的鬼画符,足以让猎狗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迷雾中惊恐地乱吠。多年前,我问他,他说等退了休,没有俗务缠身时,会潜心写作。果然,飞了那么多年,他一跃而下,没用降落伞,稳稳着地,文思泉涌,实至名归。六年写八本,创造了文学史上的伟大奇迹。
他的书,随便挑一本,读上一页,你就会明白,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全部作品,连同他的一生,都在确信无疑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失落的天堂再也无法找回。马克洛尔并不是一个人,这显而易见。我们都是马克洛尔。
作为结束语,我斗胆提议:今晚来祝阿尔瓦罗七十大寿的人,第一次,别假客套,别怕流眼泪,别骂骂咧咧,真心实意地告诉他,我们有多崇拜他,妈的,我们有多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