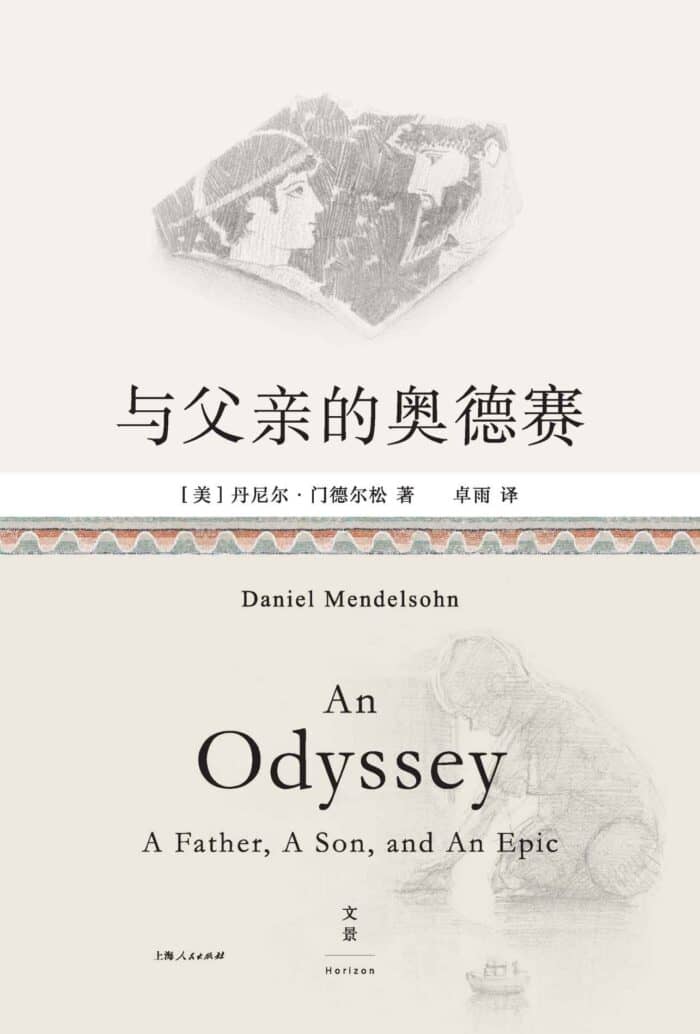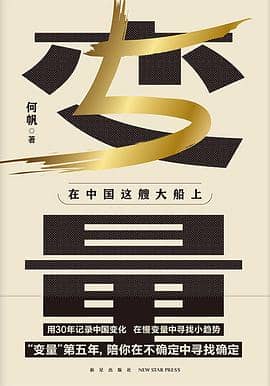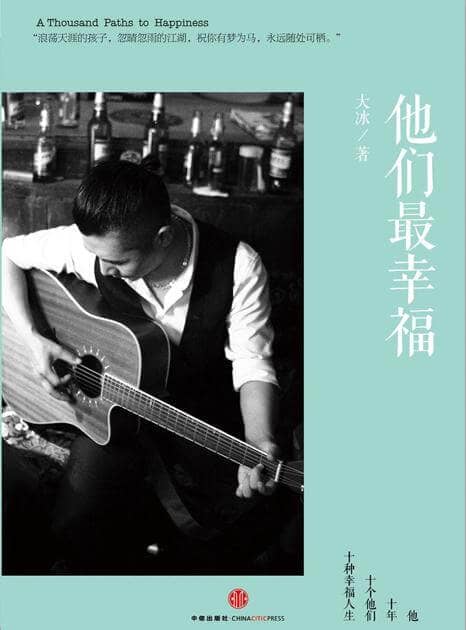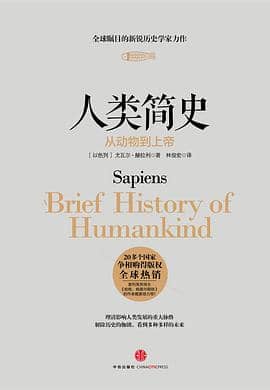内容简介:
哪一面才算真正的自己?
《奥德赛》如此设问,且一个人可能有几重面貌呢?
那一年,父亲旁听我的《奥德赛》研读课,之后我们跟随奥德修斯的脚步巡游观光。
由此我明白,答案可能出人意料。
〰〰〰 〰〰〰 〰〰〰 〰〰〰
门德尔松81岁的数学家父亲去旁听儿子给本科生开设的《奥德赛》研读课,细读关于“漂泊与回家”的12110行史诗,之后父子二人又一起参加《奥德赛》主题游轮旅行。在文本与空间的“奥德赛之旅”中,他得以一次又一次重新理解父亲。
《奥德赛》是英雄漂泊多年,历尽千辛万苦得以归乡的故事;也是稚子长大成人,在寻父过程中逐渐了解父亲的故事。
《与父亲的奥德赛》则将《奥德赛》中古希腊英雄父子的传奇史诗与当代父子的普通人生并置,在文本与现实的交叠中,两对父子相互映照。
时空交错的回旋里,父、子与史诗的故事缓缓展开。
作者简介:
丹尼尔·门德尔松(Daniel Mendelsohn,1960—),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文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博士。
门德尔松精研古希腊文学,译有《C. P. 卡瓦菲斯诗歌全集》(C. P. Cavafy: Complete Poems),著有《难以触及的拥抱:欲望与身份之谜》(The Elusive Embrace: Desire and the Riddle of Identity)、《与父亲的奥德赛》(An Odyssey: A Father, A Son, and An Epic)、《失落者:追寻六百万中的六人》(The Lost: A Search for Six of Six Million)、《如此美丽,如此脆弱》(How Beautiful It Is And How Easily It Can Be Broken)、《等待野蛮人:从古典学到流行文化》(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Essays from the Classics to Pop Culture)、《如何阅读经典》(How to Read the Classics)等著作;作品亦常见刊于《纽约客》《纽约书评》等杂志。
试读:
数年前的一月某晚,父亲问我,可否旁听我的课程,就在那之后不久的春季学期,我要给大学本科生开一门《奥德赛》研读课。父亲是名退休的研究型科学家,那年八十一岁。当时我自以为知晓他这样做的原因,我同意了。接下来的十六周里,父亲会在两地间每周往返一次:他仍与我母亲住在长岛近郊一栋朴素的错层式宅子里,我在那儿长大;由此出发,他要来我任教的河畔校园,一所名为巴德的小型学院。每周五上午十点十分,他会坐在上这门课的大一新生之中,与大家一同讨论这部古老的诗歌,一部描写了漫长的旅途、持久的婚姻,探讨了渴求还乡之真意的史诗。那些学生多为十七八岁,年龄甚至不及父亲的四分之一。
学期伊始正值隆冬,当时父亲还没有想方设法使我相信史诗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其实算不得“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会说,这人是个骗子,他还对妻子不忠!),那会儿他正因天气忧心不已:汽车挡风玻璃上积满了雪,路面上落了霙,人行道结了冰。他害怕滑倒,父亲说,他发元音还带着成长于布朗克斯区的烙印,听起来像“娃倒”。因为他害怕滑倒,我们会小心沿狭窄的柏油路走到教学楼里,那是一栋有意建得像万豪酒店的砖楼,样式中规中矩;又或穿过短短的走道前往校园尽头那栋斜顶屋,每周有几天,我会在此留宿。为避免在一天内花费六小时往返,他会在这屋子里过夜,睡在我充作书房的那间多余卧室里。他躺在一张用于日间小憩的窄床上,小时候我就睡这张床——待我到了与婴儿床作别的年纪,父亲亲手为我打造了这张低矮的木床。如今,关于这张床,有件事唯有我与他知晓:它由一扇廉价的空心木门改造而来,父亲为之添上四条结实的木腿,以角铁固定,至今,其牢固程度仍与他五十年前初初组装零件与木头时无异。除非挪开床垫、露出底下的镶板门,否则没人会知道这个有趣的小秘密。那个春季学期,父亲参加《奥德赛》研读课时,就睡在这张床上。之后不久他患病,我与兄弟姐妹不得不开始像父亲般照料他,焦虑地看着他时睡时醒,躺在各种巨大而复杂、根本无法称之为“床”的奇怪机械装置上,装置起降时伴着吵闹的嗡鸣,如起重机一般。但那都是后话了。
我有好几处住所,父亲过去一直觉得这事儿可逗了:这栋乡村校园里的屋子;我儿子与他们母亲居住的,位于新泽西的安逸老家,我会上那儿过小长假;我在纽约市的公寓,随着时光流逝、人生版图拓宽,我组建家庭,后又执掌教鞭,此处也就无异于搭火车旅行的经停站了。你总在路上,偶尔,挂电话前父亲会这样说,他讲到“路上”这个词时,我能想象出他稍显困惑,摇了摇头的模样。因他人生大半时光都在同一栋房子里度过:就是我出生前一个月他搬进去的那栋,也是二○一二年一月某日他离开后再没回去过的那栋,那天距他开始旁听我的《奥德赛》研读课,已过去了一年。
《奥德赛》研读课从一月下旬持续至五月上旬。结课约一周后,我碰巧同身为古典学学者的朋友弗罗玛通了电话,她是我研究生时期的导师,近来很爱听我向她定期汇报爸爸在《奥德赛》研读课上的进展。谈话中,她提及几年前曾搭乘的地中海游轮航线,名为“《奥德赛》巡礼”。你应该参加这个!弗罗玛大声说道。经过这一学期,你还给父亲讲解了《奥德赛》,怎么能错过呢?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我给旅行代理人朋友发了邮件咨询,一位干练的乌克兰金发美人,名叫伊莲娜。她立即以全大写字母回复:“无论如何都别参加主题游轮旅行!”可弗罗玛是我的老师,我还保留着服从她的习惯。次日上午,当我致电父亲并告之与弗罗玛的对话后,他含糊地哼哼几声道,我想想啊。
我们上网查阅游轮航线的网站。我陷在纽约公寓的沙发里,盯着笔记本电脑,这一周我也搭火车沿美国东北走廊来回奔波,此刻有些筋疲力尽。我能想象到父亲坐在家中拥挤的办公室里,那房间原为我与大哥安德鲁共用的卧室:他打造的床铺,简单、低矮;从前那张朴素的橡木桌早已换成购自史泰博连锁店的刨花板桌,光滑黑亮的桌面已被上方的计算机设备压弯,包括台式机、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扫描仪,还有一圈圈电缆、大堆接线,一闪一闪的光,让屋里有种病房的氛围。我们查到,游轮将沿着神话里英雄长达十年的曲折还乡之路航行,特洛亚战争结束后他启程回家,多次遭遇海难,与怪物缠斗,备受折磨。游轮会从特洛亚起航,此地位于现今的土耳其,并以伊萨基岛为终点,这座希腊海域西部的小岛,据传即为伊塔卡,奥德修斯的家乡。“《奥德赛》巡礼”是一条“富有教育意义”的游轮航线,虽我父亲对任何被他视为“不必要的奢侈品”——诸如游轮旅行、观光与度假——都嗤之以鼻,但他对教育有着虔诚的信仰。于是,几周后的六月,我们登上游轮,不久前,我们还全身心沉浸在荷马史诗之中呢。此次旅行为期十天,一天就代表奥德修斯漫长还乡之旅的一年。
旅途中,我们几乎欣赏到了先前期待的一切,那些光怪陆离、前所未见的风光,以及曾雄踞于此的各种古文明的遗迹。我们看到了特洛亚城,那在我们这些外行人眼里无异于让调皮鬼踢了一脚的沙堡,传说中的高墙堡垒如今只余几列零散的石柱与巨石块,与下方的大海茫然相对。我们在马耳他附近的戈佐岛上看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巨石阵,此处亦有一方洞穴,传说即为美丽的宁芙(2)卡吕普索之家。正是她将奥德修斯困在岛上七年,并宣称只要他肯为自己抛弃妻子,就将获得永生,但奥德修斯拒绝了。我们见到几列多立克柱式庙宇的石柱,优雅简朴,因某些不得而知的原因未能完工,施工者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来自西西里岛的塞杰斯塔——还乡之旅即将抵达终点之际,就在西西里岛上,奥德修斯的同伴违背誓言,吃下属于太阳神许佩里昂的牛群,因而犯下大罪,尽数死去。我们游览了那不勒斯附近坎帕尼亚海岸上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古人相信此乃亡灵之境哈得斯的入口——亦即奥德修斯归途中另一处意外的经停点,但或许也并不那么意外,毕竟,继续自己的生活之前,我们必须与死者清算旧账。我们看到了胖乎乎的威尼斯堡垒,匍匐于干枯的伯罗奔尼撒草地上,仿佛蹲在欧石南上经过火焚的青蛙。这景观位于希腊南部、荷马故事里的皮洛斯附近,据诗人所述,皮洛斯城曾由一位仁慈但有些啰唆的老国王统治。此人名为涅斯托尔,曾在这小城中款待奥德修斯年轻的儿子,后者为打探父亲音讯前来:儿子离家寻找失踪的父亲,《奥德赛》便如此开篇。我们自然也看到了大海,欣赏了它的多重面貌,时而如明镜般光滑,时而如砺石般粗犷,某些时段看起来安全而开阔,其他时候却又极为神秘莫测。有时,海水呈浅蓝色,如此清澈,能一眼望见海底的海胆,这多刺的生物蓄势待发,一碰就蜇人,宛如某些战争留下的水雷,而战争的起因与参战者早已没人记得;亦有时,海水是种如葡萄酒般深邃的紫色,我们称之为红色,而希腊人称之为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