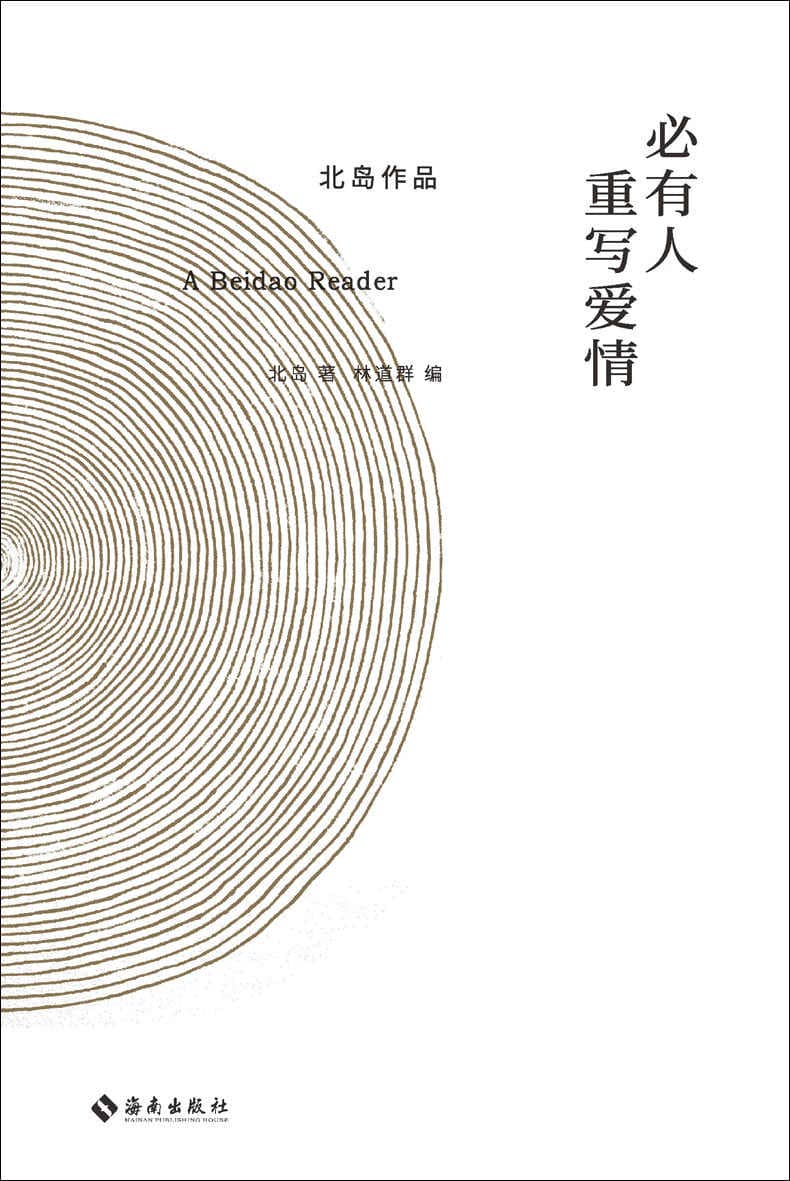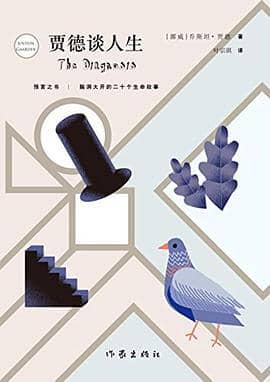内容简介:
鲁迅文学奖得主弋舟短篇小说集。
女人每次梦游都会攻击枕边人,这种“睡眠暴力”似乎和长期抑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男人被女友提出分手,学生时期对出身和外貌的自卑再次回到他的身上;
老人纠结是否将养老院发给自己的衣服带走,年轻时被栽赃的记忆再次唤醒了他内心的恐惧;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隐疾生活,无法对人诉说也无法解脱。
这些不曾被正视的隐疾,给我们带来难以填补的空虚,在漫长的人生中隐隐作痛。
作者简介:
弋舟
当代小说家,鲁迅文学奖得主。
弋舟以其对“时间”的复杂感知和精巧利用,构筑了独特的叙事模式。
他敏锐地捕捉到,生命中某些未曾被我们充分觉察的伤害,从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得到应有的慰藉与补偿,它们蛰伏在人的内心深处,令我们常常无端地陷入空茫;人生看似随波前行,实则却不断地在隐疾之上踉跄。本书为我们一一拨开这些藏匿于生活暗处的精神困境,让抚慰之光涌进。
已出版作品:《跛足之年》、《蝌蚪》、“刘晓东”系列、“人间纪年”系列作品集等长中短篇小说多部。
试读:
自退休那天起,他就开始思考“老去”的含义。其实,很久以来,“老去”这个事实已经在他身上悄无声息却又无可置疑地发生着——不知何时,他已经变成了秃头,性欲减退,眼睛也老花了。但对这一切,他都熟视无睹。他罔顾秃了的头和老花了的眼睛。在他的意识里,这些细节只是“老去”的外衣,顶多算是表层的感觉材料,而“老去”应该是某种更具本质性的突变,生命由此会有一个质的翻转——就像扑克牌经过魔术师的手,变成了鸽子。
这种偏执的思维方式也许来自他的职业。退休前,他在一所大学里教书,尽管他教授的是地理这样一门看似刻板的学科,但并不妨碍他养成那种善于抽象性的思维习惯。他习惯将大千世界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
退休意味着老年的正式降临,一种源自生命本身的紧迫感随之而来。他认为自己必须面对这个重大的问题,想清楚它,从而全面、客观地把握它。如此一来,就像一个浸泡在水里的人,自己却对水温毫无体察,他已然身陷在老年的岁月里,却孜孜以求着老去的含义。
老去是怎么回事呢?他绞尽脑汁地想。这成了他退休后的一门功课,每个夜晚入睡前,每个清晨醒来后,他都会在心里向自己发问。有时候,内心的诘问不自觉脱口而出,还会令他像一个真正的老人那样喃喃自语起来。这样的时候,他不免要梳理一番自己的生活,但生活本身却并不足以给出他所认可的答案,那无外乎就是由“秃了头、老花了眼睛”这样的碎片般的材料构成的浅显的表象。而他,需要的则是一个本质性的结论。
日复一日,十几年过去,中风袭击了他。好在救治得及时,并没有给他落下格外影响生活的后遗症。在床上瘫痪了一段日子后,他只是变得有些老年痴呆了。最初他记不清亲人的名字,后来干脆时时需要反复回忆才能记起自己的名字。十几年来困扰着他的那个问题却历久弥新,始终盘桓在他的脑袋里,以至有时他会突然口齿不清地向着虚无发问:老去是怎么回事呢?中风清空了他的脑子,只留下了这个唯一的问题折磨着他。原本可堪承受的冥想变成了备受煎熬的考问;然而事物总是有两面性,这个问题同时又激发了他几近告罄的记忆力,让他以此为基点,有限地恢复了一些脑力。
春天里的一天,就像醍醐灌顶了一般,他想起了自己的一位老同事。他们都是“困难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就读于同一所著名的大学,不同的只是一个学了地理,一个学了哲学。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了同一所学府,后来一度又结伴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共同的履历让他们成了心有戚戚的朋友,尽管平时交往不多,但彼此之间却都怀着一份默契。他不记得已经多久没有联系过这位老同事了。如今,对于具体的生活,他顶多只保留两天左右的记忆,两天前的事情对他的记忆来讲都是遥不可及的。但他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他终于想起这位教授哲学的老同事了,由此唤醒的记忆接着提示他,这位老同事睿智、深刻,差不多就是那个问题完美的回答者。他决定去向这位老同事请教。他让儿子送他去这位老同事家。其实他们住得很近,都在学院的家属区里。具体方位他当然是记不得了,好在他的儿子对一切都还算熟悉。在儿子的陪同下,他登门拜访了这位老同事。
老同事鹤发童颜,腰背挺拔,但精神却有些萎靡。对于造访者的到来,老同事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甚至还流露出了某种令人难堪的冷淡。老同事甚至都没有给造访者让座。
他自己落座了,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他的儿子为此显得有些尴尬,站在父亲身边向主人问好。
“我一点儿都不好,”老同事居然生硬地回答,“你不要跟我说普通话,你的普通话说得一点儿都不标准。”
“伯伯您真幽默。”他的儿子只好讪笑着给自己找台阶。
老同事不再理睬他的儿子,转而看向他。“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擦口水了吗?”老同事就这么刻薄地向他发问。
他下意识地揩了一下嘴角,果然有口水抹在了手指上。他感到有些羞愧,同时也生出了一股冲动。“退休这么久了……”他说,“有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搞明白。”他的口气好像是在为嘴角溢出的口水辩护。
可是,老同事一点儿也不接受他这样的辩护。“你从来就没有搞明白过什么,”老同事不屑地说,“你只知道经度和纬度这些没用的知识。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你何时搞明白过呢?”
关于“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下放时期”他们有过激烈的争论。那时他们都很年轻,在繁重的劳动和“触及心灵的检讨”之余,私下里一个以地理学为武器,一个以哲学为武器,各自立论,相互辩难,以此支撑着他们的精神生活。从那时候起,哲学便对地理学充满了蔑视。但他从未因此恼火过,这不仅仅因为那是一个哲学强势的年代,还因为从年轻时候起,他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他的这种性格,维系了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而且,那时期他们所蒙受的一切困厄,用哲学来分析似乎更能够给予他们撑下去的理由。哲学是那么有效!为此,他在心底是对这位老同事怀有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