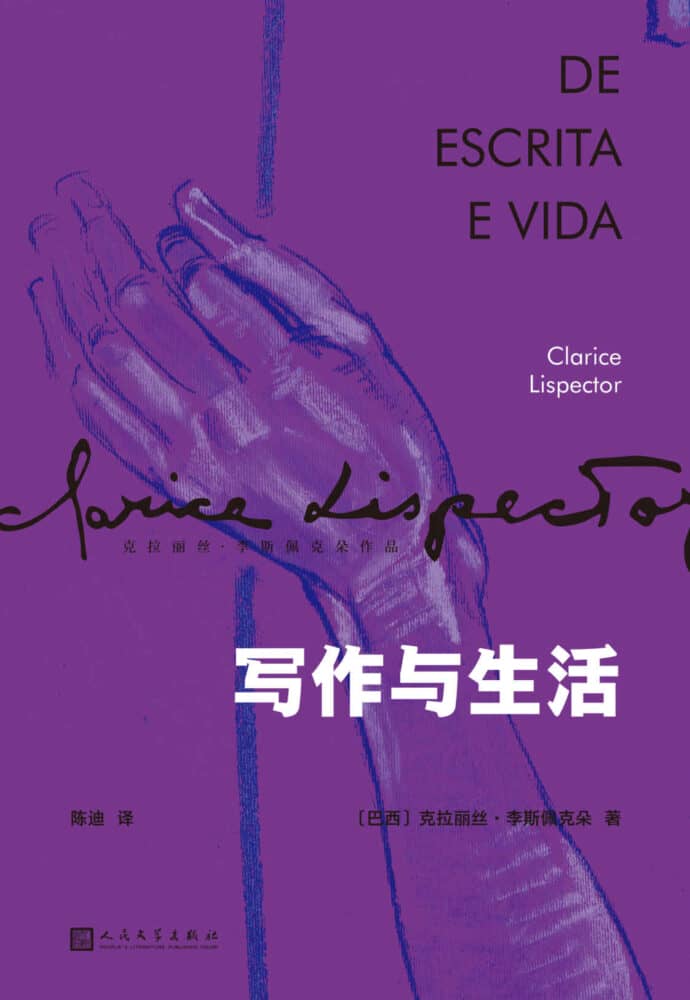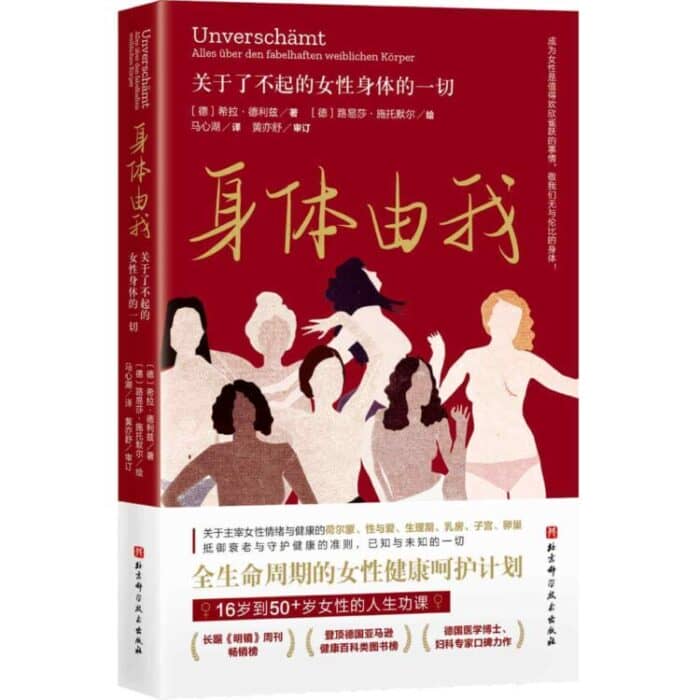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书是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对身体、空间等论题所做研究的成果结集,分为“身体的技术”“空间的政治”“后现代性的谱系”三个部分,共十九篇文章。第一部分的六篇文章论述“身体”在西方学术史中的地位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第二部分的六篇文章是作者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身体的社会学,以及权力如何把个人的身体局限在空间之中,第三部分收录的七篇文章是对后现代理论的各位大理论家德里达、罗兰•巴特、乔治•巴塔耶、福柯等的精彩评论,以及对后现代性理论的发展线索的整理回顾。
汪民安教授以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视角,考察个人身体、社会生活和现代政治的关联性,洞察细微,挖掘深入,表达精辟,会让读者对身体、对各类空间、对后现代哲学及其研究方法有更多的理解与启发。
作者简介:
试读:
第一部分 身体的技术
身体转向
罗兰·巴特在其自述中烦琐地列举了自己的诸多习惯和爱好。它们看起来微不足道并且匪夷所思,但他振振有词地说,这些源自身体的习惯和爱好是自己的个人性标记,是我和你的差异性所在。我和你不同,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1]。这是尼采哲学一个通俗而形象的说法。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再从“思想”“意识”“精神”的角度做出测定,甚至不再从观念、教养和文化的角度做出测定。也就是说,人的根本性差异铭写于身体之上。我们要说的是,身体,从尼采开始,成为个人的决定性基础。如果说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自身分成两个部分,分成意识和身体,而且意识总是人的决定性要素,身体不过是意识和精神活动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障碍的话,那么,从尼采开始,这种意识哲学,连同它的漫长传统,就崩溃了。
意识哲学的发源地在笛卡尔那里。但是,它的隐秘而曲折的起源悄悄地驻扎在柏拉图的哲学中。笛卡尔将意识和身体对立起来,但在柏拉图那里,灵魂和身体早就是对立的。
在《斐多》篇中,柏拉图记载了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态度。西方文化中第一个伟大的死亡事件——后世对此有无数的隆重分析,对当事人来说,却异常地轻松。在赴死前,苏格拉底谈笑风生,“快乐地”高谈阔论着哲学。为什么面对死亡无所惧怕?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解释道,真正的哲学家一直是在学习死亡,练习死亡,一直在追求死之状态。因为,死亡不过是身体的死亡,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自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2]。身体在死亡的过程中被卷走了,死亡就是让身体消失,让它从和灵魂的结合、纠缠中消失。这样,灵魂摆脱了身体而独自存在,并变得轻松自如。对于柏拉图来说,这完全值得庆幸。在此,柏拉图就显示了对身体的敌意。他基于这样的理由:身体对于知识、智慧、真理来说,都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因素,身体是灵魂通向它们的障碍。因为“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3]。柏拉图承认,有一种思考的境界,它完全由灵魂来实践。这样的灵魂固执地撇开身体,摆脱感受——视觉、听觉,以及其他一切身体感觉。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体,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疾病、恐惧,它们在不停地打扰灵魂的思考;同时,对战争、利益和金钱等的种种冲动贪欲也来自身体,所有这些,都搅乱了灵魂的纯粹探究,并使知识的秘密——这对于柏拉图来说至关重要——被继续曲折地掩饰起来。就此,柏拉图断定:“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4]
显然,有生之年,人们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活着意味着存在一个身体,活着的生命永远伴随着身体和灵魂间不愉快的争吵。对于灵魂来说,身体是它牢不可破的枷锁和监狱。但是,幸好有了死亡,灵魂的身体枷锁被解开了,它得以独自存在。因此,苏格拉底面对死亡,却毫无畏惧。正是由于身体的死亡,求真的坦途才得以顺利铺开,灵魂才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才能笔直地通向纯粹的智慧、真理、知识。对死亡的惧怕,对于一个求真的严肃哲学家来说,变得非常荒谬。接下来,柏拉图竭力论证了灵魂的不朽和不灭,这刚好与身体的暂时性和局限性相反。
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也拼命贬低身体,正是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导致了尘世间的苦难及罪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同样对身体的满足感嗤之以鼻,灵魂的快乐足以压倒身体的满足。那些理智的人,那些真正充实的人,无论如何不会听信身体的非理性的野蛮快乐,甚至不会将健康作为头等大事,除非健康有助于精神的和谐调节。而且,身体的欲望——对食物、性、名利等的欲望——同牲畜的欲望一样低等、任性,并可能导致疯狂的残杀。如果说,柏拉图最核心的哲学使命是对隐而不现的理念,对本质性的“一”,对一切现象背后的终极起因进行苦心挖掘的话,那么,身体则在这一挖掘过程中充当了一个捣蛋的角色,它为知识和理性的顺利推论设置了障碍。感性的东西——无论是身体还是艺术——总是与真理相去甚远,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保证身体需要的那一类事物是不如保证灵魂需要的那一类事物真实和实在的” [5]。
在这些论述中,身体和灵魂的对立二元论是一个基本的构架:身体是短暂的,灵魂是不朽的;身体是贪欲的,灵魂是纯洁的;身体是低级的,灵魂是高级的;身体是不真实的,灵魂是真实的;身体导致恶,灵魂通达善;身体是可见的,灵魂是不可见的。大体上来说,灵魂虽然非常复杂,但它同知识、智慧、精神、理性、真理站在一起,并享有一种对于身体的巨大优越感。身体,正是柏拉图所推崇的价值的反面,它距离永恒而绝对的理念相当遥远。
在此,身体,由于其需求、冲动、激情,首先在真理的方向上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它令人烦恼地妨碍真理和知识的出场并经常导向谬误。正是因为它导向谬误,所以它在伦理的方向上受到了谴责。对于柏拉图来说,伦理学的基础是理性的自由,善是灵魂的和谐,是内心世界的理性状态。身体随时爆发的冲动正是对这种和谐理性的粗暴破坏,它因此总是处在善的反面,处在伦理学所不齿的位置。在柏拉图的这个二元论传统中,身体基本上处在被灵魂宰制的卑贱——真理的卑贱和道德的卑贱——位置。可以说,自此以后,身体陷入了哲学的漫漫黑夜。
我们发现,灵魂和身体的这一对立关系在哲学传统中以各种各样的改写形式得以流传——我们不否认有一些历史片段溢出了这个传统,如文艺复兴时期。而且在这个关系中,身体总是受到指责和嘲笑。有些时候,这样的指责和嘲笑是发自道德伦理的,有些时候是发自真理知识的。但在大多数时候,它受到的哲学和宗教磨难有着上述的双重根源,只不过这种双重根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轻重之分。而且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这一对立关系中的身体和灵魂在同其他传统,尤其是同希伯来传统的结合中,各自找到了一系列的历史转喻形式:世俗人和僧侣、地上和天国、国家和教会等。它们之间的争执,都刻上了柏拉图的身体和灵魂的争执印痕。我们不可能详细地叙述这个身体受难史。只能概要地说,在中世纪,身体主要是遭到道德伦理的压制;而在宗教改革之后,尤其是从17世纪起,身体主要是受到知识的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