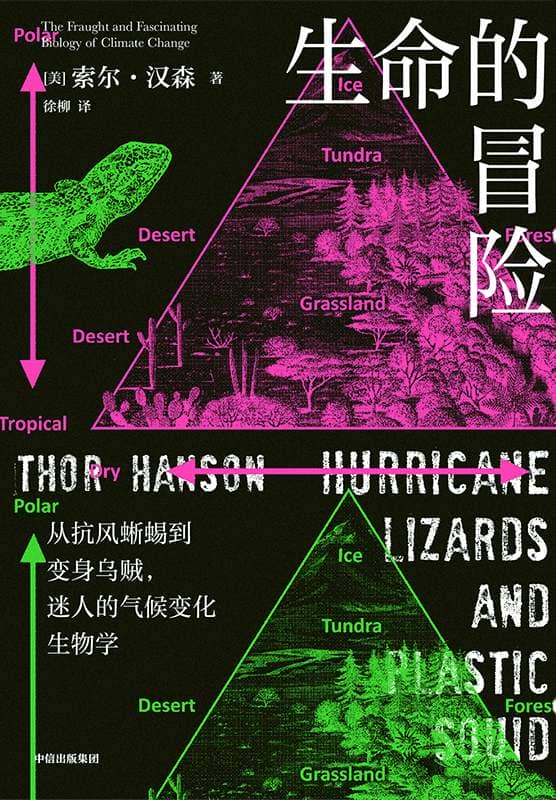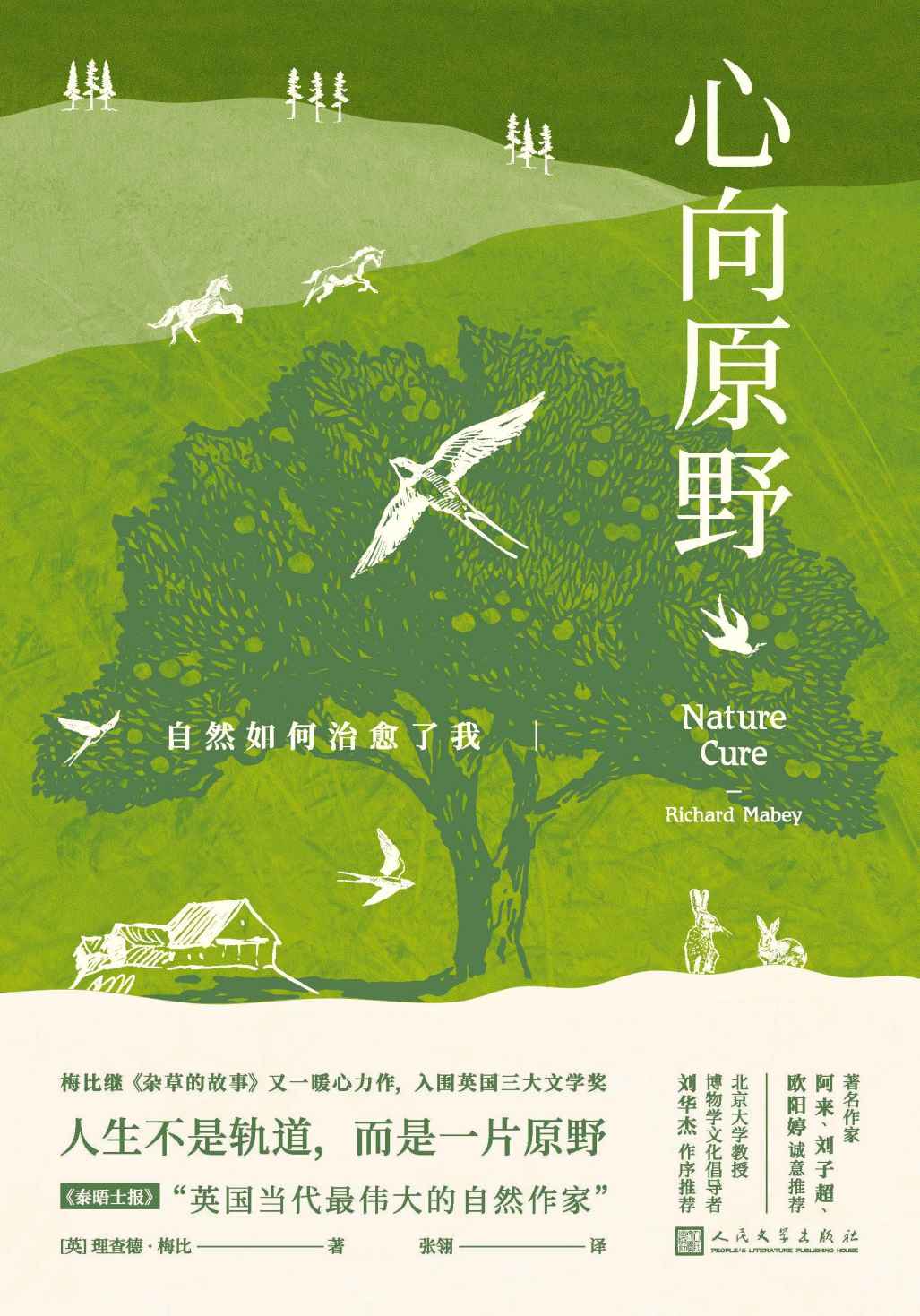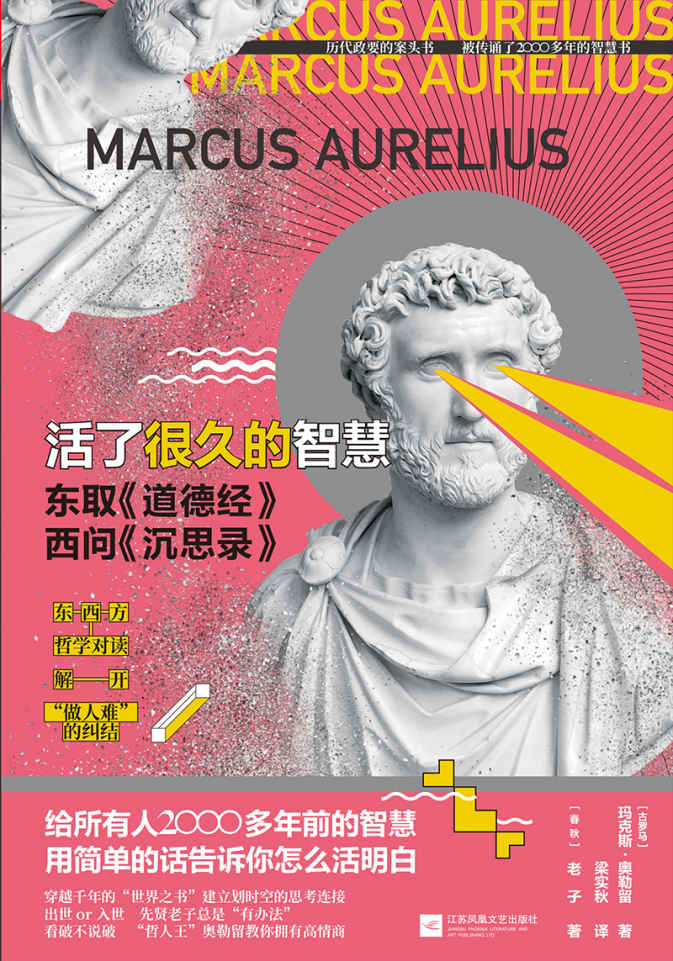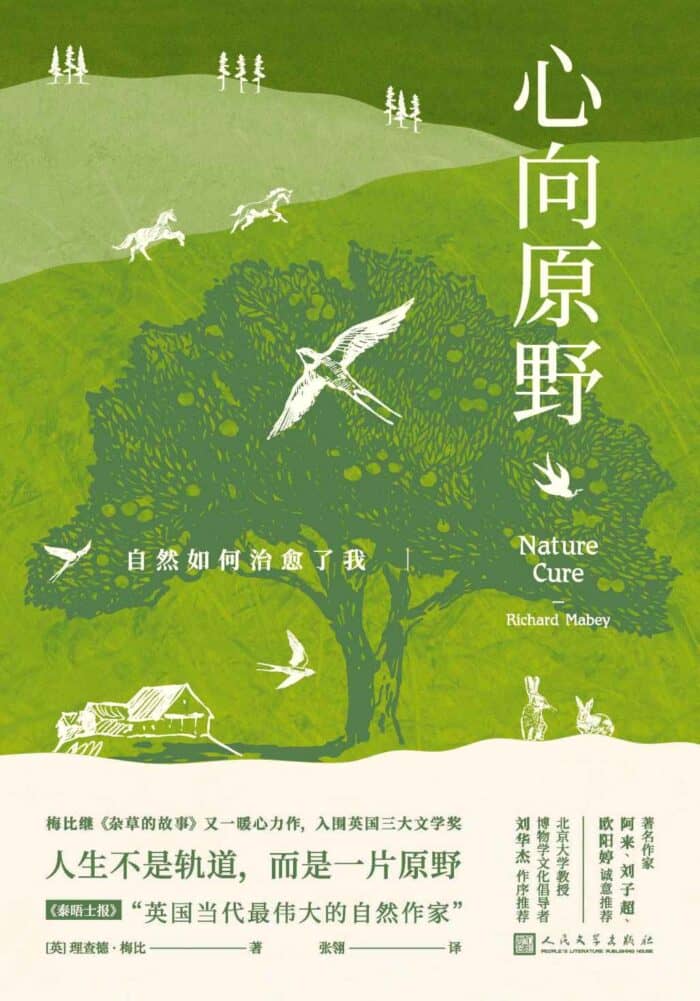内容简介:
热浪、寒潮以及其他极端气候事件已经成为现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类措手不及之际,自然界的动植物早已开始行动。
蜥蜴为了在飓风中求生,能在一代之内长出更大的趾垫;美洲大赤鱿应对海水变暖,甚至可以进化为看似不同的物种;棕熊可以放弃鲑鱼、树木移动的比鸟类还快,当珊瑚礁生病时,好斗的蝴蝶鱼没有了值得争夺的领土,立刻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大自然每天上演着关于希望、冒险以及顽强生命力的故事。
博物学家、保护生物学家索尔·汉森走访50余位学者,亲历野外考察发现,每一种动植物都展现出令人惊奇的生存策略:通过迁移、适应、进化来应对气候变化。调查与实验佐证了个体的反应有时可以决定种群、物种甚至整个生态群落的命运。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
对于人类而言,意识与行动之间似乎总有一道鸿沟。但有这么一群生物,面对生存的威胁,它们不会妄想改变,只会尽所能应对,它们是自然世界的冒险者,观察它们你会发现:行动起来,生命总有办法。
作者简介:
试读:
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的一切改变都令人厌烦。[2]
——托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1899年)
未见其形,先闻其声,两只鸟发出尖利聒噪的声音,从我头顶飞过,就像两只发狂的公鸡。噪声没完没了,我忍不住纳闷儿:怎么会有精神正常的人想在自己的房子里养这种鸟?然而,宠物交易的需求已经使大绿金刚鹦鹉从一个常见物种变成了濒危物种。我花了三年时间,研究它们在曾经的最佳栖息地的主要食物来源,不过,如今为了看到一只金刚鹦鹉,就需要花两天时间野外旅行,搭乘巴士、内河小船,最后还得来个机动独木舟才行。因此,当两只鸟突然从树顶腾起、飞越河面时,我感到了一种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的激动,我立刻明白了宠物爱好者为什么愿意忽略所有的吵闹扰攘。即便离得有点远,还是可以看到金刚鹦鹉那绚烂的绿色羽毛在阳光下闪耀,带着深红、栗色和棕色的波纹,嵌入宽大的蓝色羽翼,仿佛从天空到河流到雨林,目力所及的每一种颜色都被提取了出来,复现在它们的羽毛中。
我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些鸟儿从河的尼加拉瓜一边飞到哥斯达黎加一边,越过一行低矮的山峦,不见了踪影。瞥见鸟儿重新安家的证据,似乎很适合为我的中美洲研究画上完美句号,本来这个研究也是想鼓励鸟儿重新安家的。不过,我并不是直接研究金刚鹦鹉的,我的工作显示,榄仁木——这种树的果实像杏仁一样,是这些鸟的食物——能够在彼此不相连的小片的森林中无限生存和繁衍,通过蜜蜂勤劳的授粉工作实现远距离彼此连接。这项研究发现推动出台了一部保护哥斯达黎加东部低地榄仁木的新法律,在那里,放牧和水果种植使雨林被牧场、道路和庄稼隔开,变得四分五裂。人们希望,只要留下合适种类的树,金刚鹦鹉就能回来,从它们在北边的栖息地——尼加拉瓜自然保护区(我去一趟可真是大费周章)重新回到老地方。事实证明,这一进程目前进展得还不错。未来几年,会有成百上千的鸟儿像我亲眼见过的鸟儿一样,穿越圣胡安河向南飞,让大绿金刚鹦鹉再次成为哥斯达黎加一些地方常见的鸟类(嗯,还有常听见的声音)。人们会简单地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动物保护的成功故事来讲——返回的鸟儿不仅在榄仁木中寻找食物,还在树木巨大的树洞里筑巢、养育雏鸟。不过科学家们很快意识到,金刚鹦鹉和它们最爱的树的命运,其实是另一件事的更好例证,这件事不仅完全不同,还更重要。
回想起来,我发现“气候变化”这个词并没有单独出现在与我的榄仁木研究有关的诸多建议书、报告和同行评议论文中。当时,这个词似乎与这么一项具体、本地化的生物研究没什么关联性。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确实得到过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提示,是同一个野外工作站的另一位科学家随口提到的。她的数据显示了榄仁木如何通过提高呼吸率来应对炎热天气,“呼吸”就是植物将氧气纳入细胞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树木正喘得厉害。在一个变暖的世界里,这个迹象和其他一些应激迹象并不是好兆头,后来,气候建模师开始对中美洲进行预测,很明显,榄仁木处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一个专家告诉我“你研究的树可能不等21世纪过完就灭绝了”,还解释说,如果这个物种的分布范围向海拔更高、温度更适宜的地方移动,它就有可能存续下去。突然,一种几乎是事后想法的发现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成果——大型果蝠可以将榄仁木的种子散播到800米甚至更远之外。对于抗击炎热来说,这样够远够快吗?蝙蝠会向正确的方向移动吗?榄仁木能在已经满是树木的海拔更高的森林里站住脚吗?这一切对金刚鹦鹉意味着什么(它们也许会径直飞往凉爽的北方,而不受限于种子散播的缓慢速度)?金刚鹦鹉和榄仁木的故事表明的不是鹦鹉和树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而是一个体现了不确定性的案例,也是不断变化的地球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