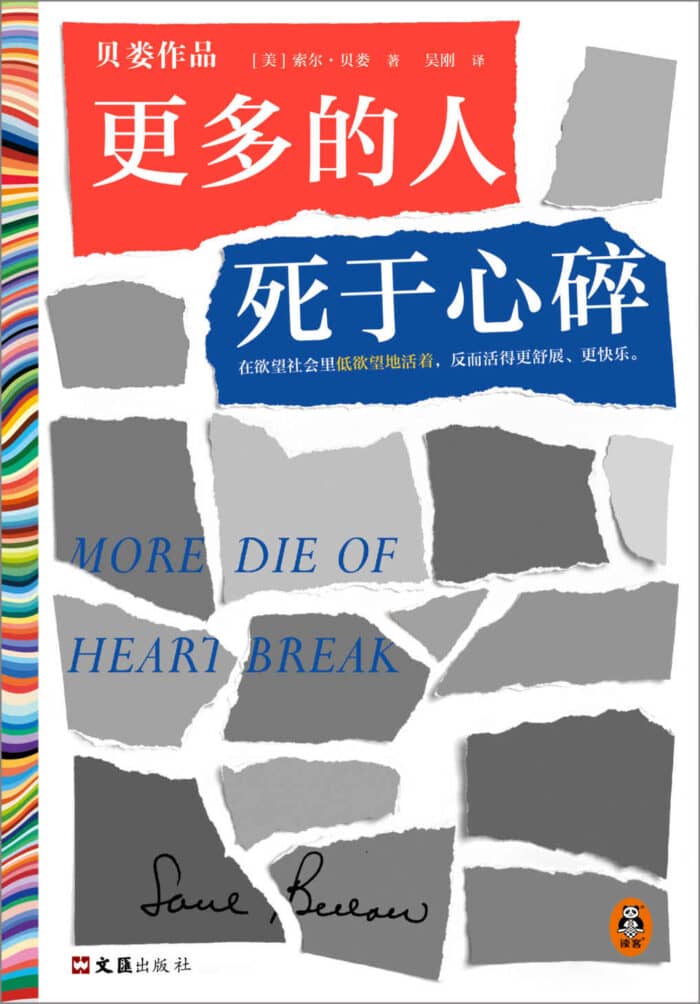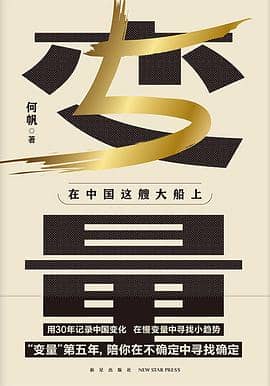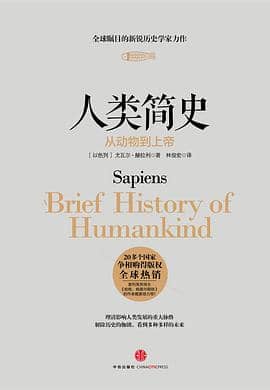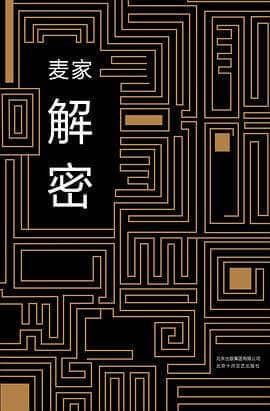内容简介:
在欲望社会里低欲望地活着,反而活得更舒展、更快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代表作01
在私人生活中我们心神不定,在公共问题上我们备受折磨……(而小说)是当代的一舍棚屋,一个遮风挡雨的精神庇护所。——索尔·贝娄诺奖获奖演说
这是一个人与欲望时代保持距离,反而过得充实的美妙故事。
我追随我的舅舅,不仅因为他是植物学天才,还因为他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怪。
他沉浸在科研的世界里,无心攀权附贵。
他更渴望幸福,却在情爱的追逐、算计和骗局中吃尽苦头。
他不敢忍受,更不会沉沦,而是感叹: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而不是核辐射。
干脆逃去北极地带,和植物待一会儿吧!
我真正想阐述的是以欲望为形式的苦难。——本书第309页
在抵达生命的尽头前,你有一张关于痛苦的清单得填满……首先是肉体上的痛苦——比如关节炎、胆结石、痛经什么的。下一类是丢面子、遭背叛、上当受骗、遭受不公正对待。但所有项目中让人最难熬的必然与爱情有关。——本书第6页
贝娄的作品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诺奖授奖词
贝娄的主人公在物质主义盛行、高楼林立和高速发展的时代里,为勇气、智慧、自我身份和人类的伟大感而战斗。——《纽约时报》
阅读贝娄,就是找回被现代生活驱逐的本真。
这个时代的心碎同样和欲望有关,心碎的时候,人更敏感,更复杂,也更容易打开自己。借由此时,我们得以调整生活的重心。
翻开本书,在欲望社会中,找回生活的快乐。
作者简介: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6.10—2005.4.5)
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获普利策奖、美国国家艺术勋章,三次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他用文学思考重要的问题,意图“在现代思想的废墟下重新发现世界的神奇”。
贝娄是文学大家,也是20世纪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的犹太移民家庭,少时就在俄语、法语、英语、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多语种环境下长大,九岁时举家迁往美国。他于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后转入西北大学。长期于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高等学府执教。1998年,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初版于1987年,小说以“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而不是核辐射”口口相传,成为时代的注脚,被无数读者反复阅读。
试读: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去年,在我舅舅贝恩(他的大名叫本诺·克莱德尔,是一位知名的植物学家)经历人生中的一场危机期间,他给我看了查尔斯·亚当斯[1]的一幅漫画作品。这幅作品平淡无奇,适足一笑,可贝恩舅舅的心思却一直萦绕其上,想要和我好好地讨论上一番。我不大喜欢对一幅漫画详加分析。他却过不去。好几次他说着说着就把话题又引到这上面来了,弄得我不胜其烦,动了把这幅漫画裱上画框送给他当生日礼物的心思。我心里想的是,索性把它挂上墙,一了百了。贝恩有时会让我心烦,是那种在你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人才能让你感到的烦。他在我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爱舅舅。
让人奇怪并且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亚当斯的其他作品并不怎么在意。他曾粗略地翻过亚当斯的一本作品大合集《怪物大聚会》,到头来令他意兴阑珊。为黑色幽默而黑色幽默,千篇一律,实在是没劲。打动他的只是那一幅作品。画面上是一对恋人——常见的带着凄凉与邪气的一对儿,场景也再典型不过:墓碑林立,紫杉森森。男的一脸凶相,女的一头长发(我想粉丝们管她叫墓地霞[2]吧),穿了件女巫的袍子。两人坐在墓地的长椅上,手握着手。下面配的文字很简单:
你不开心吧,亲爱的?
哦,不开心,不开心!不开心极了![3]
“为什么这幅画会打动我?”舅舅问。
“是啊,我也纳闷儿呢。”
他对我抱歉道:“一天里要和你聊到五次,肯定让你烦透了。我很抱歉,肯尼斯。”
“考虑到你的处境,我可以表示同情。要是换了别人钻牛角尖,我才懒得管呢。你这个我还能再扛一会儿——可你要是想看讽刺画或漫画,为什么不去看杜米埃[4]或戈雅[5]那样的大师呢?”
“人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得选择的。我不了解你们的文化。在我们中西部,心思要慢一些。我看得出来亚当斯不在大师之列,但他给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表达,我喜欢他这种疯疯癫癫的表现爱的方式。他没有想要去操控任何人。不像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舅舅对希区柯克很反感,“从希区柯克那儿你得到的是一件产品。亚当斯是循着自己躁动不安的本性来创作的。”
“几百年来爱情让我们变成傻瓜,所以这也不仅仅是他躁动不安的本性。”
舅舅的肩膀沉沉地耷拉着,一言不发。我的话他没有听进去,他要是不想听进去便是这副样子。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如果希区柯克站在我面前,我连跟他说上两分钟都不乐意,可要是换了亚当斯,我愿意跟他好好聊上半天。”
“我觉得不大可能。他不会跟你搭腔的。”
“虽说你比我小了二三十岁,可其实你在生活上的见识比我广。”舅舅说,“这我是认的。”他指的是我在法国出生并长大这件事。他每次跟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说“这是我的巴黎外甥”。他喜欢称自己不谙世故。他当然见识过很多,但或许他见识得不够用心,又或许没有带着功利的目的去见识。
我说:“你必须得跟亚当斯承认,你喜欢他的只有这一幅作品。”
“一幅,对。可它直指人心。”
然后,就像身处危机之中的人都会的那样,贝恩开始跟我讲他看到的人心是怎样的。由于被自己的麻烦事(他在婚姻上不愉快的尝试)弄得晕头转向,他对人心根本弄不明白。
“每种生活都有其基本的、各具特色的难处。”他说,“一个主题生出成千上万的变化来。变化,又复变化,直到你巴不得自己死了才好。我觉得你其实不该用‘钻牛角尖’。我对弗洛伊德没有任何不敬,但我也不喜欢用‘强迫性的重复’这个词。即便换‘执念’[6]也不对,因为它也可以指掩饰难以启齿的可耻之事。有时候我会瞎想,不知道我的主题会不会跟植物形态学有什么关系。但或许与干什么职业无关。要是我成了花店老板,或如我母亲所愿成了药剂师,我依然还会听到那同样冷酷的‘邦邦邦!’的命运敲门声……在抵达生命的尽头前,你有一张关于痛苦的清单得填满——那单子长得像联邦文件,只不过那上面要填的是你得去受的苦。有无数种分类。首先是肉体上的痛苦——比如关节炎、胆结石、痛经什么的。下一类是丢面子、遭背叛、上当受骗、遭受不公正对待。但所有项目中让人最难熬的必然与爱情有关。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每个人依然要坚持呢?如果爱情伤得他们那么痛,而且到处都可以见到为情所伤的惨象,那人们为什么不理智一点,早早抽身而退呢?”
“因为不死的向往,”我说,“或者只是希望得到幸运的眷顾。”
舅舅总是想着要来上一场重量级的对话,所以跟他说话你要当心才行。如果把什么想法表达得不清不楚,只会增加他的不快。所以我对自己也得保持警惕,因为我也有相似的弱点,非得把什么事都说明白了才行,而我也知道揪住不放其实于事无补。但在舅舅上次经历危机期间,我对他屡屡想要自我反省的作风必须加以容忍。我的工作——我全部的责任——就是要令他振作起来。他在哪儿出了问题于我来说是一目了然的,我简直可以把问题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给他听。这样做增加了我的自得。在历数他一桩桩肉眼可见的过错时,我发现自己单就此事而言像极了我父亲——无论是手势、语调、不失亲和力的优越感,还是对于能弥合所有分歧、填平所有沟壑的自信。骤然醒觉自己说话腔调像的是谁令我心中为之一震。我父亲自有其过人之处,但我仍下定了决心要超越他。按照大家惯常的说法,他是“用更好的尘土制成的”[7];他智慧过人,跟大家“不在一个级别的赛事联盟”[8]。在某些方面他的确胜我不止一筹——网球、参战记录(这玩意儿我根本没有)、性能力、谈吐、长相等。但也有些方面(我自认为是一些更高级的方面)他毫无建树,而我却遥遥领先。因此,在应对舅舅的时候,听到自己竟然冒出了父亲的口音,乃至冒出了那些他为了让你明白而会用到的法语词(在某些英语显得不够精妙的地方),这对于我的人生规划而言,不啻一个重大的挫折。我最好对那些方面再重新审视,以确定它们的确算得上是一些方面,而不是虚幻的泡影。不管怎么说,舅舅跌倒的时候,我也跟他一起跌倒。我也会一蹶不振,这是无可避免的。我想我应该一直在场。我也的确一直在场,只是方式当时根本没有预见到。
贝恩的专业是植物解剖学和植物形态学。一位标准的专家应当是这样的,他对自己这一行该知道的全都知道,但除此之外便再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比如:“我是修油位表的,别找我修里程计。”或者就像那句玩笑话所说的:“我不是给人修面的,我只管打肥皂沫。修面请去街对过。”有些专业具有更为严苛的要求,从而令人与世隔绝,这是可以理解的。它们顺理成章地令投身其中者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通过贝恩认识了一些投身此类精密科学的人,他们身上的怪癖宛如天赋特权。贝恩从没想过要得到这种与人类保持距离的特权。要是他杜绝了这种“对外的关联”,便不会像现在这般从女士们那里惹来这么多伤心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