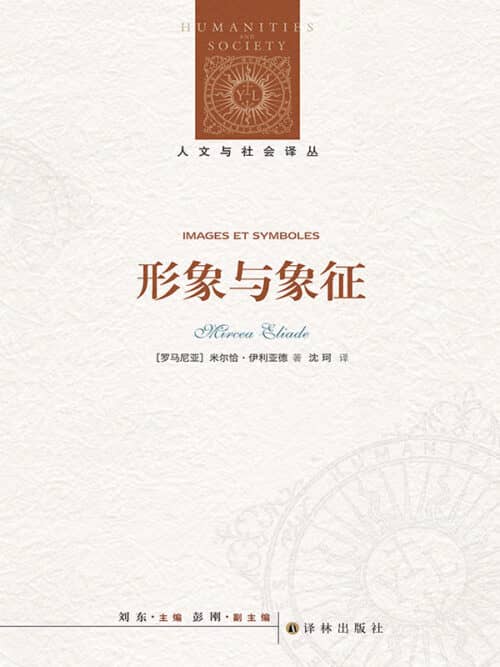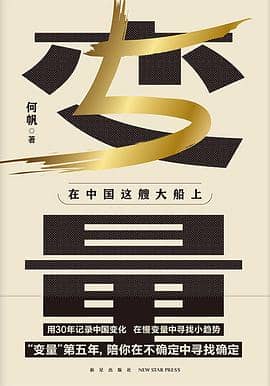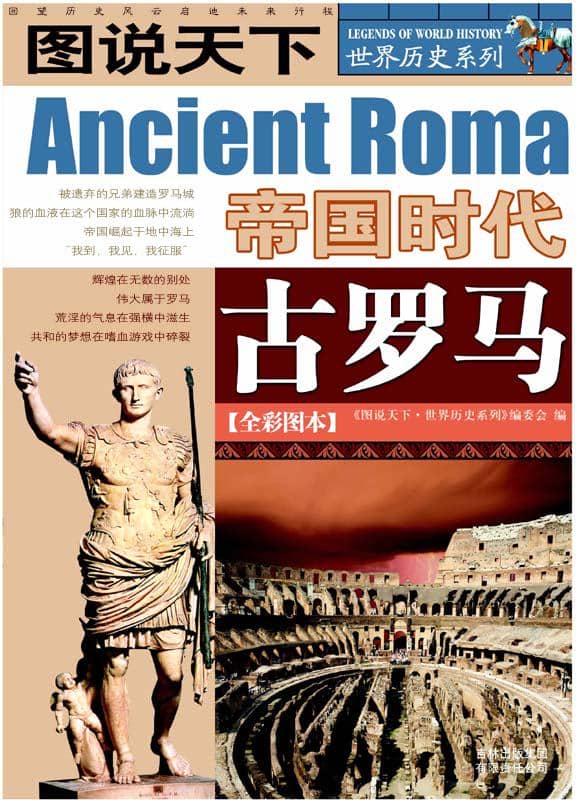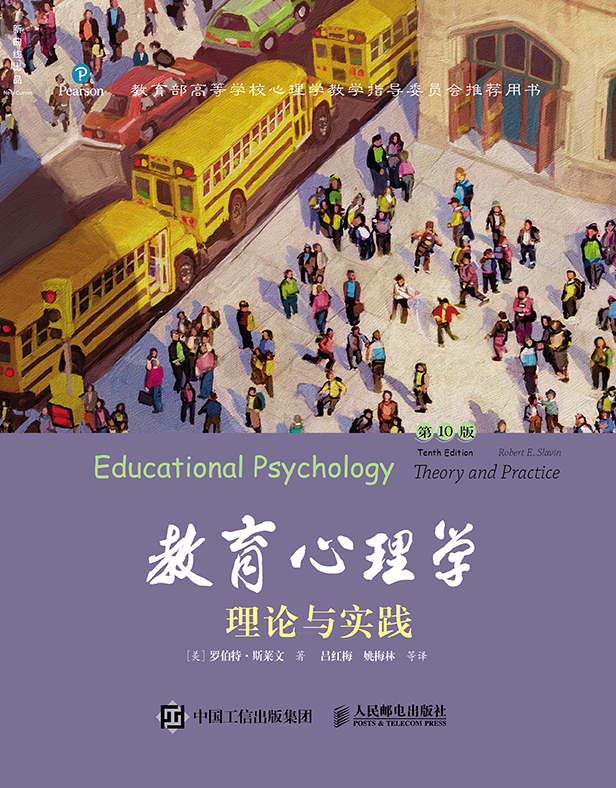内容简介:
标题:形象与象征
副标题:Images et symboles
象征性思维一直与人类共存:它先于语言和话语理性而存在。形象、象征、神话,这些并不是人们精神现象中随性的产物,它们的出现回应了某种精神需求,发挥了特定的作用,即揭示人类存在过程中隐秘的思想方式。因此,对它们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地了解渺小的人类,了解尚未向客观历史条件妥协的人类。
作者简介:
作者:米尔恰·伊利亚德
米尔恰·伊利亚德(1907—1986)
罗马尼亚宗教史学家、哲学家、科幻小说作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被认为是现代宗教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所提出的“圣显”理论和“永恒回归”理论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代表作有《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瑜伽:不死与自由》等等,几乎涵盖了20世纪所有宗教研究的重要领域。
摘选:
象征主义的重新发现
思想界掀起的精神分析狂潮,使其中的几个关键词也受到了极大关注:形象、象征、象征主义,这些字眼犹如货币一样,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关于“原始心理”的系统性研究,也证实了象征主义对古老思想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传统社会生活中起到的根本性作用。哲学中对“唯科学主义”的超越、“一战”后重燃的宗教热忱、超现实主义的诸多诗学体验,尤其是超现实主义研究(包括对神秘主义、黑色文学、荒诞主义等的重新发现),这些都在不同领域、通过形形色色的方式吸引着大众的注意,并引导他们将符号视为知识的独立表现形式。这一过程体现了19世纪反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一部分,也足以勾勒出20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的特征。然而,这一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转变并不是全新的“发现”,也不是属于现代社会的成就:象征主义只是通过重新定义“承载知识的符号”这一角色,重新回到直至18世纪依然蔚然成风的欧洲传统思维的轨道上,并显见于欧洲以外的其他文化中,包括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如亚洲、中美洲),以及古老的或是“原始”的文化。
不难发现,象征主义充斥西欧的时候,恰逢亚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亚洲在历史舞台上愈来愈活跃;同时,种族主义群体也摆脱小打小闹、若隐若现(大洋洲人、非洲人同样如此),从未真正进入过伟大历史(l’Histoire Majeure)的状态,如今也正积极地孕育和发展,并逐渐成为当下世界的重要洪流。“异域”国家或是“古老”世界正经历历史性的崛起,这与象征思潮在欧洲的再一次盛行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不过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确实非常有意思;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崇尚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19世纪欧洲会允许人们与“异域”文化进行精神的对话,况且这些异域文化无一例外地都不推崇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在面对这些被异域文化用来代表、传递和延续他们观念的形象和符号时,欧洲不会陷入瘫痪。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的现代欧洲宗教思想中,只有两种思想真正吸引过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关注,那就是基督教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思想表现形式不同,甚至出现在截然相反的领域,但都是关于救恩、灵魂救赎的学说,并将“符号”“神话”在欧洲以外的社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们可以这样说,时间上的巧合使西欧重新意识到符号的认知价值,而这恰恰发生在符号不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工具的时刻,发生在欧洲文化不得不与异于自身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共存的时刻,除非它将自己封闭在日渐枯竭的乡土氛围中。因此,所有与非理性、无意识、象征主义、诗学体验、异域的非意象艺术等相关而相继出现的研究成果和思想浪潮,都使欧洲能够更直观、更深刻地理解欧洲以外的社会准则,也更有助于欧洲与非欧洲民族的对话。要想评估近三十年来人种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世纪人种志学者面对“研究对象”以及调查结果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种学家已经完全明白象征主义对早期思想的重要性,包括其固有的严谨性、合理性,其思辨的大胆以及其“层次之高”。
不过,还是值得庆幸。如今我们正在尝试着去理解19世纪的人连想都不会想的一个问题:符号、神话、形象都是精神生活的实体,可以被掩盖、被消解、被摧毁,但永远无法被根除。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流传于整个19世纪的重要神话能经久不衰的原因。或许我们会了解,在本身微不足道又易于被人忽视而被迫不断易帜的情况下,符号、神话或是形象如何仰仗文学而免遭被雪藏的命运。[1]因此,“伊甸园”的神话能够一直流传至今,尽管在形式上它已经变成了“海洋乐园”;150年来,几乎所有的大文豪都会争先恐后地对大洋(Grand Océan)上的天堂小岛极尽赞美之能事,将这些小岛描绘成一个个极乐世界。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平淡无奇的风景、不利于健康的气候、丑陋肥硕的女人,等等。”将这样的场景置于任何一处地理的“现实”中,都屡试不爽。客观的现实与“海洋乐园”风马牛不相及:所谓的乐园只是理论层面的,是在接受了经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锻造后的各种乐园意象之后进行的模拟和再改造。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直信奉的伊甸园(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发现伊甸园!)成了19世纪的一座海岛,但它在人类心理构建中的作用从未改变:在“岛”上,在“伊甸园”里,存在是独立于时间和历史而延续着的;人是快乐的、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男人不必为了生计而劳作;女人都美若天仙,永远那么年轻,没有任何“规矩”去束缚他们的情感。在那遥远的小岛上,裸露被重新赋予了形而上学的含义:那是完人的状态,堕落之前的亚当的状态。[2]地理上的“现实”揭开了天堂景象的真实面目,丑陋肥硕的女人们走在所有游客的最前头:人们却不知道,其实每个人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