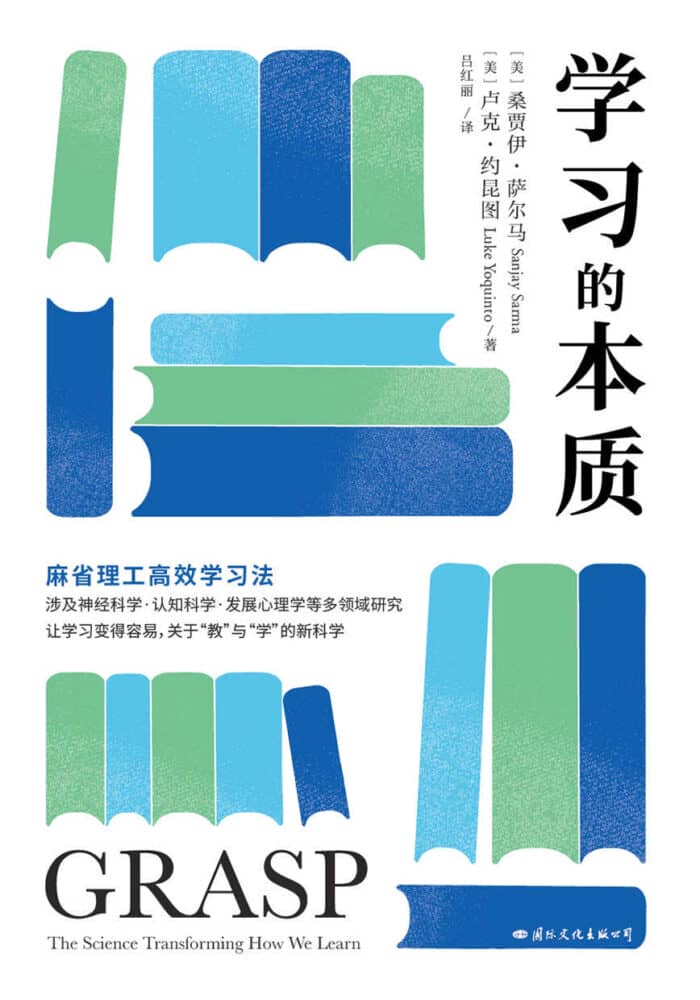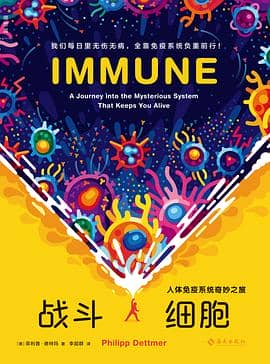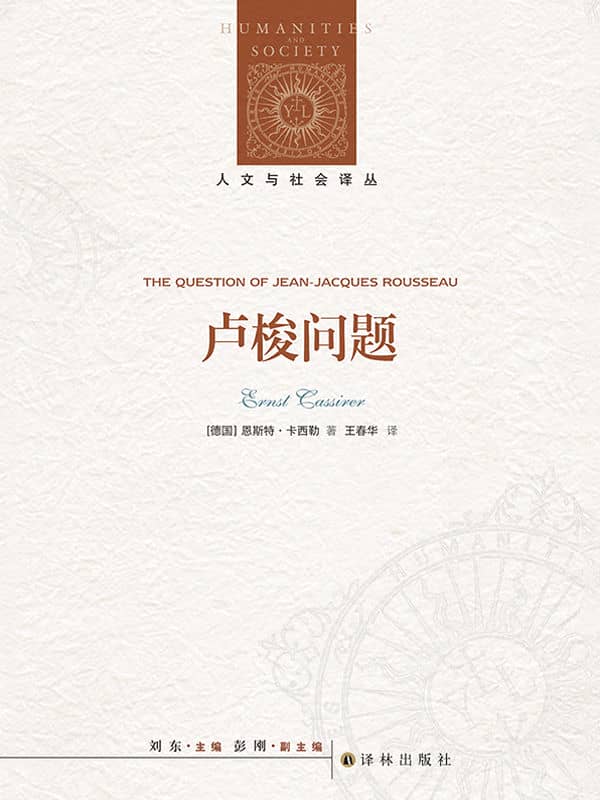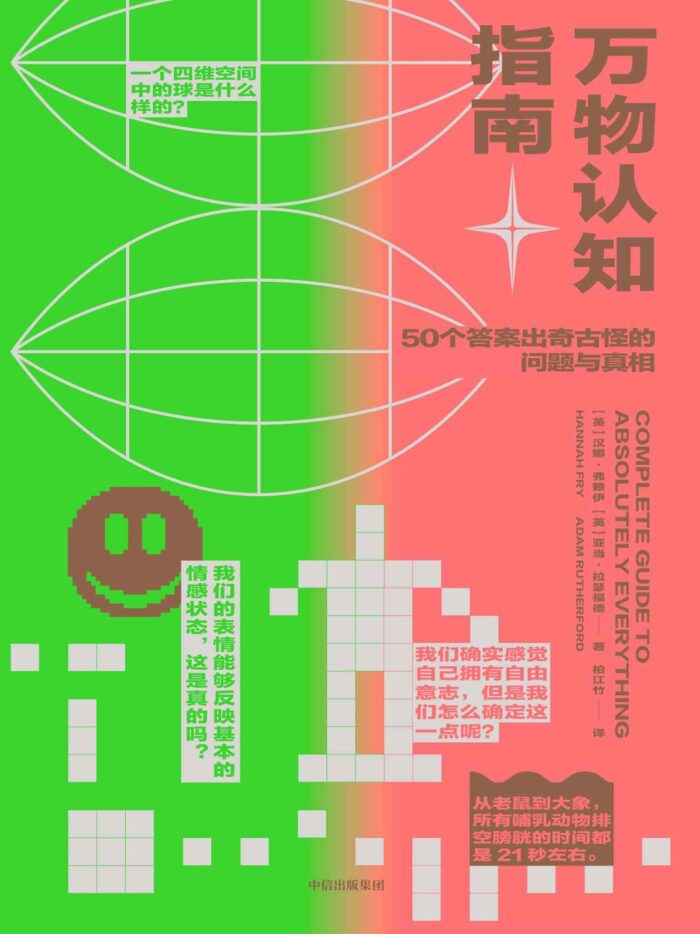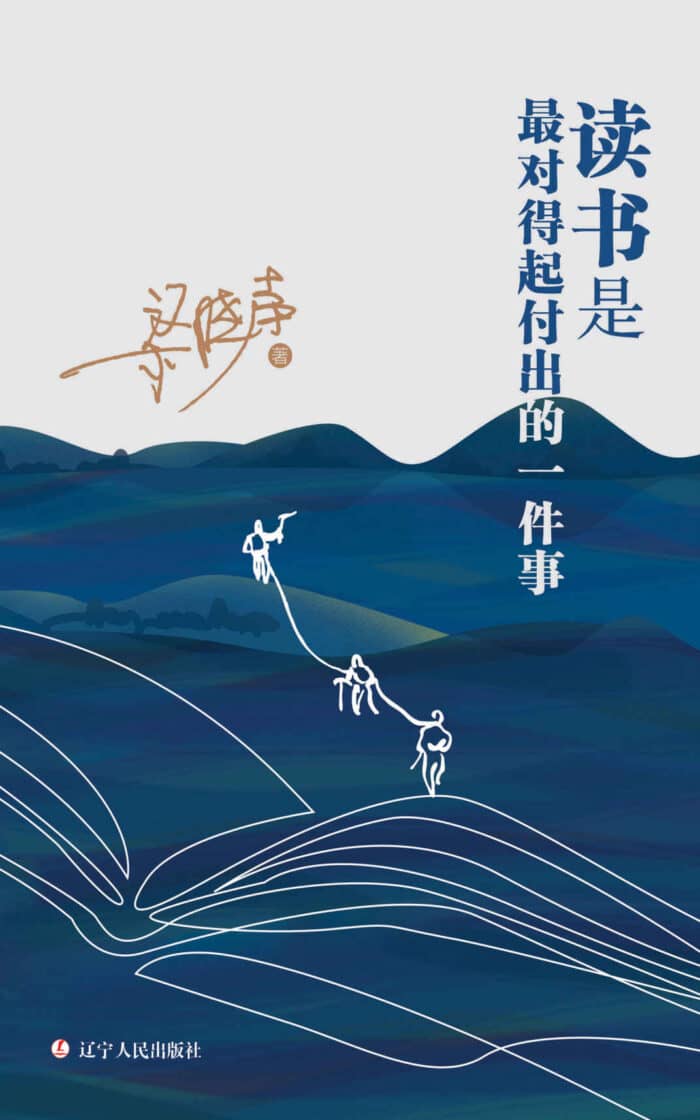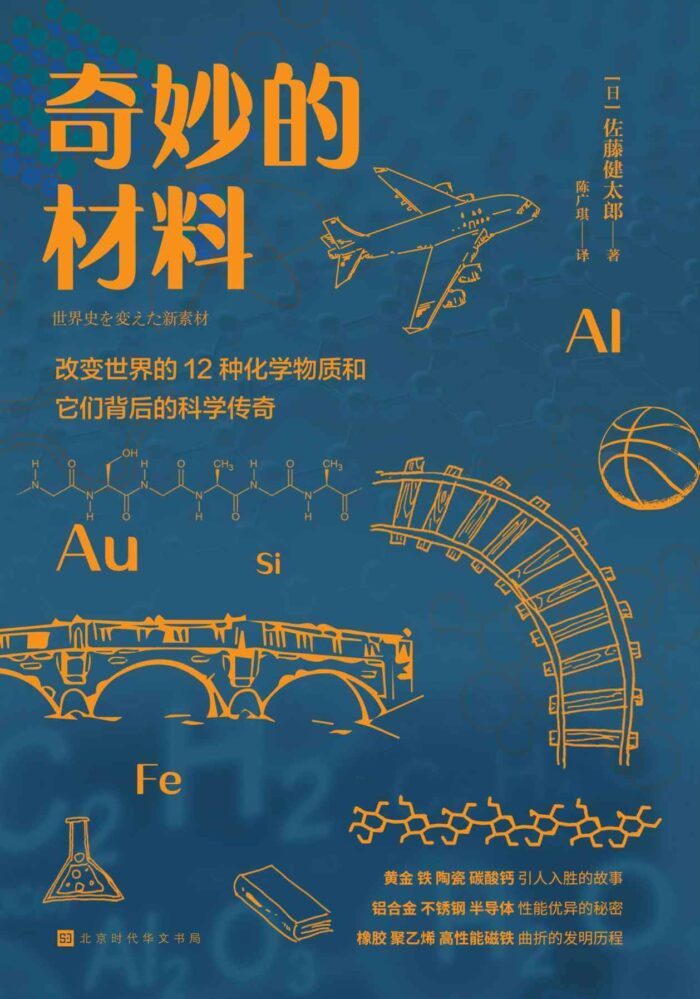内容简介:
麻省理工学院(MIT)开放学习项目(Open Learning)的负责人桑贾伊·萨尔马跨越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发展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探究了学习的真谛,并启发了人们对于未来学习和教育方式的思考。
标准化教育是无懈可击的吗?
临时抱佛脚是好的学习方式吗?
好奇心对学习意味着什么?
如何激活惰性知识?
遗忘是记忆的失败吗?
……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一场“学习的革命”正在悄然兴起。这本研究人类如何学习的科学之书,不仅为学习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对每位教育者来说也是一份及时而珍贵的礼物。想要突破传统教育形式的桎梏,教
作者简介:
桑贾伊•萨尔马拥有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的本科学位,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高级学位,目前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开放学习项目(Open Learning)的负责人。他是机械工程专业的教授,曾在能源和交通、计算几何、计算机辅助设计等领域工作过,并一直是RFID技术的先驱。
卢克·约昆图是一名科学作家,他的作品曾在《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大西洋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年龄实验室担任研究员,研究学习和教育、老龄化和人口变化等问题。
试读:
学习如同一场冒险——任何从这场冒险中幸存下来的人都会告诉你,冒险之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这条冒险之路可能是一个漫长但是能让你受益匪浅的过程,它将改变你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挖掘你深藏的潜力。然而,在重新讲述这一冒险经历时,只有那些胜利者才会赞颂冒险的经过。每一个成功斩获“教育巨龙”的冒险者总会在途中遇到几十个被“教育巨龙”击败的冒险者,横七竖八地躺在附近的洞穴里或沟渠中,怒火中烧,懊悔当初做出冒险的决定。
我在教育冒险的旅程中也遇到过困境,最近的一次不幸发生在我在坎普尔的印度理工学院学习时。直到现在,我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依然记忆犹新,仿佛一部以两倍于标准帧速拍摄的电影,就像彼得·杰克逊拍摄的那部《霍比特人》一样无比生动。
事情发生在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准确地说是发生在大学最后一年的夏天。虽然我进入大学后,学习一直全力以赴,但是不知为何,优异的成绩总与我无缘。最后,就在本该毕业之前,我挂科了一门控件操控课,这可是获得工程学学位的一门必修课。
这意味着我必须要上暑假补习班,这是学校提供给学生的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夏季一般都是雨季。坎普尔的天气不仅热而且潮湿,和我之前生活过的很多地方一样热。宿舍里没有空调,好在小露台上有两扇落地玻璃门。于是,我像其他暑期补习班“幸运”的家伙们一样,把床推到落地门附近,这样至少我的上半身可以偶尔享受一丝微风。我把我的那些日常用品——从家里带来的一箱衣服、几沓书和一堆糖果堆放在脚边——也就是房间的另一端。
一天早上,我八点左右醒来。睡眼蒙眬中,突然感觉房间有点儿不对劲。
更确切地说,是有什么东西正直勾勾地看着我。那东西还长着一口可怕的牙齿。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种从半梦半醒突然过渡到毛骨悚然的经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尝试了。当时我被吓得全身僵硬,只剩一对眼珠在眼眶中惊恐地转来转去,审视着我的造访者。我定睛一看,原来露着尖牙、盯着我看的是一只猕猴。
惊恐过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但为时已晚。我竟然把自己置身于一堆糖果和饥饿的猕猴之间——任何路过的猴子都有可能进来。
在我看来,猴子只有在电视屏幕上时才可爱。现实生活中,它们调皮至极,甚至十分暴力,有的猴子身上还携带狂犬病病毒。我和猴子就这样面对面地对峙了几分钟。我都能想象到我的讣告内容:参加暑假补习班的一名前途无量的学生遇袭身亡。
五年前我上高中时认识的朋友中,恐怕没人能够预料到我的命运会如此不济。当年我和大约7万名同龄人共赴高考的战场(如今这支庞大的队伍已增长到约100万人),我参加了印度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这场考试曾经是且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考试。参加考试的考生中,只有排名前2%(每年根据具体情况会有所浮动)的考生才有机会被印度理工学院录取,这也就意味着,每50个中只有一个胜利者。当考试成绩出来后,我发现我成功跻身全国前500名之列。这让我深深松了一口气。其实我一出生就中了人生的第一张彩票,因为我的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重视学习和独立思考。只是我家境贫寒,因此父母曾明确告诉我,若想出人头地,必先学业有成。看到通告栏中自己的名字后,我意识到我充满希望的冒险之旅就这样启程了。
然而进入大学后,这条冒险之路变得艰难起来。我很难理解我在学校所学的这些抽象课程如何能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以及为什么起作用。这不是教师的错,我的教师都是印度优秀的教授,大部分学生学得都不错。我也并不是没有用心学习,而且我迫切地希望,我现在在学校所学的东西能像童年时学习的那些东西一样毫不费力地进入我的大脑中。
但是有生以来,学习,第一次对我来说变得困难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几乎开始嫉妒起那只在我床尾流口水的猴子来。它只需要沿着宿舍窗户走几圈,看到什么食物就拿走什么。对它而言,我的大学就像一个免费的自助餐厅,摆满了美食,等着它随来随取。学习对于我而言,本应该是这样。我看到我的一些朋友都在努力接受学校所教的知识,但我实在无法强迫自己吃不愿意吃的食物。确切地说,那只猴子比我更适应我的大学生活。
30多年后的今天,我有幸在此向大家汇报,历经教育冒险中最危险的旅程之后,我最终幸存下来了。那只在床尾觊觎我糖果的猕猴最后仓皇而逃,于是整个夏天我就能静下心来强迫自己复习控件操作这门课(还阅读了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的《指环王》系列)。然而,如果我没有第二次学习那门课的机会,或者那年夏天在学业上遇到了其他什么障碍,我可能就会错过之后的教育之旅,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有点儿不寒而栗。
相反,正因为经历了一系列教育冒险,我才拥有了今天特有的地位:不仅自己终身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还成了其他许多人学习路上的领路人。我是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学习项目的负责人,我的工作就是打开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育大门,尽可能让更多人受益。
我所探索的方面并非史无前例。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许多人都雄心勃勃地做过类似尝试,其中不乏天才、幻想家、纪律严明者、反纪律主义者、管理者、哲学家和文学圣人[1]。有些人失败了,有些人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特定学生的教学上取得了成功,有些人眼看着他们的思想几乎传遍世界各地,结果却退缩了。因此,如果说我和我的团队在开放式教育方面的理念是全新的或者与众不同的,也不是没有理由。当然,这一理念不只是来源于我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经历,不谦虚地说,我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另外,这一理念的形成也不完全归因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地方正在创造的变革性新教育技术。毕竟,一个多世纪以来,所谓的改革者们一直过度夸大了教育技术的作用。19世纪末在耶鲁大学教授希伯来语的威廉·雷尼·哈珀认为,美国邮政局才是变革性技术的推动者[2]。他说美国邮政局促进了函授课程的开展:“在数量上比我们在学校和学院的课堂上完成得还要多。”1913年,托马斯·爱迪生对电影技术寄予厚望,认为随着电影的普及,教科书很快就会“过时”。接着收音机得到普及,它“在教室里应该像黑板一样常见”。之后是电视机的大众化,20世纪50年代的技术革新者将电视机称为“21英寸[3]教室”。1961年,《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杂志预测,到1965年将有一半的学生依赖自动“教学机器”满足学习需求。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计算机已一跃成为技术行业的佼佼者。1980年,麻省理工学院教育技术先驱西蒙·派珀特[4]预言,计算机很快就会成为“每个孩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等到了1984年,他又预言“计算机将充斥所有学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自19世纪中叶以来教育领域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变革,但我们大多数人学习所用的教室仍与150年前的教室没有太大差异。
因此,当我思考教育应如何变革时,我发现我的思绪更多地萦绕在我的过去,而不是对未来技术的设想。我的思绪又回到我大学时的宿舍和那只猴子,对猴子来说,标准化教学大楼的物理结构就意味着无限的机会。在我自己的教育冒险旅程中,我逐渐意识到那些如出一辙的教育体系(不只是硬件结构,还有软件体系、教育法规、教育传统、组织结构以及一些不言而喻的规则)都是千篇一律的——它们已不再是我思想的乐园,反而束缚了我的学习能力。有的人遇到的情况比我更糟糕。在我的学习冒险旅程中,学习痛苦的关键时期来得比较晚,再加上家人的大力支持,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比较少,因此我才能侥幸渡过难关。只能说,我是一个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