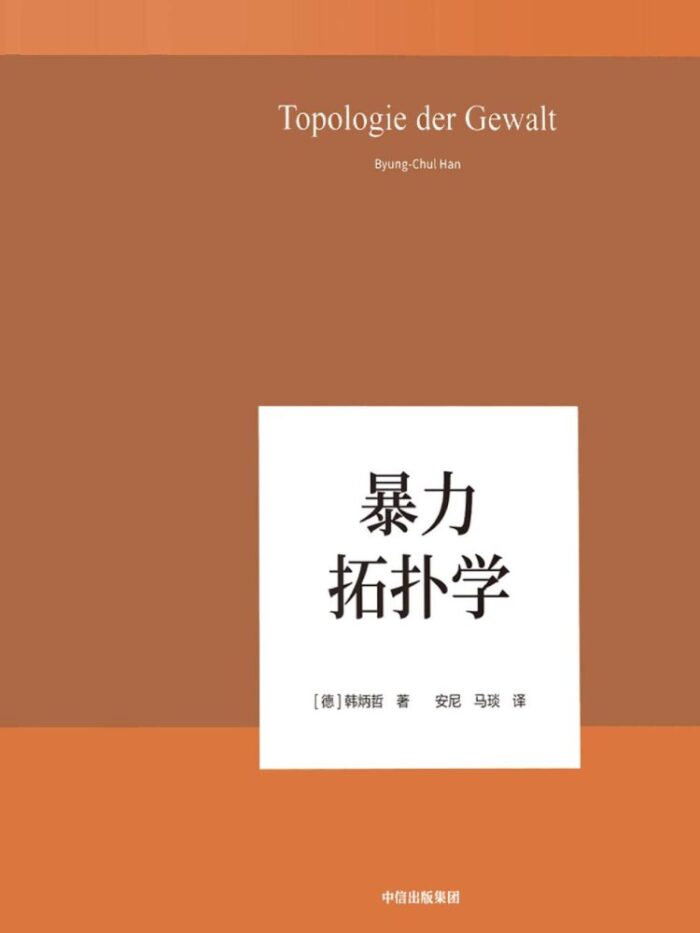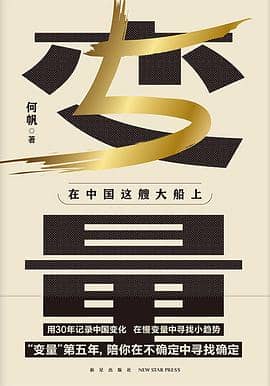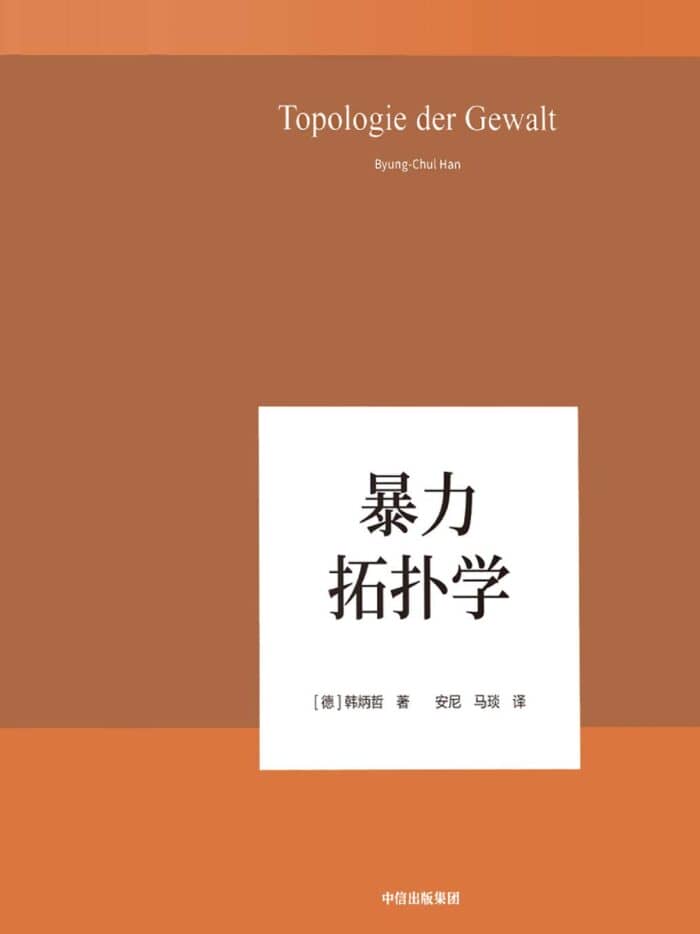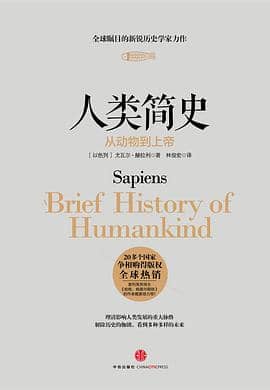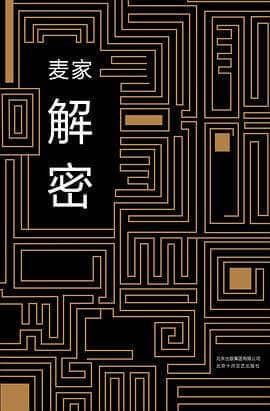内容简介:
标题:妥协社会
副标题:今日之痛
如今,随处可见一种痛苦恐惧症,一种普遍的对痛苦的恐惧。人们对痛苦的忍受度也在迅速下降。痛苦恐惧症导致一种长效麻醉。人们对所有痛苦状况避之不及,甚至连爱情的痛苦也渐渐变得可疑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症也蔓延至社会性事物。冲突和分歧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它们很可能导致令人痛苦的争论。痛苦恐惧症也席卷政治领域。一致之强制和共识之压力与日俱增。政治安守在一个妥协区域,失去一切生机与活力。
妥协社会与功绩社会相伴而生。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苦难的被动性在“能”所支配的主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如今,痛苦被剥夺了所有表达的机会,它被判缄默。
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物化了幸福。幸福绝不仅仅是众多能带来更高绩效的积极情感之总和,它对优化逻辑避之不及,不可用性是其特征。幸福中蕴含着否定性,真正的幸福绝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使幸福免于被物化的恰恰是痛苦。痛苦承载着幸福,使幸福长久。“痛并快乐着”并非矛盾的修辞。
作者简介:
作者:韩炳哲
德国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80年代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远渡重洋到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天主教神学。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弗莱堡大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2010年任教于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2012年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
摘选:
痛苦恐惧症
Algophobie
“告诉我你和痛苦的关系,我就会说出你是谁!”[1]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这句话完全适用于整个社会。我们与痛苦[2]的关系透露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痛苦即密码,它藏有解读当时社会的关键信息。因此,所有社会批判都必须完成对痛苦的一种诠释。如果仅将痛苦归于医学领域,那我们就错失其象征意义了。
如今,随处可见一种痛苦恐惧症,一种普遍的对痛苦的恐惧。人们对痛苦的忍受度也在迅速下降。痛苦恐惧症导致一种长效麻醉。人们对所有痛苦状况避之不及,甚至连爱情的痛苦也渐渐变得可疑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症也蔓延至社会性事物。冲突和分歧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它们很可能导致令人痛苦的争论。痛苦恐惧症也席卷政治领域。一致之强制和共识之压力与日俱增。政治安守在一个妥协[3]区域,失去一切生机与活力。别无选择成为一剂政治止痛药。弥漫的中庸之气治标而不治本。人们不再争辩,不再奋力寻求更好的理据,而屈服于制度强制。一种后民主蔓延开来,这是一种妥协的民主。因此,英国政治哲学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e)呼唤一种“激进的政治”(agonistische Politik),一种不畏惧令人痛苦之争论的政治。[4]妥协的民主无力锐意改革、实现愿景,这些都可能引发痛苦。它宁愿选择短期有效的止痛药,掩盖掉系统性机能障碍与扭曲。这样的政治没有直面痛苦的勇气。如此一来,同者(das Gleiche)便大行其道了。
如今的痛苦恐惧症基于一种范式转变。我们生活在一个试图消除一切否定性的肯定社会。痛苦之否定性却不容置疑。然而,就连心理学也附和这一范式转变,从“苦难心理学”这种消极的心理学,转向研究健康、幸福与乐观主义的“积极心理学”。[5]负面的想法是要避免的,它们必须即刻被正面的想法取代。这种积极心理学甚至让痛苦也臣服于绩效逻辑。新自由主义思想极具复原力,它从创伤经验中为绩效升级制造催化剂。人们甚至谈及“后创伤性增长”。[6]这种复原力训练是一种心灵上的力量训练,企图将人类塑造成对痛苦极不敏感的、永远感到幸福的功绩主体。
积极心理学的幸福使命与承诺用药物创造永乐之地,二者亲如手足。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牵涉其中的绝不仅仅是制药企业物质上的贪婪而已,它更多地是基于一种十分危险的对于人类存在的看法。单凭追求永远健康的意识形态就能导致将原本用于镇痛的药物大量应用于健康人群。美国疼痛学专家大卫·莫里斯(David B.Morris)早在几十年前便洞察此事,这绝非偶然:“如今的美国人或许是地球上第一代将一种无痛的存在奉为金科玉律的人。疼痛即丑闻。”[7]
妥协社会与功绩社会相伴而生。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苦难的被动性在“能”(Können)所支配的主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如今,痛苦被剥夺了所有表达的机会,它被判缄默。妥协社会不允许人们化痛苦为激情,诉痛苦于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