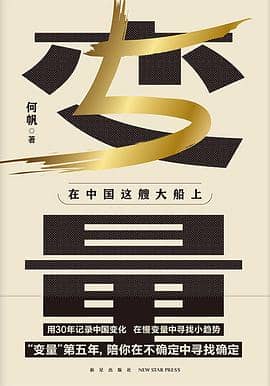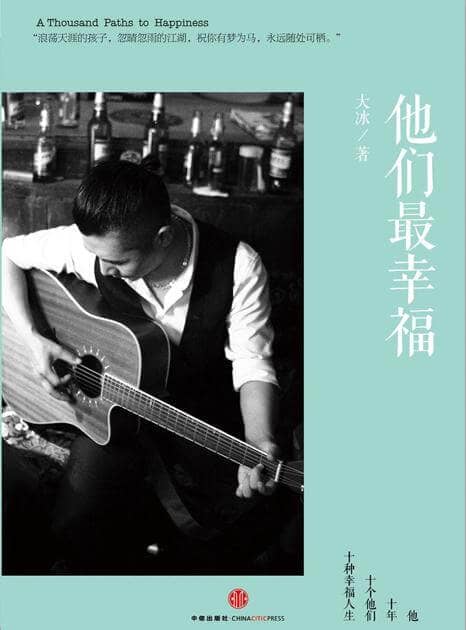内容简介:
《吕思勉国文课》分为六册,以短小精悍的课文讲古诗寓言、历史百科、山川人文,让我们近距离感受中国语文之美。其内容注重“寓教于乐”,用简洁流畅、轻松有趣的文字,启发学生“发表思想之能力”;其取材广阔,涵盖古今中外,包罗自然人文,以达到“授以切于实用之文字”的目的。华东师范大 学程怡教授深入导读,全新注释。
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语羼入,而时有鸿议创论,同学争相推敬。
作者简介:
试读:
2022年,距离吕思勉先生编写《高等小学校用 新式国文教科书》已一百零七年了。
从1916年2月至1924年5月,这套国文教科书各册的重版次数最少的也有四十九版,而第一册居然有七十版之多,足见其影响力之大,使用面之广了。
这套教科书共六册,每一学年两册。从课文的选编、组织上,我们可以看到编者对国文教育的深刻理解。六册国文教材共一百六十六课,吕先生自己编写的课文,竟然有一百二十三篇之多。他为什么要亲自编写,并且用简净、流畅的文言文来写呢?这当然与他对“国文”的定义有关。首先,国文是所谓“在纸上说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可分为古文、普通文与通俗文三类。古文指的是“先秦两汉之书、唐宋八家之文”;普通文“介于古与今之间”,是“承古代之语言而渐变者”,“如近今通行之公牍书札及报章纪事之文”;通俗文指的是“向来通行之白话小说及近人所刊之白话书报”等等。其中最早的古文书籍,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要理解它们,不是三五年有限的国文教育所能完成的任务。吕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书面语习惯于用古文做标准,因此要了解古人的精神、古代的思想和古训,不通文言则绝无可能。当时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其实也都是通文言的人,他们所主张的“名词成语采用文言,句法篇法全用语体”实在是很难实行的。因为上述习惯,数千年来已经使得我们的文言书面语与白话口语之间有了很大的距离,即使是智识之人,也难免“借文言以济口语之穷”。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街头采访,上海人只要一谈到国家大事,就不免上海话与普通话混搭一样。正因为古文难通,又不能全然不通,所以吕先生主张初小的儿童“均宜改用通俗文”做教材,同时统一用“国语”来教,而高小以上程度的国文课则应该肄习“普通文”,上古文的学习,就有待于高等学堂及大学堂了。
吕先生的旧学功底无与伦比,却并不赞成旧时私塾的国文教育,因为那种教育“不切实用”,“其所授,不必求合与天然,而但须取材于纸上”,“其教授,不必求学生之有得,而但恃教师之讲演”;且私塾教育“舍弃各种科学,以日夕从事于呫哔”,“发蒙之初,所以日受四书五经,了无益于知识道德,而转以窒酷其性灵也”。先生说他十一岁的时候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但“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里,只约略知道在东方罢了”。后来知道德国很强大,便找到家里所藏的中国人写的地理书数种,“还找不出德意志的名字,于是有人凭空揣测,说德意志一定就是荷兰”,因为他们知道荷兰一度很强大。私塾教育的不健全闹出的笑话,我小时候也听父亲说过:有人拿到了一个作文题“项羽与拿破仑”,一上来便破题曰:“项王力能举鼎,况拿一破轮乎!”我们听了大笑,父亲更是不知笑过多少回了!这大概是他们那一代人都听到过的笑话吧。如此看来,先生用浅近、平实的文言文来编写当时中国孩童需要了解的各方面的常识,正是他“授以切于实用之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的编撰宗旨的体现。
吕先生编教材的时候是三十三岁,那一年我父亲刚刚出生。后来父亲有没有读到过吕先生编写的这套教科书,已无从知晓。只记得父亲说过他五岁多一点儿就入私塾发蒙,读的全是当时私塾都要读的经典,他说自己半年便能背诵《左传》。为了不挨打,他总是努力背书,由于记性好,他常常被先生夸奖。但放假的日子总比上学的日子开心,玩疯了就会闯祸,闯了祸就会捱母亲的打。父亲十二岁到南昌补习了半年新式小学的数学课程,才考入了当时江西省最好的中学。乡塾与新式学校教育的强烈反差令父亲又惊又喜,他说,生理卫生和植物学等课程所教的常识,都是他闻所未闻的。上新式学校,简直就是从此走进了一个新世界。
吕先生同一时期还编有新式学校初高中的历史、地理、修身等教科书,为了不与其他各科的内容重复,新眼光、新思路对于国文教科书的选材,是必不可少的。吕先生的这套高小国文教科书,从进入高小的第一篇强调教育在“今日文明世界”的意义,到第六册最后一篇讲“国性”与国文的重要关系,真可以说是一个颇具当时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新体系。先生把国文的基础修习放在了一个很高、却又贴近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位置上。
日常生活对于人的童年和成长来说,其影响力远甚于书本知识。我们对家庭、邻里、社会、世界的各种事物、各种关系的认识无不源于我们最初的日常生活。吕先生认为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大的毛病,就在无所用其心,而凡事只会照老样做”。这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创新思维。在第一册的《察理》上下篇中,吕先生以烟草的发明与哥伦布让鸡蛋竖立在桌子上的故事为例,告诉学童,不要因为少见多怪而做出可笑的事情;也不要因为司空见惯,就把别人的大发现、大发明看得稀松平常,转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在第一册教科书里,他还以“盲鱼”为例,说人的头脑是用来思考的,懒得思考的人,就像那种在暗无天日的巨壑中视觉完全退化了的鱼,被强者吞噬是早晚的事情!吕先生认为,对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只有留心观察了、思考了,才能获得真知识。很多年以后,他还常常告诫学生们:“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知书上之所言,即为今日目击之何等事。”他把自己几十年读书、教书的经验,化入了对日常生活的理解,通过简雅洁净的书面语,呈现在他所编写的教材中。例如第一册教科书共三十五课,每篇课文的字数最多不过三百,少的仅一百三十余字。讲的都是日常生活、格物致知的普通道理,文字却既平实,又活泼。如第二课《喻学》用的是寓言手法,通过木与铁的对话,形象有趣地用密集的动词与夸张的动作组合表现了铁成为工具的过程以及铁被锻炼成器的痛苦,文字风格像极了《齐物论》中子游与子綦关于风的那段对话。文字的节奏生动地再现了木与铁的表情,而作者却无一字落在拟人化的表情描写上。第四课《圣迹》一篇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说明文”,作者对孔林空间准确、明晰的描述,使人如临其境,而寥寥几笔对孔林草树的描写,竟透着强烈的文化纵深感。
先生二十二岁到二十三岁时曾任教于溪山小学,对十来岁的男孩子的天性是非常了解的。“寓教于乐”、让儿童在游戏中强健体魄、发展天性的教育主张,也体现在《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编写中。《纸鸢》《钓鱼》读来颇亲切,儿时自己糊风筝、放风筝,自己“敲针作钓钩”、挖蚯蚓作鱼饵的情景犹在眼前。我父亲只会唱屈指可数的几首歌,其中就有放纸鹞的,“正二三月天气好,功课完毕放学早。春风和暖放纸鹞,长线问我爹娘要。爹娘对我微微笑,夸我功课做得好……”如今的孩子也放风筝,但却不是自己制作的了。《运动》那一篇也让我想起父亲会唱的另一首歌,叫《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努力向上跑!暖风吹,太阳照,空气新鲜景致好!你也跑,我也跑!大家一起向上跑!”小时候觉得那调子真难听,歌词也笨,现在却觉得很温馨。《运动》篇的最后一句说:“平野广阔,空气清洁,徜徉其间,心神泰然,实人生至佳之境也。”读着这样的句子,你的呼吸是否也很舒畅呢?
民国以后的新式小学分为两级,前四年为初小,后三年为高小。进入高小的学生年龄一般在十岁左右,正是好奇心、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段,影响孩童一生的选择也在此时开始成型。陈平原谈语文教育的时候说过:“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早年自传中就说自己十四岁时进常州的溪山小学校求学,当时在溪山小学校教国文和历史的吕思勉先生是他最爱戴的老师。有幸亲聆吕先生授课的好几位当代文史大家的回忆,也让我们极为亲切地感受到先生的人格魅力,而我们却只能在先生编写的教科书中,想象先生在国文讲台上的音容笑貌,通过先生的文字表达,感受中国语文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