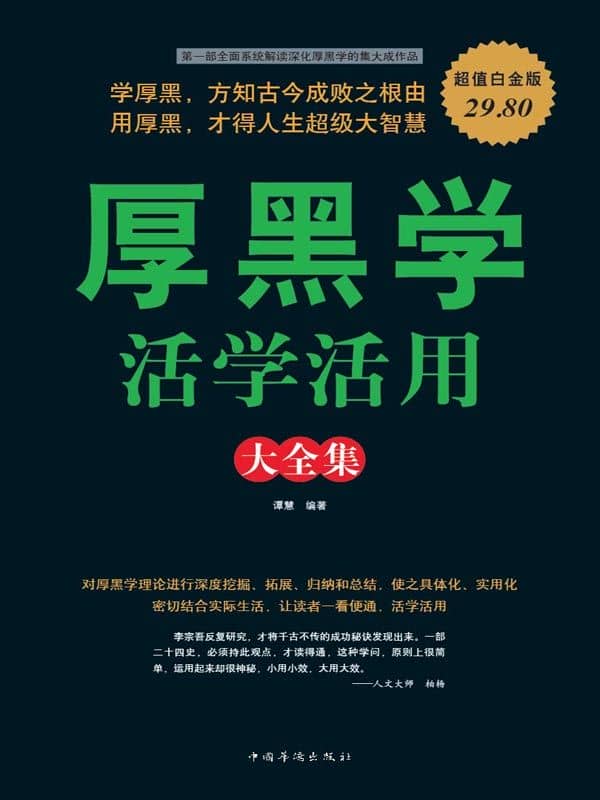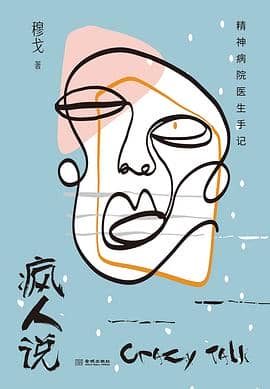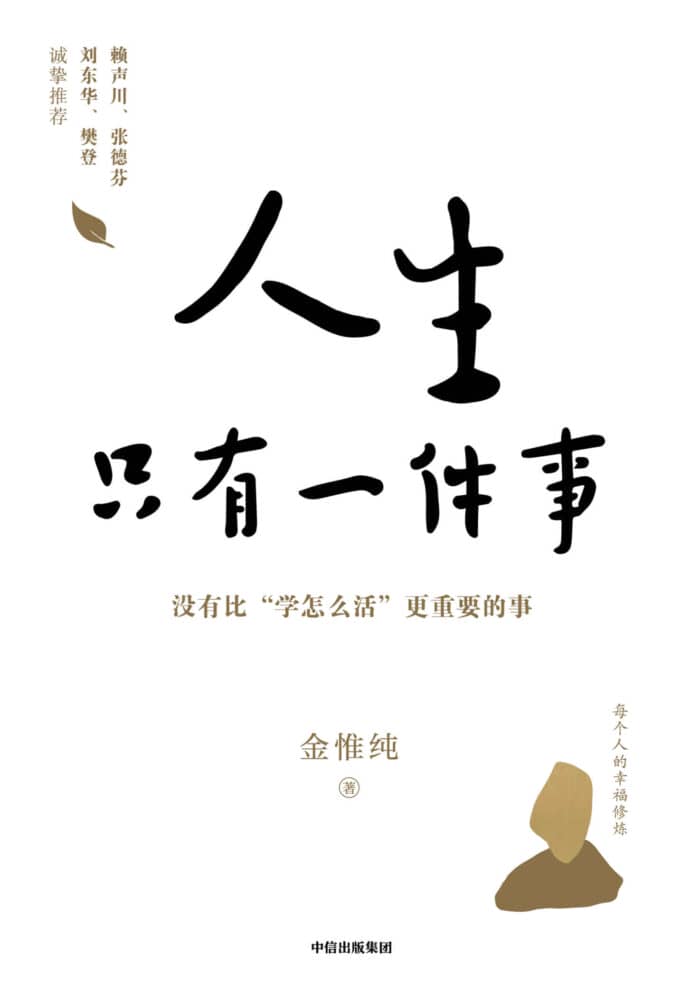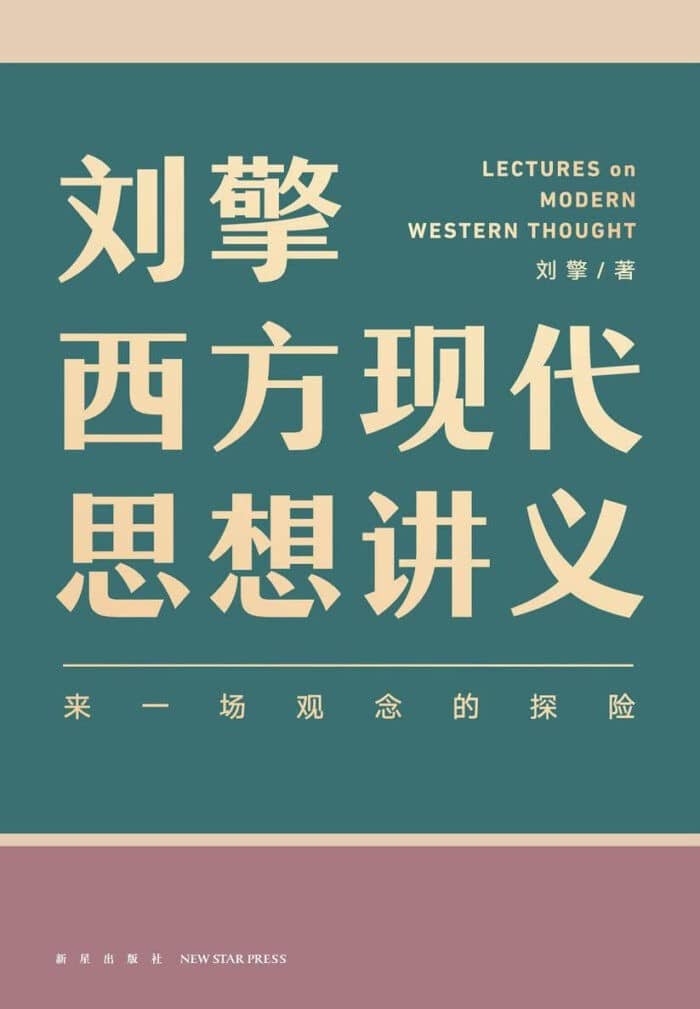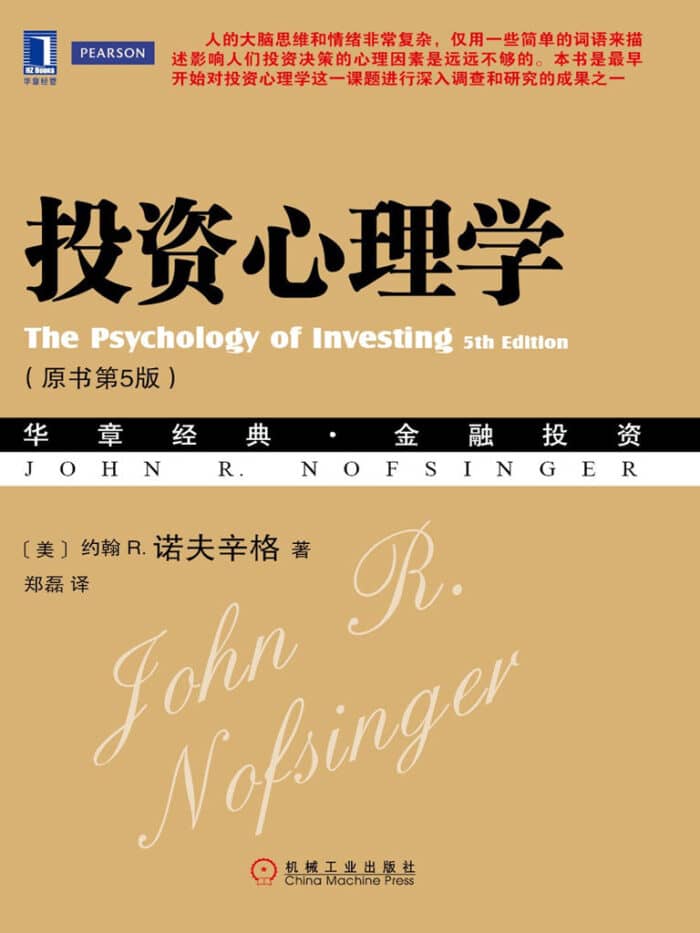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作家、记者。著有《不哭》《逝者如渡渡》《光阴》《一个一个人》《阿尔萨斯的一年》等。先后在《天津日报》《杭州日报》《福州日报》《扬子晚报》《石家庄日报》等十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导演有《龙的重生》(中法合拍)《不哭》《寻梦总统府》等纪录片。曾任南京日报驻法国记者。现为南京日报“申赋渔工作室”主持人。
试读:
自出生起我和家人就生活在熟人社会。我的乡亲都是亲戚或近邻,我们之间有几代人的交情。我们不总是有着和谐与爱,还有误会、争吵甚至打斗,但相互知根知底,从来不结深的仇怨。数百年来,靠着风俗、道理、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得越来越大的村子,虽纠葛重重却相安无事。
故乡,是阡陌交错中的白墙黑瓦,是随风起伏的滚滚麦浪,是落满大地的银杏树叶……人到中年,从家乡去到城市,从中国流浪到万里之外的异国,我在许多地方停留,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如故乡那般让我惬意放松。故乡的人们嗓门高大,乡音浓郁,举止粗鲁,这是何等亲切,却又曾经那么让我憎恨。这些乡下人的标签,让年轻的我羞愧,我使劲地想要摆脱。
十八岁以前,我无法忍受乡间看得见的黯淡前景,尤其不能忍受“要面子”的父亲对我的冷嘲热讽。抱着一去不回头的决绝,我离开了故乡。而今的我,对生活有了更多的体谅。我会为了父亲的面子,为了拜年,甚至仅仅为了某个逝去祖先的冥寿而返乡。更加频繁的返乡,却还是被迅速衰败的乡村震惊了。村里不再有年轻人,甚至没有了孩子。几乎每一次回乡,都见着一座新添的坟茔。伴随人口的凋零,就是一座座老宅的颓败和消失。曾经的田野,一点点被镇子上漫延过来的厂房占领,故乡已不复是故乡。
一浪又一浪的悲哀向我袭来。我发现,故乡是这样的一种存在——你逃离的力气有多大,反弹回去的力量就有多大。然而,回去的路已被时光的杂草湮没,再也寻它不见。
故乡消失了,我们成了没有根的人,如一个个原子,在冰冷的城市中孤独地生存。离开家乡的我们无所依傍,张皇地被城市的繁华所遮盖。周围一张张面孔,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是的,我知道在我的周围,飘荡着一个个和我一样孤独而寂寞的灵魂。我们有着共同的回忆。在我们的回忆中,有那么多曾经生动鲜活的乡亲。我们称他们为木匠、花匠、剃头匠、瓦匠……除了匠人,他们的共同身份是庄稼人。而现在,庄稼人竟然都不见了。
我的回忆只能追溯到一百年前,那是我父亲和祖父所能回忆的上限。他们跟我讲述的人,我曾经见过的那些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了,他们只成了写在家谱上的,短短的一两行字。
然而每个卑微的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那些不为人所知的乡村人物,折射着一百年,尤其是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他们构成了一个时代,他们又被那个时代所淹没。那个时代如此粗糙,却又如此温暖。温暖在,故乡就在。
生活中所需的一切,
曾经就在家前屋后。
那时的日子直接、新鲜,
带着手心的温暖。
那时的人们以情相待,
用心相处。
引子
长江流到江苏高港的时候,拐了一个大弯。从这个弯,向东伸出一条小河,沿河长着很老的银杏树。银杏树领着人们向东二十多公里,便到了长着更多银杏树的申村。
六百年之前,一位名叫申良三的农民,从苏州阊门来到这里,看中了这块沙土洼地,就此落脚。到了1970年,良三公的第十七代子孙,也就是我诞生时,申村已是有着几万人的大村。谁也没想到,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注定要看着这个村子衰亡。
2001年,离家十多年的我,回到申村,第一次看到一座大门紧锁的颓圮的屋子。这是纸扎匠的家。他的坟就在屋后,院子的门被一把锈锁锁着,青瓦的屋顶上长满了杂草。此后,每次回家过年,我都会看到一座又一座被抛弃的,正在荒废着的老屋。
多年在外,对他乡的熟悉胜过故乡的我,忽然感到彻骨的悲凉。我所熟悉的一代人,一个个凋零。这个村庄,很快就将不复存在了。儿时乱跑的旷野,一半已经砌了厂房。当新城镇的钢筋水泥延伸到这里,过去的一切,那个存在了六百多年的申村,可能就像海市蜃楼一样不复存在了。
在申村的时候,那些不复存在的匠人们的脸,一次次地出现,一次次地把我拉回到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年代。
这些匠人们,都是我所熟悉的。都曾是日日相见。每一个人都知根知底。他们来了,又走了。什么痕迹都没留下。他们原先是从古至今代代延续的一环。这个环,到今天,就断了。他们不在了,我的故乡也就真正没有了。我将真正成为流浪在城市里的孤儿。
据说,一个人失明的时间长了,就会忘记他所见过的一切。写下他们,是怕有一天,我会完全忘掉故乡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