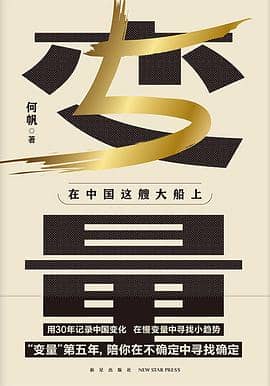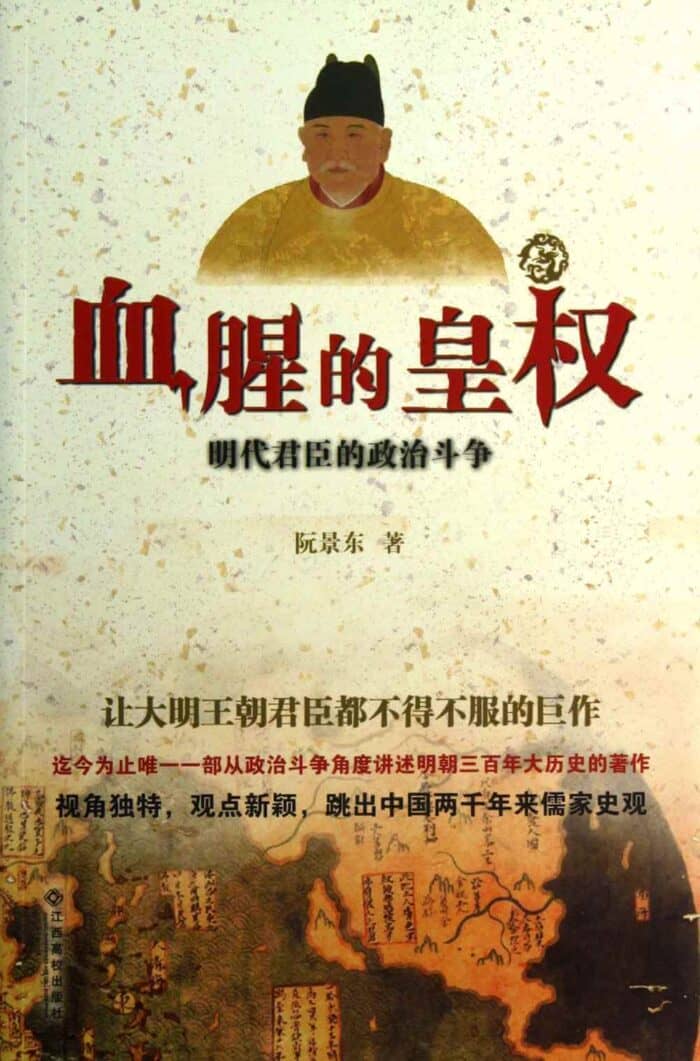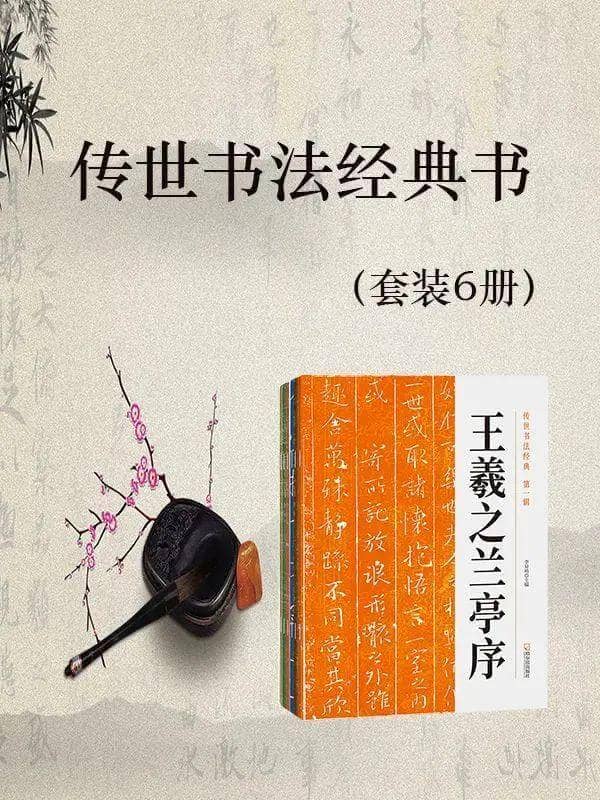内容简介:
试读:
那时我们住在一所租来的房子里,在我的童年岁月里,我们一家住过许多这种地方,这既不是其中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恰恰是在我们搬进这所房子后不久,父亲向我们宣讲了他所谓的“租来的生活”的哲学。他声称不可能有别的生活方式,以为可以选择性地尝试这种生活,这是最糟糕的自欺欺人。“我们必须积极拥抱‘非所有权’的现实,”我母亲、姐姐和我一同坐在租来的房子里一张租来的沙发上听他居高临下、手势沉重的演说,“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们。一切事物都是租来的。我们的脑袋里充满租来的观念,由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不论你的想法最终落脚到哪里,那都是无数其他人的想法落脚并且留下过印记的同一个地方,正如其他人的腰背也在你们现在坐着的这张沙发上留下过印记。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每个外观,每种观点或激情,这一切全都被陌生人的身体和头脑沾染过。虱子——从其他人那儿传来的智力的虱子、身体的虱子——在任何时候都爬满我们全身和周围。这是无可逃避的事实。”
然而,在我们住在这所房子的日子里,我父亲最热衷于逃避的恰恰是这一事实。这是一个虱子格外多的居所,位于一个糟糕的社区,而周边的社区甚至更糟糕。这个地方也略微有点神神鬼鬼的,那几乎是我父亲选择租住地的标准。事实上,我们一年会有好几次打包搬家的经历,并且前后两个居所之间总是相距甚远。每次我们刚刚搬进新租来的房子,父亲都会宣称这是他能够“真正完成某件事”的地方。过后没多久,他就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房子的地下室里,有时会连住几个星期。我们其他人被禁止闯入父亲那个地下王国,除非得到他明确的要求去参加某个项目。大多数时候我是他唯一可用的臣民,因为母亲和姐姐经常外出“旅行”,具体是怎样的旅行,她们回来也对我只字不提。父亲把她们的缺席称作“未知的休假”,以此掩饰他对她们行程的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我说这些,丝毫不是要抱怨自己受到冷落(我也完全不想念我的母亲,以及她那些污染房子空气的欧洲香烟)。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我很擅长找到某些充满激情的方向,让自己过得充实无比,完全不在意自己的激情是不是租来的。
一个深秋的傍晚,我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里,正为出门找乐子做准备,突然听到门铃响了。对我们这家人来说,这堪称非同寻常的事件。那时,我的母亲和姐姐正外出休假,父亲已经多日没出地下室露过面,因此,应付这令人诧异的铃声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搬到这房子里以来我就没听到过门铃响,我也记不起自己在童年的随便哪个出租屋里听到过。(我一直认为,由于某些原因,父亲每次一搬进新家就会把门铃切断。)我犹犹豫豫地挪动身子,希望这不速之客最好在我走到门口之前就离去。门铃又响了。幸运并且难以置信的是,父亲从地下室里冒了出来。我刚好站在楼梯顶上的阴影处,看着他的大块头穿过客厅走向前门,一边脱掉脏兮兮的实验室外套,丢进角落。我自然以为这位访客是父亲正在等待的,也许同他在地下室的工作有关。然而,情况显然并非如此,至少在楼梯顶上偷听到的对话告诉我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