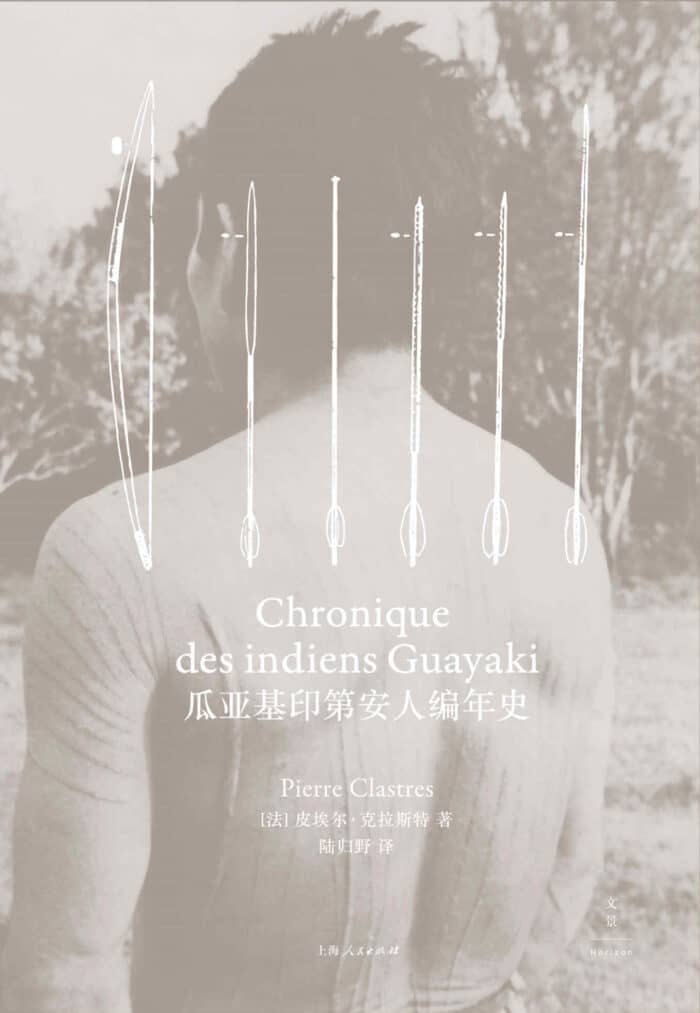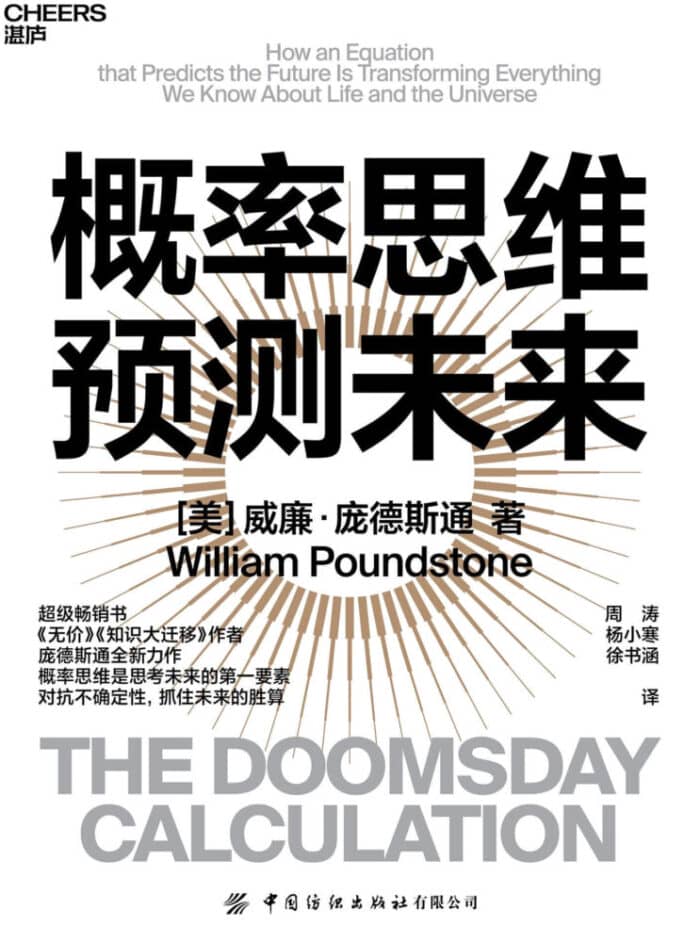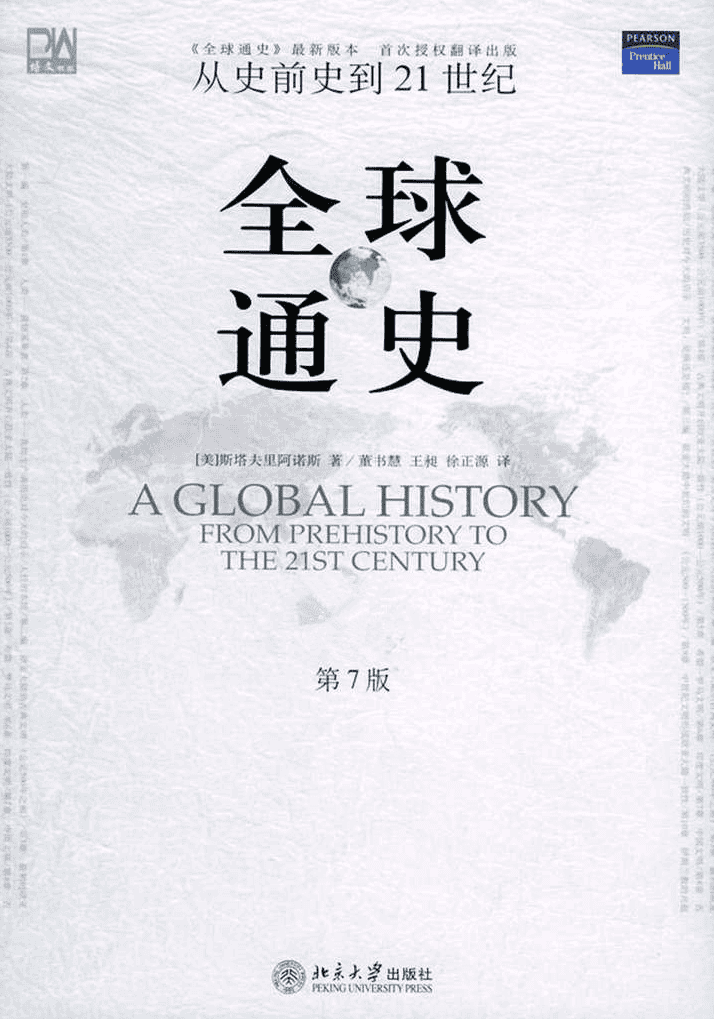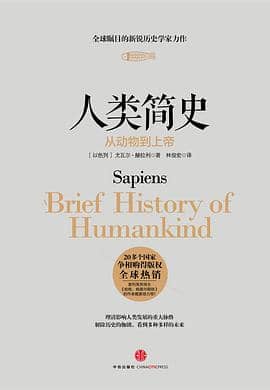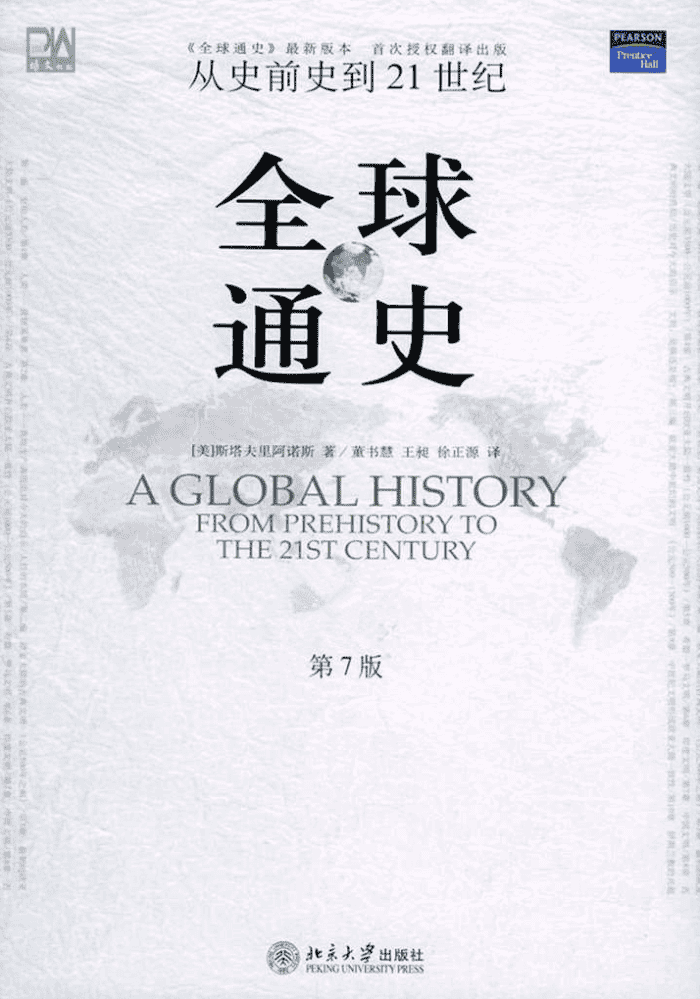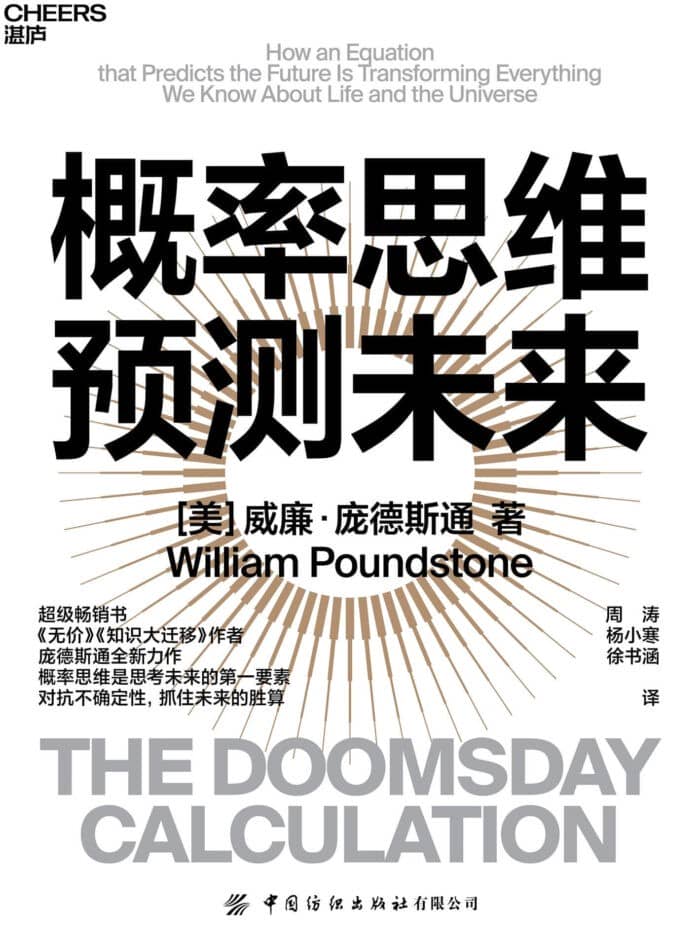内容简介:
我相信,你简直无法不爱上这本书。
作者写作时的慎重与耐心,观察之犀利,其中的幽默,思维之严谨与书中的悲悯——这些 品质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这部重要又令人难忘的著作。这是一个人经历的真实故事,提出的都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一个人类学家是如何得知信息的,两种文化之间会进行什么样的交易,人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守秘密?
在为我们刻画这个未知的文明时,克拉斯特的写作带着优秀小说家的狡黠。他对细节的关注一丝不苟、无比精确;而他那种将自己的思想融汇为胆大又自洽的论点的能力往往令人称奇。他是那种极为少见的、毫不犹豫就采取第一人称写作的学者,而最终的成果不仅仅是一幅他所研究的民族的肖像,也是一幅他本人的自画像。
—— 保罗·奥斯特
--------------------------------------
与南美丛林中最后的食人部落一同生活,见证出生、成年、婚配、死亡、节日、祭祀……
浸入瓜亚基人的生活与头脑,真挚发问:
人类能不能放弃追求一切,告别惶惶不可终日,
拒绝屈服权力,也拒绝过度生产,更从容、自由、坚定地生活,摆脱外部世界的束缚?
--------------------------------------
瓜亚基人,一群生活在巴拉圭密林中的印第安人。他们以打猎、采集为生,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与社会制度。16世纪起,西方殖民者和当地居民一道,不断占领、吞食他们生活的领地,他们躲避、抗争、流亡、被“安置”……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个部落的人口已不足三十。
1963年,本书作者、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在瓜亚基人被安置于定居点后进入了这个部落,与他们一同生活,对他们在生育、死亡、饮食、求偶、部落管理、性向认同、劳动分工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书写。
在书中,克拉斯特直面瓜亚基人的残忍、习俗之状况,以及他们缓慢的衰亡。这是一种充满人情味的民族志书写,情感充溢全篇:克拉斯特于瓜亚基人一同经历了生育、成年、死亡与逃亡;它也是一种客观的民族志,摈弃了一切道德偏见:面对瓜亚基人的吃人风俗,卡拉斯特并没有止步于猎奇与惊叹,而给予他们最大程度的理解。
法国著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面对这部作品,感叹道:“这本奇妙的著作标志了一种新型民族学的开端:它富于感性、积极于行动,又充满政治性;它是‘种族大屠杀’一词彻底的对立面。”
作者简介
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生于1934年。他起先在巴黎进修哲学,随后转攻民族学。他在巴拉圭形形色色的印第安部落中生活了数年,包括瓜亚基部落、瓜拉尼部落,以及大厦谷中的阿什卢斯莱部落。在圣保罗教了一段时间书后,他曾与委内瑞拉境内亚马逊丛林中的亚诺马米人共同生活。此后他返回法国,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担任研究工作。此外,他也是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社会人类学实验室的一员,接受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指导。
作为一名研究者,他致力于从政治人类学方向构建民族学。在与瓜亚基人共同生活后,他出版了《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1972)一书,以无与伦比的精确性观察并描绘了瓜亚基人不起眼的习俗、语言和思想。他与瓜亚基人亲密无间,在潜移默化中,部落中人在举止、思想上与他互相影响,这本书就是最为重要的见证。
在《编年史》外,他还著有《反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 1974)、《壮言》(Le Grand Parler, 1974)、《政治人类学研究》(Recherches d’anthropologie politique, 1980)等书。
皮埃尔·克拉斯特于1977年因车祸去世。
译者介绍
陆归野,1992年生人,长于浙江。书多未曾经我读,事少可以对人言。
试读:
这是我所知的最悲伤的故事之一。如果不是因为时隔二十年后的一次小小的奇迹,我甚至怀疑自己能否鼓起勇气讲述这个故事。
一切始于1972年。我当时正住在巴黎,因为和诗人雅克·杜宾(Jacques Dupin)的私交(我曾翻译过他的作品)而成了《瞬息》(L’Éphémère)杂志的忠实读者,那是一本由玛格画廊(Galerie Maeght)出资的文学杂志。雅克是杂志编委会成员之一,与他共事的还有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安德烈·杜布歇(André du Bouchet)、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以及保罗·策兰(直到策兰在1970年去世)。杂志一年四期;有那么一群人为它的内容把关,《瞬息》中刊载的作品自然向来都是上上之作。
杂志的第二十期,同时也是最后一期在那年春天面世,而在惯常的来自著名诗人与作家的稿件之外,里面还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无众之一》(De l’Un sans le multiple)的文章,出自一位名为皮埃尔·克拉斯特的人类学家之手。短短七页,它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高妙,引人深思,论证严密,不仅如此,文笔也十分优美。克拉斯特的散文似乎同时具备了诗人的气质与哲学家的深刻,文章的直截了当、人情味和毫不做作打动了我。这七页透露出来的笔力让我意识到,刚刚发现的这位作家,我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关注他的作品。
我问雅克这是何方神圣,他向我解释,克拉斯特曾师从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年纪还不到四十,而且是法国新一代人类学家中最被看好的一位。他在南美洲的丛林中进行过田野调查,也曾在巴拉圭和委内瑞拉最原始的石器时代部落中生活,并有一本讲述这些经历的书即将付梓。当《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在不久后出版时,我出门给自己买了一册。
我相信,你简直无法不爱上这本书。作者写作时的慎重与耐心,观察之犀利,其中的幽默,思维之严谨与书中的悲悯——这些品质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这部重要又令人难忘的著作。《编年史》不是干巴巴的、以“在野蛮人中生活”为题的学术研究,也不是一篇记者将自己的身影从其中抹去的关于某个陌生世界的报道。这是一个人经历的真实故事,提出的都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一个人类学家是如何得知信息的,两种文化之间会进行什么样的交易,人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守秘密?在为我们刻画这个未知的文明时,克拉斯特的写作带着优秀小说家的狡黠。他对细节的关注一丝不苟、无比精确;而他那将自己的思想融汇为胆大又自洽的论点的能力往往令人称奇。他是那种极为少见的、毫不犹豫就采取第一人称写作的学者,而最终的成果不仅仅是一幅他所研究的民族的肖像,也是一幅他本人的自画像。
我于1974年夏天搬回纽约,在接下来的数年间试着以翻译为生。那是一段艰难岁月,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勉强糊口度日。因为根本没有挑挑拣拣的余地,我经常得接手一些无甚价值的作品。我想要翻译好书,想要干值得干的活,这可比赚面包钱要紧多了。《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在我书单的第一位,我曾一次又一次向我供稿的各家美国出版社推荐这本书。在无数次被拒之后,总算有人表示了兴趣。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在1975年底或是1976年初,可能有半年左右的误差。不管怎么说,这是家新出版社,刚刚起步,乍一看一切迹象似乎都不错。他们有很优秀的编辑,签下了几本不错的书,也愿意冒险。在那之前不久,克拉斯特和我刚刚开始通信;当我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时,他和我一样激动。
翻译《编年史》对我来说是一次无比愉悦的经历;译稿诞生之后,我对这本书的感情也没有减退半分。我将底稿交给了出版社,他们通过了我的翻译,而正当一切似乎正奔向一个圆满的结局时,问题开始出现了。
似乎,那家出版公司不像世人以为的那样资金充足。更糟糕的是,出版商本人在金钱问题上似乎颇有些不该有的偷鸡摸狗之处。这一点我很确定,因为本来我翻译的稿酬是应该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给出版公司的拨款支付的,但当我向他们索要稿酬时,出版商却顾左右而言他,向我保证届时一定会把钱付到我手上。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已将拨款挪作他用。
那些日子我已经穷得揭不开锅,根本没法干等着稿酬到手。这关系到我是有饭吃还是断粮,付得出还是付不出房租。在接下来的数个星期中,我每天给出版商打电话,可他永远在敷衍,不停想出新说辞搪塞我。终于有一天,再也等不下去的我亲自跑去了他的办公室,要求他当场付钱。他再次找了个借口开场,但这一次我丝毫不肯让步,宣布他若是不给我一张全款支票,就绝不离开。我应该没有做到出言威胁的地步,但说不定也干得出来。我当时怒火中烧,甚至还记得自己想过,万一一切手段都没有奏效,我已经准备好了对着他的脸来上一拳。事情最终没有发展到那个局面,不过我确实把他逼到一个角落里,而那一刻我看得出,他开始害怕了。他终于意识到,我是认真的。于是他当场打开了桌子的抽屉,拿出支票簿,把钱付给了我。
回头想想,这被我看作是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刻之一,是我作为一个人类的职业生涯中无比灰暗的一章,而我的所作所为也毫无值得骄傲之处。但我当时一贫如洗,也完成了工作,所以他们应该付我钱。为了说明那些年过得有多拮据,我就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为例。我从来没有给手稿留过底。我没钱复印译稿,而鉴于我以为稿子交到了靠谱的人手里,世上的唯一一份译稿就是出版商办公室里的那份打印稿。这个事实,这个愚蠢的疏忽,这种赤贫状况下的工作方式日后会回来找我的麻烦。这完全是我的错,而它让一次小小的不走运变成了一场全面爆发的灾难。
但在那个当口,似乎,我们又回到了正轨。在稿酬相关的种种不快得到解决后,那个出版商表现得仿佛他确实很想要把这本书做出来。译稿被交到了排字工人手上,我修改了校样,又把它们交还给了出版社——并再一次没有留底。这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现在出版流程已经启动。这本书出现在了图书预告目录中,预定1977至1978年的冬天就会出版。
然后,就在《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行将面世之前数月,传来了皮埃尔·克拉斯特死于车祸的消息。根据我听到的说法,在法国某地,他在行驶时因轮胎打滑,失控翻下山崖。我们从未见过面。他去世时不过四十三岁,我一直以为日后自有大把见面的机会。我们曾通过数封信,在通信中成了朋友,并且都很期待可以坐下来一起喝茶谈天的那天。世事之吊诡无常让这次谈天无从实现。而即便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后,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1978年来了又去,不见《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出版。又是一年悄然而逝,然后又过了一年,书依然不见踪影。
到了1981年,出版社已是日薄西山,我很难打听到任何消息。就在那年,要不就是第二年,不然就是第三年(这一切已经在我脑子里混作一团),那家公司终于倒了。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书的版权被卖给了另一家出版商。我打了个电话过去,对方告诉我,是的,他们打算把书做出来。又一年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又打了个电话过去,前一年和我通话的那个人已经不在那家公司了。另有一人接了我的电话,他告诉我公司无意出版本书。我想向他们要回我的译稿,但他们没能找到。他们甚至连听都没听过这么份稿子。似乎,我的译稿从未存在过。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事情就这么陷入了僵局。皮埃尔·克拉斯特已经去世,我的译稿也已消失不见,整个计划就这么跌入了遗忘的黑洞之中。去年夏天(1996年),我写完了一部名为《穷途,墨路》(Hand to Mouth)的关于金钱的散文体自传。我本有意将这个故事加入叙事之中(因为我失策没有给译稿留底,因为发生在出版商办公室的那一幕),可等到要提笔时,我丧失了勇气,没能咬咬牙将它落纸成文。我觉得这一切都太悲伤了,讲述这样一个悲惨至极的漫长故事毫无意义。
在我完稿之后两三个月,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在差不多一年前,我受邀前往旧金山,去赫斯特剧院的城市艺术讲座系列露个面。活动定于1996年10月举行,到了日子,我就上了飞机,如约前往旧金山。等到台上的活儿结束之后,我需要坐在大堂里签售。赫斯特是一个客容量很大的剧院,大堂里排起了长队。人们正等着我给他们的书签名——这可真是份价值可疑的荣耀——这时,在人群中,有个人我看着眼熟。那是个我曾经在别处见过一次的年轻人,一个朋友的朋友。这个年轻人恰巧是位狂热的藏书家,一头善于搜寻初版和稀罕玩意的警犬,是那种可以在灰尘遍布的地窖里对着零落的弃书翻上整整一个下午,就为了捡到个小宝贝,还把这种事当成家常便饭的书籍侦探。他微笑了一下,同我握了手,然后把一沓带封皮的校样塞到了我手里。校样有着红色的平装封面,而直到那一刻,我从未见过它的任何复印本。“这是什么?”他说道,“我从没听说过这么本东西。”它就这么出现了,突然间,就在我的手中:我那失踪多年的译稿校样,尚未经过修改。自世事之大者而观之,这或许算不得什么值得让人大惊小怪的事件。但对我而言,从我个人微观的角度来看,万千情绪在一瞬间吞没了我。我拿着这本书,双手开始发颤。我感到晕眩,头脑一片混乱,几乎连话都说不出。
这校样是在一个二手书店的清仓书架上发现的,那个年轻人花了五美元买下了它。现在我望着这校样,饶有兴味地注意到,讽刺的是,封面上宣称的出版日期是1981年4月。对于一部完成于1976或1977年的译作而言,这实在是一次漫长到近乎煎熬的磨难。
如果皮埃尔·克拉斯特今天尚在人世,这本失踪之书的发现将会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斯人已逝,而我在赫斯特剧院感受到的那一阵短暂的、奔涌而出的喜悦和不可置信,如今也已慢慢消散,化作深切而悲伤的哀痛。世界如此堕落,竟这般作弄我们。世界如此堕落,一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贡献的人,竟然如此年轻就已经辞世。
以下,便是我对皮埃尔·克拉斯特的著作《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的翻译。且不论其中描绘的世界早已消逝,作者在1963年至1964年间曾经生活其间的这个小群体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且不论作者本人也已逝去,但他写的书依然与我们同在。亲爱的读者,你的手中正握着这本书——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胜利,是在面对造化弄人的摧枯拉朽时,一次小小的胜利。至少我们可以为之庆幸。至少皮埃尔·克拉斯特的著作流传了下来,而这已聊足慰怀。
保罗·奥斯特
1997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