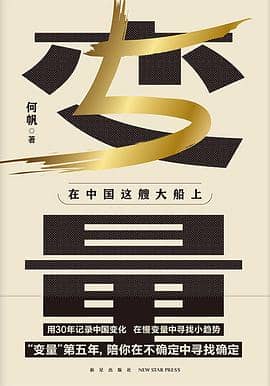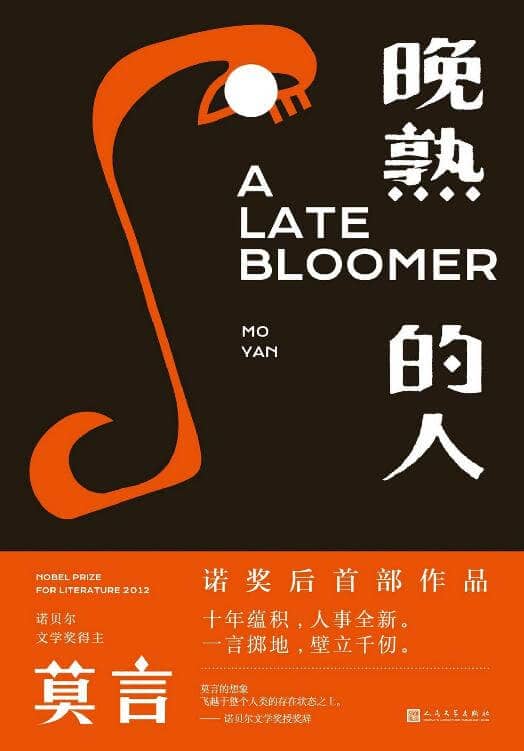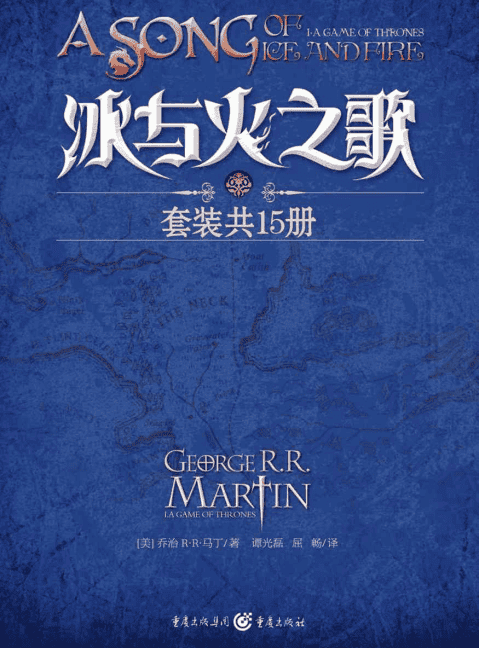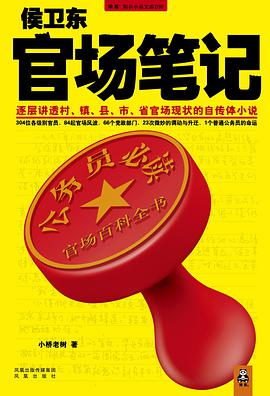内容简介:
你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冷酷的作品?
虽然我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代表作
入选诺贝尔学院“所有时代百部最佳文学作品”
被《泰晤士报》誉为“当今世界最卓越的一部作品”
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卡夫卡的《审判》并驾齐驱。——《柯克斯书评》
萨拉马戈用想象力、同情心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让我们把握到捉摸不定的现实。——诺贝尔颁奖辞
萨拉马戈和马尔克斯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两位作家,但在我看来,萨拉马戈对现实的隐喻更强。——著名作家 苏童
----------------------------------------
繁忙的路口,绿灯亮了,中间车道的头一辆汽车却停止不前,司机在挡风玻璃后面挥舞着手臂,围观的人打开车门之后,才知道他在喊:我瞎了!没有人会相信,他的眼睛清晰明亮,巩膜像瓷器一样洁白致密,然而他却一再绝望地喊着:我瞎了!我瞎了!
一位路人送他回家,却被传染上失明的怪疾。眼科医生成了第三个牺牲品。失明症迅速蔓延,整个城市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作者简介
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
葡萄牙当代最杰出的作家。1922年生于葡萄牙,高中时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先后从事技工、文员、记者、编辑等多种职业。1979年开始投入文学创作。1982年出版的《修道院纪事》为他赢得国际声誉。此后出版《里斯本之围》《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等多部影响深远的小说。1998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葡萄牙迄今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2010年在西班牙兰萨罗特岛去世。
试读:
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陈家琪
应该承认,读这本书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仅有勇气还不够,还要有坚强的神经;而这里所讲的“勇气”与“神经”, 又全都是在一个平常到几乎可笑的意义上而言的,这就是:还好,我没有失明,至少眼下还没有失明。
但真这么确定吗?
“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这就是小说的最后,失而复明的医生与他那一直“没有失明”的妻子的一段对话。
什么算“失明”?什么算“盲人”?什么叫“复活”?什么又叫“再生”?医生的妻子,这位在所有的人都失明后仍能看得见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的“唯一女性”,为 什么当大家复明后坚持要把“失明”与“盲人”、“复活”与“再生”区分开来?
199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只有两本书译成了中文,即《修道院记事》和这本《失明症漫记》,译者均为中国国际广播台葡萄牙语部译审范维信先生。
人类的苦难无疑是萨拉马戈永恒的主题,而在这一主题中,人类的灵魂是如何遭受败坏的又是他的着眼点。他是着眼 于灵魂来处理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关系的。
“着眼”,首先得能看见,于是眼睛或视力的好坏也就成了一个问题;而所谓的高明者,无非是看到了别人所未看到的东西。一旦涉及灵魂的败坏,能否看到的问题也就成了一个是否具有自我审视的能力问题,或者说,这种自我审视的能力是如何遭受败坏的呢?
《修道院纪事》里的另一位同样也把“失明”与“盲人” 区分开来的“唯一女性”叫布里蒙达。(附带说一句,也许在萨拉马戈看来,只有女性才可能具有某种非凡的洞察力,所以他的《失明症漫记》才专门题献给他的妻子与女儿。)布里蒙达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闭着眼睛吃东西,不吃东西不敢睁 眼,因为一睁眼就能看见一般人都看不见的东西,这首先指的是人体的内部器官,如内脏、骨头、肌肉等等。所以在未进食的情况下,布里蒙达尽量不看,什么都不看;万一手边找不到可吃的东西,她就要让她所钟爱的断臂人巴尔塔萨尔走在她后面,为的是避免看到他(的内部),因为“人们的内部比外表更加一样”,也更加不堪人目。(该书第十一章)除了能看到人体的内部结构外,布里蒙达还能看到人的意志,“胸口一团类似于密云”的东西。
有一样东西是布里蒙达所看不到的,这就是思想。思想是某种用概念图式与表达系统所构成的东西,它也可以理解为想法,总之是一种内心的活动,大约对人类被败坏的灵魂而言的所有阴险、恶毒、残忍的东西也都可归为某种想法;从想法到意志,涉及精神与肉体间的关系。布里蒙达虽然知道“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通向肉体”(该书第九章),也能看到意志支配下的肉体的行为,但就是看不到“看不到的思想”是如何转变为“可看到的”肉体的行为的。这也是一直困扰着萨拉马 戈的一个问题,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从为什么要修造那样庞大的一个马芙拉修道院到失明后的人们何以生存。《修道院纪事》中的布里蒙达区分了“看”与“望”,认为只“望”不“看”的人是另一意义上的瞎子 (该书第八章《失明症漫记》(1995)中的医生的妻子则在巨大的灾难中进一步认清了“理性的盲目”(因盲目而失明,)与“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因拒绝而视而不见)
1997年3月12日,萨拉马戈来北京在《修道院纪事》的中文版发行仪式上曾说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以一种想法为基础的,所以他每写一本书,首要的是确定书名,“也就是说,是以书名中蕴涵的某种思想为出发点去写这本书,去解决我所面临的问题;换句话,我写的每一本书都希望能解决我与世界与 他人的关系中面临的一个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主题先行” 的创作思路,问题只在于你所看到的是什么层次上的主题。他说,“我以为,包括作家在内的当今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成为评论员,无论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如此。是把矛头对准其所置身的时代的评论员,原因是,尽管今天的年代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但总是有必要以批判的方式看待之。”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以及他周围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首先体现着一种精神运动的方向,一个“社会可以更公正,而不只有金钱”的方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奇怪或不奇怪的地方在于不仅他的思维方式是基督教式的,而且谈论最多的也就是上帝。正是上帝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生活 与意识,当然也正是上帝才给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相信 “再坏,总还有一丝希望”,“无论如何,爱总是可能的”。也许萨拉马戈先生不认为这种“希望”与“爱”和上帝有关,他也可以就如找到有别于“复活”的“再生”一样找到一些别的词语来表达非宗教意义上的希望与爱,但到底什么才是思想(想法)中的“善”(希望与爱)的“根据”(依托、起源),什么又是未被败坏的灵魂和“再生”后的“新人”呢?我们当然关心的不是萨拉马戈先生的论证,而是他的叙事,是他所讲给我们的故事(他显然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高手)和讲述方式中所蕴涵的寓意。比如《失明症漫记》中的所有人物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其实也就本无“自己”可言,放给谁,在那种境况下都一样,这是一个毫无任何主体的确定性可言的世界,有的只是声音,这些声音作为话语没有引号、问号、感叹号,从声音中也辨别不出性别、年龄、地位的差异,“结果就产生出一种中性的、光秃秃的、脱离任何支撑、任何主体的话语;这 种无法记忆的话语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超越时代,从不固定下来(‘有一天她谈到另一件事,句子没说完,有人会将句子说下去,但不知何时和为什么。又另一个人再往后会把句子说完的,但在什么地方,目前暂且只说是有一天’)死人和活人的声音,真与假的声音,也就这样难解难分的混杂在一起。” 对人来说,最深或最厚的东西就是皮肤,因为它把人分割成内外两个世界。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所在。萨拉马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位回归欧洲“以思想为基础”的文学传统的现代派大师;说是“回归” “思想的传统”并不确切,因为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只能在童话式的寓意中加以接近的东西,它永远处于梦幻与现实、历史与虚构之间,就如“现实”或“历史” 一样, 只能在充满想象力、同情心和讽刺的寓意中才可变得易于理解 (这是瑞典文学院给萨拉马戈的授奖词);说是“现代派大师”,是因为他向“真实性”发起挑战,“使自由的种种可能成倍增加”。作为一个思想者,他想要人们看到内外两个世界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作家,他又只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感性(依赖于但也可能穿透皮肤)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被听觉、视觉、味觉、气息、忧郁、忘记、想象混合而成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什么都是可能的,什么也都可以被说成是另外的样子。 使这样一个感性的世界得以成立的可能就建立在想象力与逻辑的力量之上,在想象中体现逻辑的力量,或在逻辑中给想象开辟无尽的空间,这就是萨拉马戈作品独具风格的魅力。
他的《石筏》(1986)假想欧洲大陆沿比利牛斯山裂开,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便脱离了欧洲大陆在大西洋上漂浮,宛如一块巨大的“石筏”,既有可能与附近的一系列群岛(如亚速尔群岛)相撞,也有可能寻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宿(与南美洲重 新结合在一起)。可以对这种合逻辑的想象所蕴涵的寓意进行各种猜测(如反对欧洲的一体化方案等等),但作者显然更关心的是“石筏”漂浮过程中人们的作为,关心的是一切看起来 被固定下来的东西其实都有另外的可能。他的《耶酥基督眼中的福音书》(1992)和《所有的名字》(1997)也都贯穿着同样的意图,他要给人以想象的勇气,因为“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一塌糊涂”一这句话是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的一个基本观点。
而在想象中把这种逻辑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就是这本《失明症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