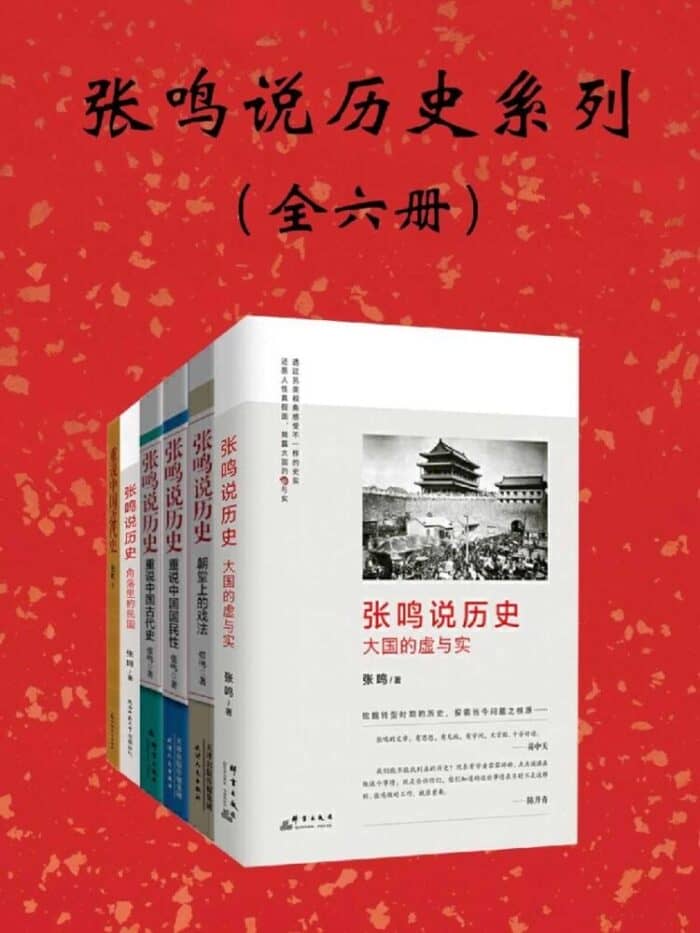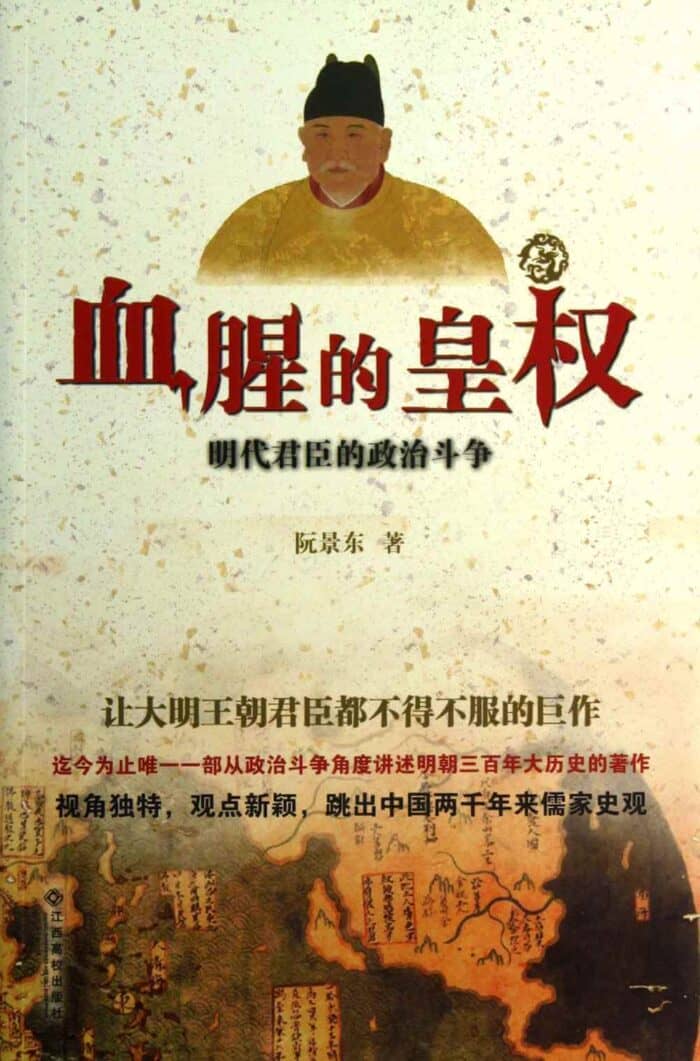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杨渡,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市,诗人、作家、媒体人。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曾出版过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及传记作品《南方》《漂流万里》《民间的力量》《红云:严秀峰传》等十数种。2016年推出简体版作品《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被评为年度十大“华文好书”之一。
试读:
推荐序 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
《在台湾发现历史》给人的“温度”
张作锦
历史书里常有很多仇恨。
但咎不在历史,仇恨在人心里。
因此,解恨在人。
怎样解恨?杨渡以台湾为例,力陈以大历史的悲悯回望过往,益以宽容与理解,历史本身就会有感动人的力量。所以他在自己的新书《在台湾发现历史》伊始便说这是“有温度感的台湾史”。正像钱穆一九四〇年在他《国史大纲》首页要求读者的,应对其本国历史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
必须有钱穆所要求的“温情”,才能探知杨渡的“温度感”。
台湾史难写,因为它的发展轨迹铺满了惊险,也伴随了苦难。自十六世纪第一波全球化的大航海时代,荷兰和西班牙人就觊觎和掠夺台湾的资源。台湾的生态改变了,台湾先住民的生存环境也改变了。再经明郑、清朝收入版图、甲午后日本殖民五十年,中国抗日胜利光复台湾,一个因久战而百孔千疮的国民政府,来接收一个相对初步现代化了的台湾,再加上大批新移民追随而来,于是衍生了许多政治、文化、社会的扞格与冲突的台湾,终于走到旧貌换新颜的今天。
要想解决问题,先要找出问题,不避讳问题。“国者人之积也”,生活在台湾岛上的人被分化了,这是台湾当前最根本和危险的困难所在。
很多人自认他们是“本土”,那么“非本土”即有“非我族类”之嫌。但杨渡问:“什么是本土?”
杨渡把台湾移民史划分成七大波段,这些大量的移民构成今天“台湾人”的主体。如果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撤退移民来台的人,已经在台湾生下第四代儿孙,都不能称为台湾人,那什么叫“台湾人”?
早自荷兰、西班牙,以及后来郑成功、清朝、日本、国民党、民进党,全部都是“外来政权”。如果“外来政权”应该退出台湾,这样的台湾还剩下什么?
杨渡认为,划分这些界限的人,多只为从中攫取政治利益。
台湾族群形成隔阂,“二二八”是个主要分界线。历年来,有人想把它弭平;另有人则把它作为一个发酵桶,不时搬起来摇晃一下,让它不得安息。所以在书中,杨渡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最直接,最坦诚,也最彻底。十篇文章,有三篇讨论“二二八”。这桩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因缉私卖烟而引发的不幸事件,女主角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当时在妈妈身边。她明确还原了当时的现场景况,那是一连串巧合造成的悲剧。但悲剧中也有十分“戏剧性”的“喜剧”,林明珠后来嫁给了陈诚的侍卫队长,两人生儿育女,恩恩爱爱地过了一辈子。
这故事具体代表了“和解”与“宽容”,正是杨渡全书的主调。“我们将因为包容,所以开创;因为开创,所以壮大;因为壮大,所以本土才有生命力。”
杨渡这本书,是集结他过去发表过的十篇长文而成的,这些文章脉络一贯,表里如一,虽然有的文章写于多年前,但理仍在,气仍在,对讨论台湾病理核心问题所谓“本土意识”,依然是有用的参考处方。而且,可去胸中“寒气”,使人有“温度感”。
在台湾这些年来的政治氛围里,杨渡写这些文章,出这本书,是要有些道德勇气的。在有些人的眼里,他是“本土人”,应有“本土意识”,他的言论,或可目为离经叛道的政治不正确。
杨渡写的是“台湾历史”,这叫我想起一则“历史”故事: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关山万里,国脉民命,前途多艰。当时中国最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之一龚自珍,给林则徐建言,指出困难所在,并一一试为解答。林则徐途中复谢,誉之为“非谋识宏远者所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
谋识宏远属知识层面,关注深切则是道德层面。后者尤为难得,此杨渡之书所以使人有“温度感”也。
(张作锦,曾任《联合报》总编辑/社长)
自序 有温度感的台湾史
一
一九八三年秋天,阳明山上阳光灿烂,下午的山风开始有微微的凉意。
我在图书馆里,把古老的《台湾民报》找出来,一大本一大本地抱着,到窗户边的桌子上,就着斜斜的光,一张一张地翻阅,一页一页地寻找,所有与文化活动、戏剧表演有关的报导,都不放过。
报纸是如此的老旧,蒙着浓浓的一层灰尘。在窗户边的桌子上,老报纸翻开的瞬间,那些夹在内页里,沉埋了几十年的灰尘都飘了起来,一粒一粒,晶晶莹莹,像许多记忆的精灵,在空气中飞舞。
古老的印刷字体,虽然被时间沉积得有些苍黄,微微模糊,依旧可以辨认。
……且时间迫切,又降雨连绵,不得已演剧终止,而变易为文化讲演,以免辜负民众之热诚,是夜虽大雨,而听众不下千人,其热心可嘉也。
翌夜七时起在妈祖宫内开该地有志者大恳亲会,定刻,会员不论何种职业,冒雨纷纷而来会者不下千人,着席后,先由陈煌氏叙礼,次会员五分间演说,来宾演说,余兴有奏乐文化剧(彰化留学生文化剧团一行)第一出演《社会阶级》,第二出演《良心的恋爱》,至十二时,剧毕,由周天启氏代表一行述谢,连太空氏吟诗以为告别,最后郭戊已氏述文化剧之精神为闭会辞。当演剧中有柳川巡查部长正式临监,而无持详细之脚本,对照取缔,亦能得平稳通过,可见当道之刁难证据充分也。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台湾民报》
即使隔了六十年的时空,那时代的反抗热情仍动人心弦:至十二时还未曾休息的演讲会,在纷纷雨中观看文化剧而不愿离去的上千双眼睛,如晶莹之光,在阳明山秋日的空中飞舞。
一九八三年的台湾,台湾史研究依然是禁忌,我想做的“日据时期台湾戏剧运动”,只能靠着有限的资料,甚至从旧报纸中,拼拼凑凑,把无政府主义运动、黑色青年联盟 (1) 、张维贤 (2) 、张深切 (3) 等人的作品与行迹,依照时间,慢慢联结,构成一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台湾社会与文化运动的形貌。
从秋天到冬天,整个过程虽然很艰辛,资料也难寻又敏感,但重新看见历史而展开的视野,寻找到台湾文化人心灵的知心感,以及了解自己的父祖之辈曾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曾参与如此深沉而壮烈的反抗运动,曾和日本的、世界的社会运动合流,一起脉动,那种看见而且触摸到父祖心灵的感觉,让我常常独自徘徊在阳明山的冬雨中,感到一种既温暖又孤独的欢喜。
然而,麻烦也来了。我找不到指导教授。研究历史的学者是有的,但他们不知道戏剧运动要如何着手;研究戏剧的学者是有的,但以传统戏曲为主,与社会运动结合的戏剧研究,实未曾有过。几度碰壁后,终于有一位老师指点我说,有此开创气魄的学者,可能只有曾永义 (4) 老师。所幸,在曾永义老师的指导下,我顺利通过论文和口试。
我知道有些什么温暖的情感正在失落,永远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