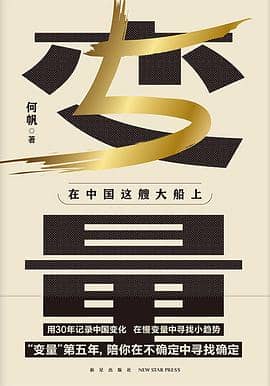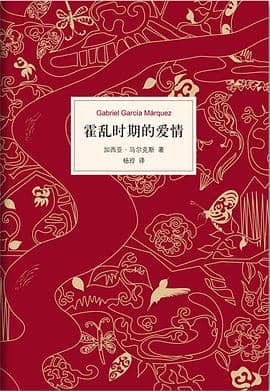内容简介:
奎妮的情歌
the love song of miss queenie
在《一个人的朝圣》里,65岁的哈罗德,87天行走627英里,只为了一个信念:只要他在走,奎妮就会活下来。
这是故事的另一面,这是奎妮,这里有一个埋藏了20年的秘密,有生命中无数的微小瞬间,有温暖的大手,坐在车里的对话,海上的花园。如何处理痛苦,如何爱,如何休息和放松,如何相处,“因为同一样东西发笑也可以是另一种在一起的方式”。当哈罗德开始旅程的同时,奎妮的旅程也开始了。他们因此各自变得完整。
★触动万千读者的欧洲首席畅销书、布克文学奖入围作品《一个人的朝圣》相伴之作。全系列简体中文销量超过300万册!
我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朝圣》的续集,也不是一部前传。我写的这一本书,它和哈罗德•弗莱比肩而坐。我会把这本书称为,一个伴儿。
作者简介
蕾秋•乔伊斯:英国畅销书作家、BBC资深剧作家,2012年出版小说《一个人的朝圣》,入围当年布克文学奖及英联邦书奖,目前已畅销近四十个国家,全球销量近800万册。乔伊斯也凭此书获得当年英国图书奖“年度作家”,并在2014年入围“英国年度作家”短名单。之后,乔伊斯相继出版《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一个人的朝圣2:奎妮的情歌》,以及《奇迹唱片行》《一千亿种生活》等。
试读:
哈罗德·弗莱的亲爱朋友:
《一个人的朝圣》首次出版时,有几个人问过我,会不会写一部续集。我很快向他们保证,不会的。我觉得关于哈罗德和莫琳,该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说了,是时候让他们继续生活了,我不该在一旁观看记录。我没有考虑到的人是哈罗德的朋友——奎妮·轩尼斯:是她写了第一封信,启发了一段改变哈罗德·弗莱人生的步行之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她一直保持沉默(这正是奎妮会做的事情),然后突然有一天,她一声大喊:“我在这儿哪!”
时机不对。我的新书已经写了两万字,还在做一个广播节目。这个时候,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去开始写别的东西。但后来,我和我的孩子们待在厨房里时,奎妮的故事悄然来到。它是那种灵光乍现的想法,但出现时一切就绪,于是你感觉它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告诉了孩子们,因为这个想法已经让我非常兴奋,没法憋在心里。然后,孩子们说了句“哦,很好啊,那午饭吃什么?”之类的话。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脑子里全是奎妮的话以及她的故事。我不知道那些话里有没有哪句有意义,但我确凿地知道,我已经开启了什么东西的头,得继续留下,找出完整的故事。早晨再次翻阅《一个人的朝圣》时,我突然想起,实际上很久以前,我已经有了这个念头,要写出奎妮视角的故事——我已经尝试用她的声音写过一小段,就在《奎妮与礼物》那一章。我有过这一念头,但没有好好看到它。
过去的几年里,关于哈罗德·弗莱,我讲了很多。但有时人们也向我问起奎妮。我承认有几个读者问过,为什么?为什么非得让奎妮得那种毁容的癌症?我一直尽可能温柔地解释,但对于我来说,它还是一个情绪化的回答——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自己必须忠于事实。但以此作答,也同样困扰着我,因为尽管我父亲的癌症到最后可怕得难以直视,那毕竟不是他。比如,当我现在想起他时,我想到的是得癌症之前的那个是我父亲的男人。我想到他的大笑,他在喊“你好吗,蕾秋?”,或是他搬着梯子走过窗前。奎妮也是一样。在成为书的结尾处我们在一间疗养院里发现的那个女人之前,她也有过声音,有过人生。我想找出所有那些。当奎妮从她自己的视角复述这个故事时,她从不使用“癌症”这个词,也几乎不提她的外貌。癌症不是她的旅程。她的旅程是一段修复之旅。通过讲述她的故事,她变得完整。
我的父亲在家中过世。他没有痛苦。所以为了写这本书,我和几位麦克米伦癌症慈善机构的护士相处了一段时间,并拜访了两间收容绝症晚期病人的疗养院。去之前我很担心。我会不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会不会被吓到?我会不会出洋相然后大哭?但在两间疗养院和护士们的身上,我却被其内在的生命力所震撼。喜悦。安乐院里光线通明,充满欢笑。我遇到的护士们有无穷无尽的搞笑故事可讲。于是我开始着手写一本书,关于充满生命力的死亡。在我看来,你似乎没法真正记叙二者之一,而回避另一个,就好像如果你不去面对悲伤,就没法真正记叙快乐一样。我想,正是通过观看一件事的全貌,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质。
在疗养院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事。也聊到我的父亲和他的死亡。在一次会面的最后,一位管理人员对我说,你得写这本书。我很可能哭了——因为那一天有很多情绪。但我之所以哭,还因为他是对的。
于是我创作了我自己的疗养院,圣伯纳丁。几个病人到位了,一开始在我脑海里还很模糊,但随着我的书写,他们逐渐有了色彩和形体。你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像是变成了奎妮的伴唱,她的和声。照顾这些病人的修女们的灵感则来源于一个修女团体,她们住在我们格洛斯特郡的村里,共有七人。我们第一次过来看房子时,我见到了其中一位——一个穿着乳白色长袍和黑色围裙走在大地上的身影——那幅画面有种格外祥和的感觉,以至于这些修女立刻成为我在这片住地的一部分经验。就在昨天,我打开大门取车,发现一个修女靠在我们花园的围墙上。她似乎在等待什么,也可能就是在擤鼻涕。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她当时都很惬意。
为了找到奎妮的家,她的海边小屋,我和丈夫孩子回到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参观了诺森伯兰郡绝佳的海岸线。我又回去过两次。直到最后一次参观——就在我提交手稿之前的那个周末,我们又走了一趟,才发现恩布尔顿湾以及悬崖上的海滨木屋。奎妮的小屋是我在头脑里创造的,但如果你去过恩布尔顿湾,就会发现沙丘上刻有一组沙阶,或许曾经通往她的花园。
奎妮的海上花园就那么开始了。在研究过诺森伯兰的花园以及滨海小路之后,我的想象力才给她的海上花园种上花花草草,放进人形浮木。我很高兴她拥有那些东西。她用她生命中的人来填充她的花园,和我用我生命中的人来填充我的写作是一样的。而且顺便提一句,我的孩子们都很高兴看见我们的老边境猎狐犬(那只狗)回来了。
至于玛丽·安贡努修女,我喜欢这么去想,她是父亲借给我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看见他们的花园里有个男人。这个时候父亲已经非常虚弱,病得很重,但他让母亲扶他走向这个男人。母亲没看见任何人,但他们还是一起走到那个地点。走了好几次。
让母亲震撼的是,父亲对花园里有个男人竟然很开心。有过几次——没有多久以前——他还会大吼大叫,很可能还会挥拐杖呢。
父亲并不虔诚。他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宗教信仰。但他看到一个男人,这个人让他感到平和,他渴望和这个人待在一起。大约一天之后,他去世了,就躺在母亲用来搬动他的靠背长椅上。他没有蜷缩也没有闭眼。就那么停摆了。
当我对疗养院管理人员说起这件事时,他微微一笑,就好像这种事我们都应该知道一样。这很普遍。临终经验,他们是这么说的。它们无法被解释,却无疑发生。它们经常能缓解病人的痛苦,因此也助他走过死亡通道。它们似乎也和有时因药物引起的幻觉现象形成鲜明对比。我想多去想象一点父亲看到什么景象,于是虚构了玛丽·安贡努。
重翻《一个人的朝圣》并扭转角度回放一些章节对我来说十分特别。它也赋予莫琳一个不同的声音,还有戴维,以及找到奎妮爱上、其实更是莫琳爱上的那个哈罗德。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奎妮感觉被重新拼凑完整,他们也是。
还是要正式说明一下,我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朝圣》的续集,也不是一部前传。我写的这一本书,它和哈罗德·弗莱比肩而坐。他们真的应该那样出现——她坐在乘客座,他坐在驾驶座。肩并着肩。
我会把这本书称为,一个伴儿。
哈罗德·弗莱就要来了,我想。我等了二十年,现在他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