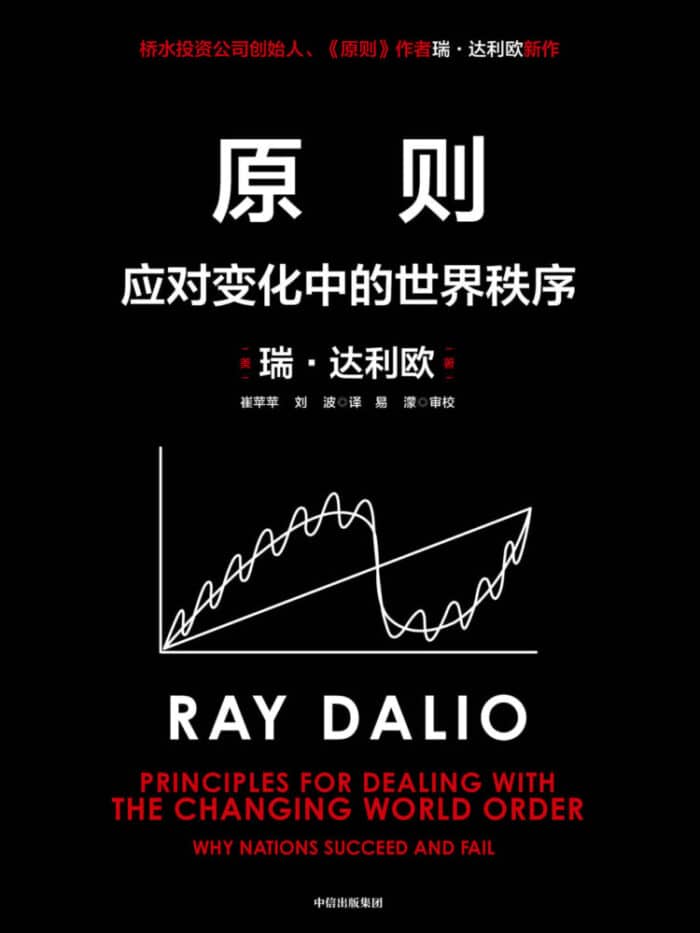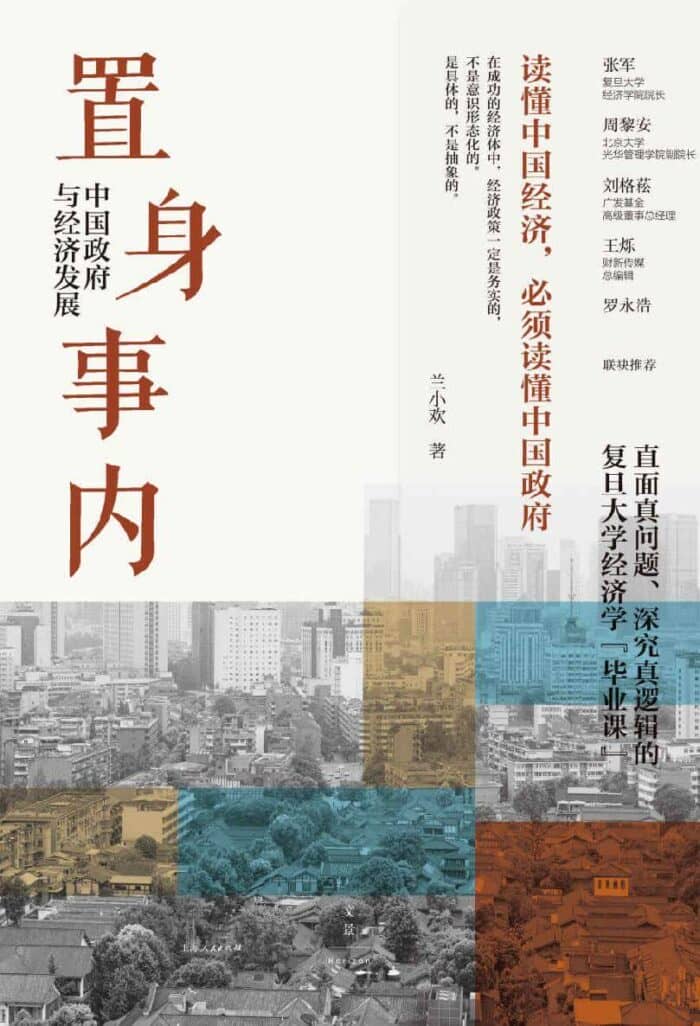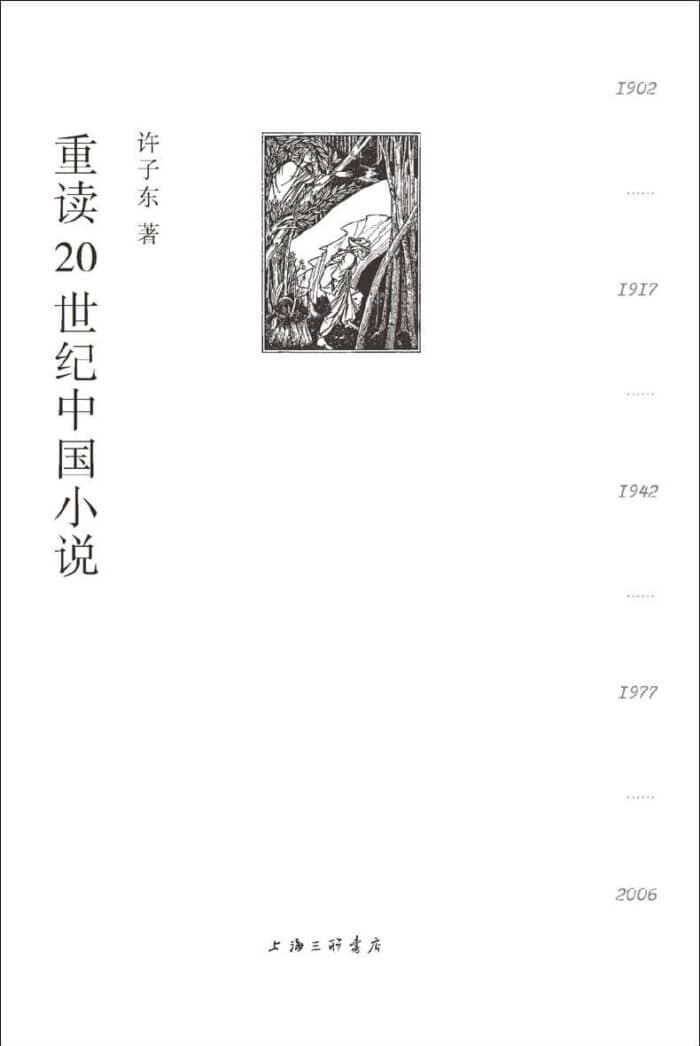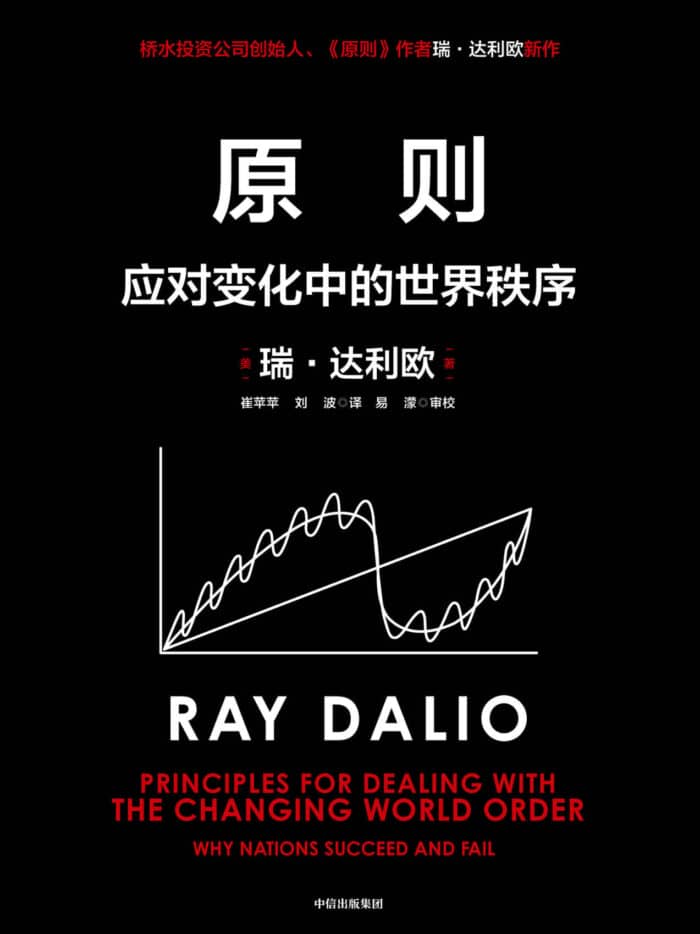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
社会心理学家,德国柏林马普所(Max Planck Institute)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在世界各国讲授风险课,教人们正确地认知风险和进行风险沟通,听他讲课的人有小学生以及杰出的医生、银行家、企业家和政治家。获得多个奖项,包括1991年的“美国科学促进会行为科学研究奖”和德国2002年度“科学书籍奖”。
他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和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试读:
第1章 愚蠢的“智人”
知识是恐惧的解药。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美国思想家、诗人
还 记得笼罩冰岛的火山灰云团吗?还记得次贷危机吗?还记得疯牛病吗?每一次危机都会让我们焦虑不安。我们淡忘了这次危机,下一次危机又来了。遥想当时,很多人滞留在拥挤的机场,很多人遭受养老金不断缩水的严重打击,很多人不敢大口品尝美味的牛排。问题出现时,我们总会听到这样的话:为防止危机再次发生,我们需要开发更好的技术,制定更完善的法律,建立更强大的政府机构。以此类推,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呢?答案是:更严格的监管与更多更优秀的理财顾问。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呢?答案是:建立国土安全部门,启用全身扫描仪,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如何解决卫生保健费用激增的问题呢?答案是:增税,合理化改革,发现更多的“标记基因”。
但是,上述种种方法却没有包含“让人们正确地认知风险”这一条,这是有原因的。
《经济学人》(Economist)曾刊文称,“人类容易犯错,懒惰,愚蠢,贪婪,脆弱”。有人说,我们缺乏理性,是冲动与欲望的奴隶,沉溺于美色、香烟和电子产品。二十几岁的年青一代开车时长时间打手机,殊不知这样会延滞他们的反应时间,使其像70岁的老人一样迟钝。有1/5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薪资最高的那1%的人,还有很多其他人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加入高薪者行列。银行家对人们投资理财的能力缺乏尊重。有些医生告诉我,他们的大多数患者都很愚钝,向他们讲述健康信息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一开始他们就会曲解这些信息。所有这些都说明一点:用“智人”(智慧的人)来命名现代人是错误的。我们的基因出了问题。进化过程似乎用低劣的智力软件欺骗了我们,并让我们的大脑发生了连接错误。简言之,每个人都需要不断被指导,就像小孩需要父母的教导一样。虽然我们身处21世纪的高科技时代,但某种程度上家长式管理却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关上门,让专家聚到一起,告诉公众什么才是对他们最有益的。
这种宿命论的内容,你不会在本书中读到。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个人的愚笨,而在于整个社会都不知道风险为何物。
读写能力是民主社会的文化公民的生命力所在。但是我们只知道读写还不够,能正确地认知风险才是我们在现代科技社会中所需的基本生存能力。今天,科技日新月异,人类认知风险的能力不可或缺,正如我们的读写能力。没有认知风险的能力,你的健康和财富可能会被置于危险境地,你也可能会陷入不切实际的恐惧与幻想之中。也许有人认为,关于风险的基本知识已经在学校学过了,但是放眼中学、法学院、医学院等,却看不到传授这类知识的影子。因此可以说,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正确地认知风险的能力。
认知风险并不仅仅指识别已知风险,还指识别未知与不可预测的风险。认知风险与规避风险截然不同。不冒险,就不会有创新与乐趣,勇气也会荡然无存。认知风险也不意味着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小心谨慎,人类可能早就灭绝了。
你也许认为,有这么多咨询专家可以帮助你,何必多此一举呢?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惨痛的经历告诉我们,专家的意见可能是很危险的。很多医生、金融顾问以及其他风险专家自己都没有正确地认知风险,或者根本无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解释风险。更糟糕的是,其中不少人绝对不会给自己的家人同样的建议。所以,你别无选择,还是自己来吧。
下面,我邀请你踏上一段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旅途,首先从天气预报以及被大雨淋成落汤鸡这一风险开始。
降水概率为30%,你会带伞出门吗?
美国电视台有一位天气预报员曾这样播报天气:
周六的降水概率为50%,周日的降水概率为50%,所以整个周末的降水概率为100%。
我们大多数人听后都会忍俊不禁。不过,如果在天气预报中听到“明天的降水概率为30%”,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30%指什么呢?我住在柏林,大多数柏林人会认为“明天30%的时间会下雨”,也就是说,降雨会持续七八个小时。还有人认为“30%的地区会有降雨”,也就是说,我们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可能不会下雨。而纽约人则觉得这两种看法都是无稽之谈,他们认为“在历史上具备这种气象条件的日子里,只有30%的天数会下雨”,也就是说,明天很可能不会下雨。
图1–1 “明天的降水概率为30%”意味着什么?有人认为,明天有30%的时间会下雨(上图)。有人认为,明天有30%的地区会下雨(中图)。还有人认为,3位气象学家说会下雨,7位气象学家说不会(下图)。其实,气象学家真正的意思是:在具备这种气象条件的日子里有30%的天数会下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理解偏差,不仅仅是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还因为专家未能清楚解释降水概率的意思
人们会不会因此感到无助和困惑呢?出现这个问题,部分要归咎于专家,他们从来不知道如何准确地解释概率。如果他们能够清晰地说明降水概率具体指的是时间、地区,还是天数,困惑就会消失。气象学家真正的意思是,在发布这种天气预报的日子里有30%的天数会下雨。这里的“雨”是指超过某一微小阈值的降水量,比如0.01英寸[1]。如果让人们自己理解,他们会凭直觉想出一个自认为合理的解读,比如持续时间、覆盖范围或是降水强度。想象力更丰富的人还会有其他的解读方式,正如纽约一位女士所言:“我知道30%的降水概率指什么,那就是3位气象学家认为会下雨,而7位认为不会。”
我的观点是,随着天气预测技术的进步,气象学家可以用更精确的说法来预报天气,而不只是告诉我们会不会下雨或降水概率是多少。但是,精确度的提高并没有增加人们对天气预报的理解。事实上,自从1965年美国开始播报降水概率以来,人们的困惑就一直存在,并且不仅限于降水概率,还包括任何事件的概率。比如,“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其性生活出现问题的概率是30%”,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30%的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的性生活会出现问题,还是一个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30%的性生活会出现问题?对于这个长期存在的普遍问题,其实解决方法相当简单:
一定要问清楚“指称词”,即具体指的是什么的概率。
如果天气预报员知道如何与公众沟通,我们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被淋成落汤鸡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风险,不过,对农民和赛车手来说,降水概率却很重要。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举行前,赛车手们讨论最多的就是天气预报,因为根据天气选择合适的轮胎对赢得比赛至关重要。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来说,天气预报决定着能否正常发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灾难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大多数人面临的风险至多是取消全家郊游的计划,或是淋雨,所以我们也许不会特意去关注降水概率。
绝对风险和相对风险有天壤之别
英国有很多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对避孕药的恐慌。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每隔几年就有一些报告提醒女性注意:口服避孕药可能导致血栓,即在腿部或肺部形成血块,威胁她们的生命安全。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英国药物安全委员会发出警告称,第三代口服避孕药会使女性罹患血栓的风险增加一倍,即100%。还有比这个数值更具确定性的吗?这一耸人听闻的信息以信件的形式传递至19万名普通医师、药剂师以及公共卫生负责人,并以紧急通知的形式发给了媒体。顿时,全英国上下警钟四起。忧心忡忡的女性开始停服避孕药,结果导致意外怀孕和堕胎率骤增。
那么,100%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一数字是根据多项研究得出的,这些研究表明,每7 000个服用第二代避孕药的女性中,大约有1位会患血栓;若服用的是第三代避孕药,则患血栓的女性人数会增至两人。也就是说,绝对风险仅增加了1/7 000,而相对风险增加了100%。与绝对风险相比,相对风险看起来大得吓人,可能会引起很大的恐慌。但是,如果药物安全委员会和媒体报道的是绝对风险,则几乎不会有女性因此惊慌失措并停服避孕药,甚至根本没有人会在意。
发生恐慌后的第二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女性堕胎数量增加了约1.3万次。更糟糕的是,其负面影响持续了不止一年。警告发布前,堕胎率一直呈直线下降趋势,发布后却发生了逆转,接下来的几年里堕胎率持续增长。女性对口服避孕药的信任程度下降,避孕药的销量也急剧下降。意外怀孕后,并非所有的女性都选择了堕胎,其中约有一半的女性选择生下孩子。堕胎和生育数量的增长在16岁以下的女孩中尤为明显,这一群体的怀孕人数大约增加了800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怀孕和堕胎是由患血栓的风险引起的,但第三代避孕药的风险却被夸大了。这次恐慌伤害了英国女性,重创了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制药业的股票价格也一路下跌。英国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在堕胎方面的支出增加了400万~600万英镑。除了那些将这则警告放至媒体头版的记者们,没有别的人从中受益。
意外怀孕和堕胎可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事,正如一位女性所说:
当发现自己怀孕时,我与男友已经同居两年了。他的第一反应是“你把孩子打掉吧”。我把他赶了出去。我很想上大学,努力构建未来,但我意识到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我唯一不想做的就是依靠政府,或者更糟的,依靠一个男人。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堕胎。现在两天过去了,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是最佳的选择,但是我的心却很疼。
对避孕药的恐慌在英国反复出现,持续至今。要彻底消除它,靠的不是更好的药品或更复杂的堕胎技术,而是能正确认知风险的年轻男女。向青少年解释相对风险(100%)和绝对风险(1/7 000)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迄今为止,记者们仍可以用夸张的数字年复一年地造成大众的恐慌。
解决方法还是那条简单的法则:
一定要问:绝对风险增加了多少?
用数字误导我们的不只是记者。顶级的医学杂志、健康手册、互联网也会如法炮制,因为数字越大,越有吸引力。2009年,久负盛名的《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刊发了两篇有关口服避孕药和血栓的文章。其中一篇在摘要中写清楚了绝对风险数值,而另一篇则凸显了相对风险——“口服避孕药会使女性患静脉血栓的风险提高5倍”。当然,“5倍”这个数字放在标题中会更显眼,因此,《伦敦旗帜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等报纸根本没有想过要刊登绝对风险数值。一般说来,虽然我们拥有高科技药品,但医生和患者却得不到易于理解的信息。
加强报道的透明度应是每位记者的责任,也应是所有伦理委员会和卫生保健部门的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曾写过《计算风险》(Calculated Risks)一书,解释了如何帮助公众和医生正确理解风险数字。该书出版后,时任达特茅斯学院院长的神经科学家迈克·加扎尼加(Mike Gazzaniga)拜访了我。他对利用相对风险与其他手段误导公众的做法表示愤慨,作为总统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一员,他表示会将此事上报。他说,用数字误导公众的情况,在美国并不比英国少,这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解决的伦理问题之一。其他并不十分明确的伦理问题,比如堕胎、干细胞、基因检测,往往会让伦理委员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我十分感谢加扎尼加的努力,但是,伦理学委员会并没有意识到误导公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从未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伦理学委员会不保护公众,那医生为何不挺身而出呢?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很多医生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释风险,因为医学院几乎没教过这一技能。上万封“致医生的信”的负面效果证明,很多医生都被相对风险蒙蔽了。所以,专家确实需要培训,否则,当下一次对避孕药的恐慌来袭时,他们以及所有受影响的人可能会和以前一样手足无措。
我曾向上千名记者解释过相对风险和绝对风险的区别,其中很多人已经开始报道绝对风险,不再让公众受到惊吓,但是还有一些人仍在报道相对风险。我们也许不能制止所有喜欢制造恐慌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学会如何识破他们的“骗局”。
恐惧心理比恐怖袭击的杀伤力还大
大多数人都会清晰地记得2001年9月11日那天自己身处何地,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画面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当时,所有话题似乎都与这场恐怖袭击有关。3年后,“9·11”调查报告出炉,集中阐述了基地组织的发展状况、外交策略、法制改革与科技措施。但是,这份长达636页的报告却丝毫没有提及公众对风险的认知情况。
让我们回到2001年12月。假设那时你住在纽约,想去往华盛顿,你会选择坐飞机还是开车?
我们知道,“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很多人拒绝乘坐飞机。那么,他们是选择待在家里,还是驱车前往目的地呢?我查看了交通统计数字,找到了答案。“9·11”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内,汽车里程数大幅增加,3个月时间里,乡村州际公路的汽车里程数上升了5%,因为长途旅行的人一般都会经过这里。而恐怖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2001年1月到8月)里,人均汽车里程数与2000年相比仅上升了不到1%,这是每年的正常增长幅度。汽车里程数在快速增长了12个月后又恢复正常水平,因为那时世贸双塔着火的图片已不再出现在媒体上。
陆路交通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后果。“9·11”事件之前,致命交通事故的数量基本接近前5年的平均值(图1–2的基准线)。但是“9·11”事件之后的一年里,每个月发生的致命交通事故的数量都超过了基准线,并且大多数都高于前5年的最高值。共有大约1 600名美国人因为规避坐飞机的风险而在公路上丧生。
这个数字是“9·11”事件中遭劫持的4架飞机的总死亡人数(256人)的6倍多。这些在车祸中丧生的人如果选择乘飞机,也许现在还活着。2000~2005年,25万名乘客乘坐了美国商用航班,没有一个人因空难丧生。所以,虽然“9·11”事件中大约有3 000名美国人丧生,但是之后一年内因车祸死亡的人数比这个数字的一半还要多。
图1–2 恐怖分子的“第二次袭击”。“9·11”事件后,美国发生的致命交通事故的数量持续增长了12个月,大约有1 600名美国人因试图规避乘飞机的风险而在公路上丧生。以1996~2000年的5年平均值为基准线。2001年9月之前,每月发生的致命车祸的数量均接近基准线。“9·11”之后的12个月里,每月发生的致命车祸的数量都超过基准线,并且大多超过上一年的最大值(图中的竖线上端代表最大值,下端代表最小值)。“9·11”事件后出现的峰值足以触发恐怖警报
让我们看一个幸运的例子。
26岁的贾斯廷·克拉宾(Justin Klabin)是一名很有竞争力的橄榄球运动员,还是一名志愿消防队员。他在看到哈得孙河对岸的世贸双塔倒塌后,和消防队其他队员一起赶到了事发地点。经历了这次事件后,他决定不再乘坐飞机。一个月后,克拉宾和女友开车去佛罗里达旅行,他们的轻型货车成功行驶了上千英里[2],但在回程的路上,他们听到“砰”的一声,紧接着货车的两个前轮胎都横了过来,就像雪犁一样。连接转向柱和车轮的横拉杆断了,货车抛锚了。幸运的是,他们这时已驶入了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停车场。如果这次事故发生在几分钟前——他们还在公路上以70英里的时速行驶时,克拉宾和他的女友很可能会像那些不幸的人一样,为规避坐飞机的风险而在车祸中丧生。
恐怖分子其实对我们进行了两次袭击。第一次借助的是体力,第二次借助的是我们的大脑。第一次袭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美国政府投入几十亿美元建立美国国土安全局等庞大的机构,并研发新科技,比如可以穿透衣服看到皮肤的全身扫描仪。而第二次袭击却几乎没人注意到。事实上,从新加坡到威斯巴登,我曾到各地的国际情报部门和反恐部门讲授风险管理课,但主办方却接连不断地表示惊讶,因为他们从未考虑过我所说的第二次袭击。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曾兴致勃勃地解释,他如何用很少的钱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基地组织只花了50万美元,而据保守估计,美国因这次突发事件耗费了5 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基地组织的每一美元投入都换来了100万美元的回报”。要想防止恐怖分子的自杀式袭击是很难的,但消除袭击给我们带来的非理性恐惧则相对容易一些。
恐怖分子究竟利用了我们的什么心理呢?导致很多人突然同时死亡的低概率事件,即所谓的“忧虑风险”,会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触发一个心理学反应:
如果很多人在某一个时间点同时死亡,人们就会产生恐惧,并试图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请注意,这种恐惧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死亡本身,而是因为某种特殊的死亡方式,即在某个时间点或短时间内同时死亡。当很多人突然同时死亡,比如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我们进化的大脑就会产生极大的忧虑。但是,如果还是那么多人或者有更多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分别死亡——比如在汽车和摩托车交通事故中——我们就不怎么害怕。仅就美国而言,每年都会有3.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但很少有人会在开车时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有人说,开车时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坐飞机时则不是,但从心理学角度讲,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此。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人也无法控制汽车,更别说坐在后面的乘客了,但他们同样无所畏惧。其实,我们并不害怕在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故中丧生,我们害怕的是突然间和很多人同时丧生。我们害怕罕见的核电站事故,却不怕煤电站污染会慢慢导致人类死亡。我们听到猪流感疫情可能造成上万人死亡的预测后,会被恐惧缠身,虽然这类预测从未变成现实。每年,全球会有上万人死于普通流感,但很少有人为此担忧。
这种害怕“忧虑风险”的原因是什么?从人类历史来看,这可能是一种合理的反应。为了生存,原始人类会组成采集狩猎的小部落,成员往往有20~50人,极少超过100人,当今世界上还有类似的部落存在。在这种小部落中,如果很多人突然死去,部落中剩下的人遭受掠夺和饥饿的风险就会增加,整个部落的存亡也会受到威胁。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生存不再依靠小团体或部落的支持和保护,但是,要引发这种心理反应还是很容易的。直到今天,真正或假想的灾难都有可能引起恐慌。
“原始大脑”对忧虑风险的害怕会抑制进化的“现代大脑”闪现的任何念头。正如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给我的信中所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我向妻子解释开车比坐飞机的风险大,但她根本不信。”理性的论据并不总能消除原始大脑的恐惧,尤其是夫妻一方试图说服另一方时。不过,有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也许能够帮助这位教授:
当理性与某种强烈的情感发生冲突时,不要用争执的方式去解决,而应该用另一种与该情感相冲突并且更强烈的情感。
父母的关心就是与对“忧虑风险”的恐惧相冲突的一种情感。上述那位教授可以提醒他的妻子,开车行驶那么远的路程,不仅是拿丈夫的生命冒险,也是在拿孩子们的生命冒险。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更可能帮助心有余悸的他们克服坐飞机的恐惧。聪明的“现代大脑”能够让一种正在形成的恐惧对抗另一种恐惧,从而使人类更好地存活于现代社会。进化并不是终极目标。
恐怖分子的第二次袭击侵犯了公民自由:“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前,如果没有合理根据的话,进行光身搜查就会被视为侵犯人权,但现在这却被视为公民的责任。忧虑风险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在机场排起长队,将液体放入塑料袋,脱掉鞋子和夹克,解下腰带,让陌生人触碰自己的身体。安全支出的增加导致服务质量更加低下,座位更加拥挤。人们不再无忧无虑,而是忧心忡忡。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已耗资1万多亿美元,导致数千名士兵以及更多的平民丧生,由此造成的资金紧张很可能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类似的袭击再次发生,我们不应该再让自己的大脑被恐怖分子利用。只有正确地认知风险,我们才能抵制恐怖分子的操纵,才能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具弹性的社会。对此,我们必须做到三点:了解恐惧的本质,如果理性不奏效可以用冲突的情感控制这种恐惧,弄明白坐飞机的真正风险。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你应该坐飞机,还是开车?假设你住在纽约,想去往华盛顿,你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安全到达。开车行驶多少英里会和乘坐直飞班机的风险相同?针对这一问题,我曾经问过很多专家,答案不一而足:1 000英里,10 000英里,绕地球转三圈等。其实,最佳答案是12英里。是的,只有12英里。如果你开车安全到达机场,那么旅行最危险的部分很可能已经结束了。
面对风险,人们是否无计可施?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发现自己不懂降水概率?为什么这么多人因为不知道相对风险和绝对风险的区别而意外怀孕或堕胎?毕竟,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降水概率和对避孕药的恐慌现象就已出现,每当新的威胁出现,不管是疯牛病还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或禽流感,人们对忧虑风险的恐惧就会一遍遍地发生。为什么人们不学习如何应对风险呢?
很多专家认为,原因在于人们基本上无法理解类似的事情。随着争论的继续,试图教导人们改正错误的各种努力几乎都失败了。在这种悲观看法的基础上,德意志银行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列举了我们这些“智人”所犯的非理性错误。许多图书不断重复这一信息,说智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需要地球上那些理性的人“助推”他们一下,他们才能够做对决策。
我的观点正好相反,人类并不愚蠢,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培养人们认知风险的能力方面存在盲点。我们教孩子学习数学中的各种确定性——几何学和三角函数,却没有教他们如何认识不确定性,即如何运用统计学思维。我们教孩子生物学,却没有教他们关于恐惧和欲望的心理学。令人惊讶的是,甚至连专家都没有接受过如何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向公众解释风险的培训。当然,吓唬人能给某些人带来益处:在媒体头版发表文章,劝说人们放弃公民权利,或是销售某种产品。所有这些外因共同导致了这个问题。
好在这个问题并非无解。几百年前,谁能想到今天地球上有这么多人会读书和写字。终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所有人都想具备认知风险的能力,所有人也都能够做到。根据我和其他同事的研究,我认为:
1. 任何人都能学会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本书介绍的原则对于有求知欲的任何人而言,都是简单易懂的。
2. 专家是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询问专家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专家自己也不了解风险,缺乏解释风险的技能,他们追求的利益与你并不一致,很多银行倒闭的原因正在于此。不懂风险的权威人士负责引导公众时,往往收效甚微。
3. 少即是多。面对复杂的问题,我们会寻找复杂的解决方法。当此法不奏效时,我们会寻找更加复杂的方法。在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这绝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复杂问题并不一定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法。从金融衍生品到税收制度,过于复杂的体系让人难以理解却容易操纵,以致越发危险。而简单的方法却能让我们更加明智,去创建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认知风险需要人们有勇气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挑战权威,并提出具有批判性的问题,重掌自己情绪的控制权。这种改变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具启发性,让我们的焦虑更少。此书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练就认知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