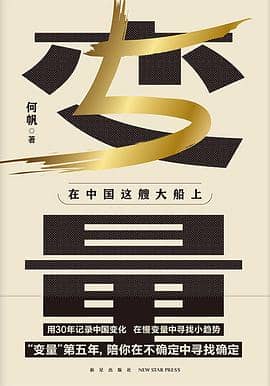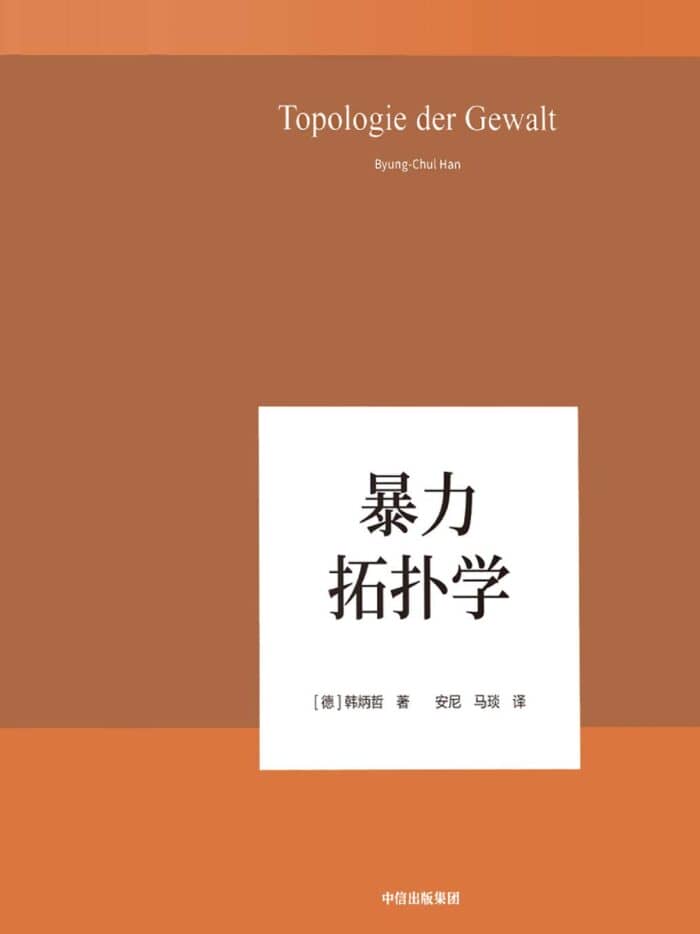内容简介:
莱昂诺尔·冈萨雷斯生活的小社区位于秘鲁境内安第斯山脉5 500米的高处,那里是海拔最高的人类居住地之一。与已故的丈夫一样,她在金矿上工作,其工作方式与西班牙征服后的印第安人被迫从事的几无二致。在当地,文盲、营养不良和疾病与五百年前一样盛行,而时至今日,一个矿工的生存状况依然受制于更广阔的全球市场。
卡洛斯·布埃尔戈斯是古巴人,年轻时曾在安哥拉内战中浴血奋战,现居住于美国新奥尔良郊外的一个安静社区。他是1980年古巴驱逐到美国的数百名罪犯中的一员。他的故事呼应了贯穿拉丁美洲历史的暴力行为,从前哥伦布时代的征战到西班牙殖民的暴行,从19世纪和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到今日的街头动乱和军事镇压。
哈维尔·阿尔沃是一位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耶稣会神父,他移民到玻利维亚,数十年如一日在原住民中工作。他自认在思想和情感上都是一名印第安人,因而在自己的“第二祖国”广为人知。尽管他的目标更多是学习而非传教,但他的经历实际上与一段充满变数的过去一脉相承。那时,神父与征服者并肩前进,为了争夺新世界而强制原住民皈依基督教。从那时起,天主教会就在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中心作用,而这种作用显然具有两面性。
在《银、剑、石》一书中,秘鲁裔作家玛丽·阿拉纳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扎实的纪实写作将三位当代拉美人的故事与拉丁美洲过去千年的历史无缝编织在一起,从而阐释了自前哥伦布时代至今,定义拉丁美洲的三个恒久主题:来自外部的对资源的无尽索取(银)、挥之不去的暴力阴影(剑),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石)。串联历史与现实,抛开“胜利者视角”,阿拉纳尝试挖掘拉丁美洲的独特经历奠定的“本性”,勾勒出这片土地上人民的身份、心态与命运。
作者简介
[美] 玛丽·阿拉纳(Marie Arana)
出生于秘鲁利马,现居美国华盛顿。她是作家、编辑、记者和文学评论家,也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高级顾问和美国国家图书节文学总监。
阿拉纳的职业生涯始于图书出版业,曾任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副总裁,后连续十多年担任《华盛顿邮报》文学栏目“图书世界”主编,目前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也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西班牙《国家报》、哥伦比亚《时代报》和秘鲁《商业报》等多家媒体撰文。她同时从事虚构和非虚构写作,是一名优秀而成熟的写作者。
她的代表作《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Bolívar: American Liberator)荣获2014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她撰写的回忆录《美洲女孩》(American Chica)描述了她本人横跨北美和南美两种文化的童年,入围200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终选名单。阿拉纳另著有小说《玻璃纸》(Cellophane)和《利马之夜》(Lima Nights),还曾参与电影《女孩崛起》(Girl Rising)的编剧工作。
试读:
第一章
至今尚寻黄金国
秘鲁是坐在金板凳上的乞丐。
——秘鲁古谚语[1]
天还没亮,莱昂诺尔·冈萨雷斯(Leonor Gonzáles)就离开她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一座冰峰之上的石头小屋,在砭骨的寒气中沿着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上山,在岩石中仔细寻找星星点点的金屑。[2]她和以前祖祖辈辈的人一样,步履蹒跚地背来一包包沉重的石头,用粗陋的锤子将石头打碎,用脚把碎片蹍细,再将其磨为粉末。然后,她把石粉倒入水银溶剂中不停地摇晃,偶尔运气好的时候,能析出微小的黄金颗粒。她才47岁,但牙齿已经掉了。她脸上的皮肤被烈日烤得颜色黧黑,被寒风吹得干燥开裂。她的双手呈紫红色,手指弯曲变形。她的视力严重受损。但是,每天太阳从阿纳尼亚山(Mount Ananea)的冰峰后露出脸来的时候,她仍然和拉林科纳达(La Rinconada)这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定居点的其他女人一起,爬上通往矿井的陡峭沟沿,搜寻一切闪光的东西,把石头塞进麻袋,傍晚时背着压得人直不起腰的麻袋下山回家。
这幅景象好似来自古老的《圣经》时代,其实不然。莱昂诺尔·冈萨雷斯昨天爬上那座山梁去寻找黄金,那是她的祖先自古以来的营生。明天她会再次爬上那座山梁,继续做她从4岁起就跟着妈妈做的活计,尽管不到50千米外,一家加拿大矿业公司正使用21世纪的大型机械做着同样的事,在的的喀喀湖这个印加文明摇篮的另一边,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的大公司也斥资数百万美元购买最先进的设备,来参与拉丁美洲兴旺繁荣的采矿业。在这片大陆上,从地层深处挖掘亮晶晶的宝藏这个行当源远流长,在多重意义上塑造了拉丁美洲人民。
本书标题中的“银、剑、石”三元素是拉丁美洲为之无法自拔的千年执念,而莱昂诺尔·冈萨雷斯就是它们活生生的体现。“银”代表着对贵金属的渴望。这种渴望主导着莱昂诺尔的生活,正如它主导着在她之前世世代代拉美人民的生活。她近乎疯狂地寻找的宝物不能为己所用,而是要送到她永远不会踏足的城市中去。拉丁美洲对黄金白银的喜爱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在西班牙对美洲大陆开展无情征服后更是沉溺其中。这种痴迷驱动着残酷的奴隶制和殖民剥削,引发了一场血腥革命,造成了整个地区连续数世纪的混乱,如今又变身为拉丁美洲美好未来的最大希望所在。印加和阿兹特克统治者将黄金白银当作荣耀的象征;16世纪的西班牙因为控制了贵金属的供应而富强无比;今天,采矿业依然是拉丁美洲实现兴旺发达之希望的关键。对挖掘出来装船运走的闪亮宝物的痴迷持续至今,尽管矿产资源并非无穷无尽,尽管这种狂热必须停止。
莱昂诺尔是“银”的产物,也是“剑”的产物,后者代表着拉丁美洲长期以来的强人文化。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何塞·马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人都说过,就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言,拉丁美洲喜欢靠单方面展示骇人的力量,靠无情手段,靠强力压制,靠独裁者和军方为之自鸣得意的“铁拳”(mano dura)。公元800年的莫切人(Moche)强悍好战,动辄使用暴力;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统治期间,暴力越发普遍;西班牙通过埃尔南·科尔特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残酷统治把暴力完善化、制度化;19世纪拉丁美洲惨烈的独立战争更是使暴力深入社会肌髓。国家恐怖主义、独裁统治、无尽的革命、阿根廷的“肮脏战争”(Guerra Sucia)、秘鲁的“光辉道路”(Shining Path)、哥伦比亚的“哥武”(FARC)、墨西哥的犯罪卡特尔、21世纪的毒品战争——这些都是拉丁美洲暴力历史的遗产。500年前,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哀叹说,西班牙殖民地“满是印第安人的血污”;[3]今天,剑在拉丁美洲仍旧是权威与权力的工具。
压迫和暴力对莱昂诺尔·冈萨雷斯来说毫不陌生。她的祖先是高原[4]居民,先被印加人征服奴役,后又在西班牙征服者手中遭到同样的厄运。印加帝国为压迫被征服者,创立了“米特马克”(mitmaq)移民制,后来又被西班牙采纳;好几个世纪期间,莱昂诺尔的祖辈在“米特马克”制度下动辄被强令搬迁,或是被迫离开故土,迁入天主教会设立的“传教区”(reduction),那是天主教会为拯救原住民的灵魂而建立的庞大定居点。19世纪,莱昂诺尔的祖辈被剑逼着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队伍里作战牺牲。20世纪,他们为逃脱“光辉道路”的大肆屠杀,在安第斯山上越退越高,直退到白雪皑皑的山巅。但是,即使在海拔5 500米的空气稀薄地带,剑仍然是王。今天,在拉林科纳达这个混乱蛮荒、无法无天的矿区小镇上,谋杀和强奸司空见惯,用人当祭品向山鬼献祭的惯例仍在继续。连政府的警长都对这个地方望而却步。在这里,莱昂诺尔和500年前她的祖先一样,随时可能遭受野蛮暴力的袭击。
每天早上,莱昂诺尔起床后,都要摸一下摆在床头的一块小小的灰色石头,石头旁边是她的亡夫胡安·西斯托·奥乔乔克(Juan Sixto Ochochoque)一张褪色的照片。每天夜里,她爬到和子女以及孙辈共盖的毯子下入睡之前,都要再摸一下那块石头。她对登门拜访的我说:“这里面安息着他的灵魂。”[5]莱昂诺尔的家是建在冰川边上的一间小屋,面积顶多有10平方米,屋里寒冷难耐。和她同住的有她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两个孙辈。她和照片里那位面色红润的矿工胡安并未真正结婚;在莱昂诺尔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举行过天主教会的结婚仪式。对她来说,胡安就是她的丈夫、她孩子的父亲。有一天,矿井发生了塌方,胡安吸入大量致命烟雾后身亡。自那以后,莱昂诺尔床头那块灰色圆形石头就成了胡安的化身,也承载了她的全部精神生活。从格兰德河[6]到火地岛,许多原住民只接受天主教教义中与自己祖先的神祇相吻合的内容,莱昂诺尔也不例外。圣母马利亚是帕查玛玛(Pachamama)的另一个化身;帕查玛玛是大地母亲,是我们脚下的土地,是世间万物的来源。上帝是阿普(Apu)的别名;阿普是山中的精灵,太阳是他的精力来源,石头是他的栖息地。撒旦是掌管死亡、冥界和地下黑暗世界的恶神苏佩(Supay),它严苛无情,需要讨好、安抚。
莱昂诺尔的石头代表着过去1 000年来拉丁美洲的第三种痴迷:笃信宗教,不管宗教场所是神庙、礼拜堂、精美壮观的大教堂,还是圣石堆成的石头堆。1 000年前,哥伦布尚未到来时,这个地区的强国征服他人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被征服者的神像捣为齑粉。西班牙征服者到达美洲后,常常把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建造的宏伟石头神殿推倒,在上面建起大教堂。此中意义对被征服者来说显而易见。岩石上堆叠岩石,神殿上筑起神殿,原住民每一个大型神庙或瓦卡[7]顶上都建起了天主教堂;宗教成为强大而具体的证明,时刻提醒着人们谁是胜利者。随着时光的流逝,天主教在拉丁美洲成为一家独大;后来,一些天主教徒又在五旬节派的吸引下脱离了天主教。经过这一切,拉丁美洲人民仍然笃信宗教。他们经过教堂时在胸前画十字。他们在家里安设神龛。他们在钱夹里放圣像,对古柯叶喃喃自语,在汽车后视镜上挂十字架,往衣兜里装圣石。
受银、剑、石主宰的不止莱昂诺尔一人。大多数拉丁美洲人都和她差不多。在墨西哥、秘鲁、智利、巴西和哥伦比亚,矿产开采重新成为和400年前一样的首要经济活动,采矿业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进步,拉动了经济,推动了脱贫,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宝贵的矿产从乡村运到城市,由棕种人交给白种人,从穷人手中转给富人。莱昂诺尔住的小屋下面的岩石中挖出来的黄金推动着一整套复杂的经济活动,参与其中的包括离她家仅有几步之遥的破烂啤酒屋、山下普蒂纳(Putina)城里成群的雏妓、利马的银行家、加拿大的地质学家、巴黎的社交名媛和中国的投资者。这项产业的利润最终会流向海外,到达多伦多、丹佛、伦敦、上海,正如昔日黄金装在西班牙的大帆船里跨过大西洋,抵达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和北京。钱的走向并未改变。它只短暂停留——让人用它在小酒馆里买杯啤酒,或买上一条羊腿挂在房梁上,招来成群的苍蝇——便很快流走了,去到那些地方。
“剑”同样历史悠久,从奇穆[8]武士用来将敌人开膛破肚的锋利石刀,[9]到墨西哥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的泽塔(Zeta)帮派成员使用的粗陋厨刀,暴力文化在拉丁美洲挥之不去,隐身暗处伺机爆发。这个地区向着和平与繁荣的进步本就时断时续,暴力更是构成了对进步的威胁。在这个各种不平等触目惊心的地区,剑是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掌权、受过教育的白人占人口多数的智利是如此;在今天街头流血事件频发,人民贫穷困苦、目不识丁的洪都拉斯也是如此。世界上最危险的10个城市都在拉丁美洲。[10]难怪大批绝望的难民逃离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蜂拥进入美国。[11]恐惧是驱使拉丁美洲人北上的引擎。
至于掌控精神的“石”,有组织的宗教无疑在美洲发挥着关键作用,古今皆然。印加时代,伟大的印加王帕查库特克·印卡·尤潘基和图帕克·印卡·尤潘基“翻转了世界”,[12]扩大了帝国版图,不仅征服了南美的大片土地,还迫使被他们打败的人民膜拜太阳神。从那时起,信仰就既是促进社会统一的工具,又是压迫人民的利器。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一样征服无餍,也深知宗教的用处,但他们改变被征服者信仰的方法与印加人截然不同。他们经常把被征服民族的神祇一并接纳下来,因为他们认为,别人的神与他们自己的神可能有许多共同之处。信步走过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的任何一个村庄,都能发现古老的信仰在当代艺术和传统仪式中的生动表现。
今天在拉丁美洲,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亚洲人和欧洲人的宗教都有信众,但最鲜明的烙印仍然是500多年前西班牙留下的。拉丁美洲是个坚定信仰天主教的大陆,全世界天主教徒中有40%在这里。[13]从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到墨西哥的蒙特雷(Monterrey),教徒们被一条强有力的纽带紧紧连在一起。给6个南美共和国带来了解放的西蒙·玻利瓦尔甚至认为拉丁美洲信仰天主教的西语国家是世界上一支统一的力量,潜力巨大。西班牙王国政府千方百计不让各个殖民地互相交流、开展贸易或建立和睦关系,但自从它把殖民地带到耶稣面前起,就把它们永远地联合为一体了。最终,玻利瓦尔没能把他所解放的那些都讲西班牙语、信仰基督,但各不相同、骚动不宁的人民组建为一个强大的泛美联盟。但是,今天的教会和玻利瓦尔的时代一样,仍然是拉丁美洲各地最受信任的机构。[14]
本书讲述的是千年来塑就了拉丁美洲社会的三个关键成分。我无意对历史做出权威的全面叙述,只想解释拉丁美洲人民的遗产和我们历史上的三个要素,希望对我们的未来有所启发。当然,使我们欲罢不能的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它们显示了这个地区可爱的一面,例如,我们对艺术的迷恋、对音乐的激情、对烹调的喜好、对修辞的热爱。拉丁美洲人笔尖下流淌的西班牙语产生了当今时代最具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顾家爱家、热情待人也是这个地区人民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比不上拉丁美洲对采矿的痴迷、对蛮力的喜爱和对宗教的笃信。是它们最有力地推动了人口流动,镌刻了大地,书写了历史。
这三种痴迷并非彼此无关,对它们的叙述也不能完全分开。过去1 000年中,它们之间不断碰撞、叠加,盘根错节,正如黄金、信仰和恐惧在莱昂诺尔·冈萨雷斯的生活中密切交织。拉丁美洲笃信宗教,崇尚暴力,顽固坚持一种古老的采掘业形式,尽管它未必能带来持久发展;这一切多年来一直使我深感兴趣。我相信,研究这些倾向的历史能使人深入了解拉丁美洲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拉丁美洲是“一个天生不合常规的大陆”。[15]它自成一体、特立独行,其他地方形成的理论或学说几乎全不适用于它。我也相信,虽然我为撰写本书费时多年,努力择清理顺历史的脉络,但我仍然不可能讲清楚历史的全貌。
怎么来解释一个半球和那里的人民呢?这实在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过去500年偏颇的历史记载更加大了这一任务的难度。不过,我仍然坚信,西班牙语美洲的经历造就了一种共性,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具体的性格。我还坚信,这种性格直接源自两个世界的巨大碰撞。这样的经历造就了一种勉为其难的宽容,这是我们的特性。在北边没有与之对等的东西。
在拉丁美洲,我们也许不能确知自己属于哪个种族,但我们知道自己与这个“新世界”的联系比与“旧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经过不同种族间数世纪无拘无束的交融后,我们血液中棕种人的成分比白种人的多,黑人或印第安人的成分也比有些人以为的要多。但是,自从殖民者和原住民的“第一次接触”以来,每一代焦虑不安的“白人”都死抓住政治权力不放,所以,真正弄清我们身份特征的设想从来都无法实现。无论如何,拉丁美洲原住民的历史得以持续至今(这一点和北美不同),说明它一定有其特殊的原因。在此,我谨谦卑地提出我的一己之见,希望与读者分享一些心得。
我父亲家这边在秘鲁定居快500年了,但我的祖母罗萨·西斯内罗斯-西斯内罗斯·德·阿拉纳(Rosa Cisneros y Cisneros de Arana)却对西班牙的一切情有独钟。她常对我说起西班牙的一个习俗:把儿子们送入各种行当,为强大的社会提供栋梁。按照这个习俗的思路,第一个儿子要做通达世事的工作(律师、从政者或生意人),第二个儿子要当军人,第三个儿子则应担任神职。老大通过管理国家的权力和财富来确保国家繁荣;老二身为军人为国服务,维持和平;老三通过宣讲上帝之道打开通往天国的大门。[16]我在历史书中从未读到过这个习俗,不过我在拉美各国旅行期间不止一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慢慢地,我认识到,银行家、将军和主教的确是我们社会的柱石,正是他们维持着当年西班牙创立的僵硬等级制度中的寡头统治、性别关系和种族关系。印加人、穆伊斯卡人(Muísca)、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也把主权寄于君主、武士和大祭司组成的三巨头身上。最高统治者经常身兼三职。无论如何称呼,三角控制的准则在拉丁美洲有效运作了好几个世纪。各古代文化依靠它扩张地盘,征服异族;殖民者利用它牢牢钳制住殖民地人民的钱袋、拳头和灵魂。虽然拉丁美洲对世界贡献良多,尽管我们有着众口传颂的古老文明,但统治着拉美地区的力量始终是银、剑、石。
[1] 通常认为这句话是19世纪曾在秘鲁生活和教学的意大利科学家安东尼奥·雷蒙迪(Antonio Raimondi)所言,但这一点从未得到证实。尽管如此,这句谚语在南美洲流传已久,尽人皆知。秘鲁矿业工程师学会(IIMP)甚至曾竭力反驳这句谚语;事实上,其负责人声称:“秘鲁不是坐在金板凳上的乞丐。在我们国家,矿业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和出口总额的60%。”这恰恰能说明问题。几乎所有金子都流出了国门,而四分之一的秘鲁人生活在贫困之中。IIMP, accessed January 29, 2019, www.iimp.org.pe/actualidad/el-peru-no-es-un-mendigo-sentado-en-un banco-de-oro; Reuters, “Peru Poverty Rate Rises for First Time in 16 Years: Government,”April 24, 2018. 关于这句谚语参见:A. Alcocer Martínez, “Conjetura y postura frente al dicho ‘El Perú es un mendigo sentado en un banco de oro,”Boletín de la Academia Peruana de la Lengua [Bulletin of the Peruvian Academy of Language] 41 (2006): 45–58。
[2] 所有关于莱昂诺尔·冈萨雷斯的信息都基于她在秘鲁接受的跟踪访谈:2012年2月17—22日于拉林科纳达;2012年2月23日于普蒂纳;2013年2月15—19日于胡利亚卡;2014年2月19—24日于胡利亚卡和普诺;2015年2月11—15日;2016年2月20—24日;2017年3月2—7日;2019年1月31日—2月5日。从2013年起,我与这家人保持每周的非正式沟通,每年至少去一次胡利亚卡拜访他们。
[3]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penultimate paragraph, Project Gutenberg, www.gutenberg.org/files/23466-h.html.
[4] 原词altiplano特指南美洲中部的高原台地。——编者注
[5] 她的原话是:“Su alma ahí en el rumi.”rumi是盖丘亚语中的“石头”一词。
[6] 格兰德河(Rio Grande)是墨西哥与美国的界河,亦即拉丁美洲的北界。——编者注
[7] 瓦卡(huaca),安第斯地区原住民认为栖息着神明的石头堆。详见本书第三部分。——译者注
[8] 奇穆(Chimú)文化是印加帝国之前出现在秘鲁的古代文化,15世纪被印加帝国所灭。——译者注
[9] Carmen Pérez-Maestro, “Armas de metal en el Perú prehispanico,” Espacio, Tiempo y Forma, I, Prehistoria y Arquelogía, T-12, 1999, 321.
[10] USA Today, July 17, 2018(巴西的贝伦、委内瑞拉的瓜亚纳城、墨西哥的维多利亚城、巴西的福塔莱萨、墨西哥的拉巴斯、墨西哥的蒂华纳、巴西的纳塔尔、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World Atlas, October5, 2018(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洪都拉斯的中央区;墨西哥的维多利亚城、委内瑞拉的马图林、萨尔瓦多的圣萨尔瓦多;委内瑞拉的瓜亚纳城、委内瑞拉的瓦伦西亚、巴西的纳塔尔)。另见David Luhnow, “Latin America Is the Murder Capital of the World,”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0, 2018。
[11]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13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August 2014, 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ois_yb_2013_0.pdf. Miriam Jordan, “More Migrants Are Crossing the Border This Year,”New York Times online, March 5, 2019.
[12] 帕查库特克(Pachacutec)或帕查库蒂(Pachacuti)的字面意思就是“翻转世界者”或“撼动大地者”。Mark Cartwright, “Pachacuti Inqa Yupanqui,” Ancient History En cyclopedia, last modified July 18, 2016, www.ancient.eu/Pachacuti_Inca_Yupanqui.
[13] Pew Research Center online, “The Global Catholic Population,” last modified February 13,2013, www.pewforum.org/2013/02/13/the-global-catholic-population; US Central Intelli gence Agency online, “Religions,” in The World Factbook, accessed January 29, 2019,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122.html.
[14] Edward L. Cleary, How Latin America Saved the Soul of the Catholic Church, 3. See also Feline Freier, “Maduro’s Immorality and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Venezuela,”Georgetown University Berkley Center for Religion, Peace & World Afairs online, last modified, June 15, 2018.
[15] Eric Hobsbawm, Viva la Revolución, ed. Leslie Bethell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6).Credit also to Tony Wood’s review of that book in the Guardian (UK edition), July 18,2016.
[16] 这就是人称“los ricos, los militares, y los curas”,即“银行家、将军和主教”的权力铁三角。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总统曾称这种权力三角将严重削弱资本主义。他的思想要点见Socialismo del Siglo XXI (Caracas,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Ministerio del Poder Popu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