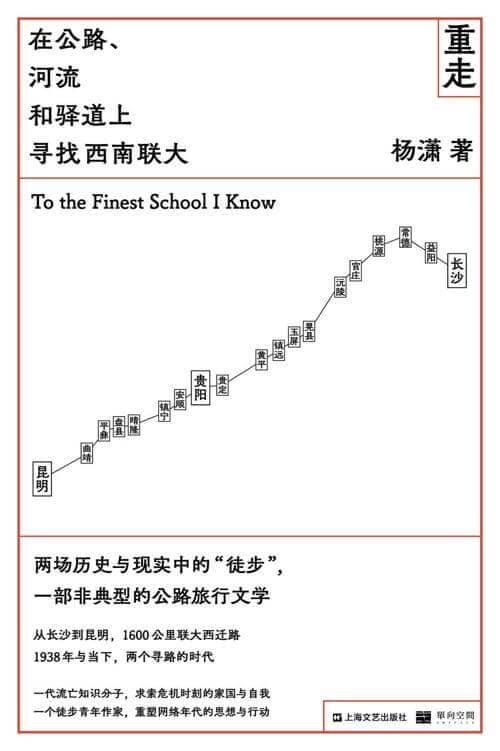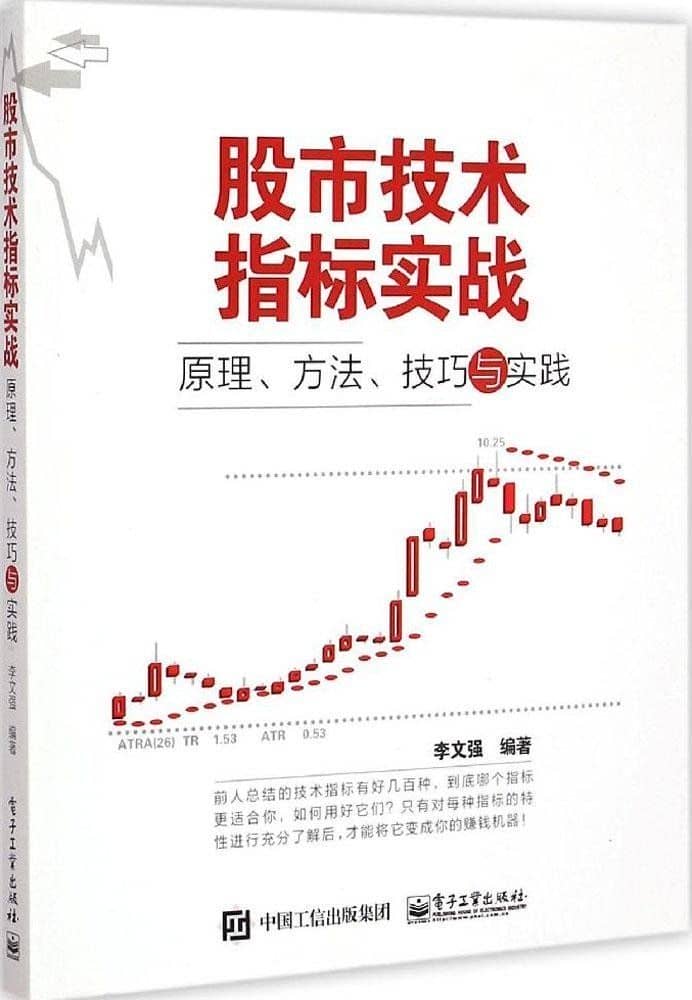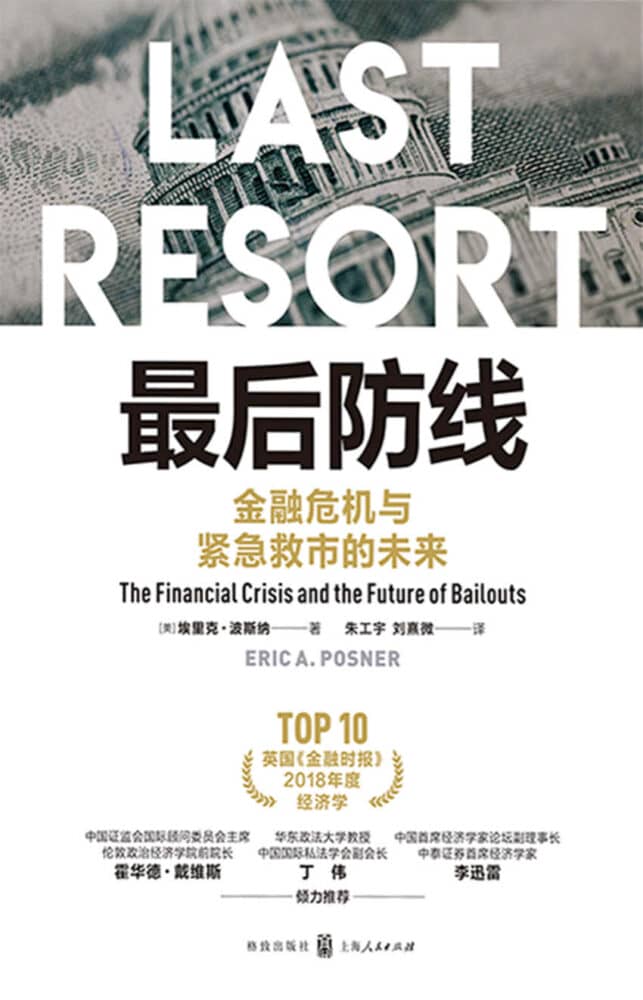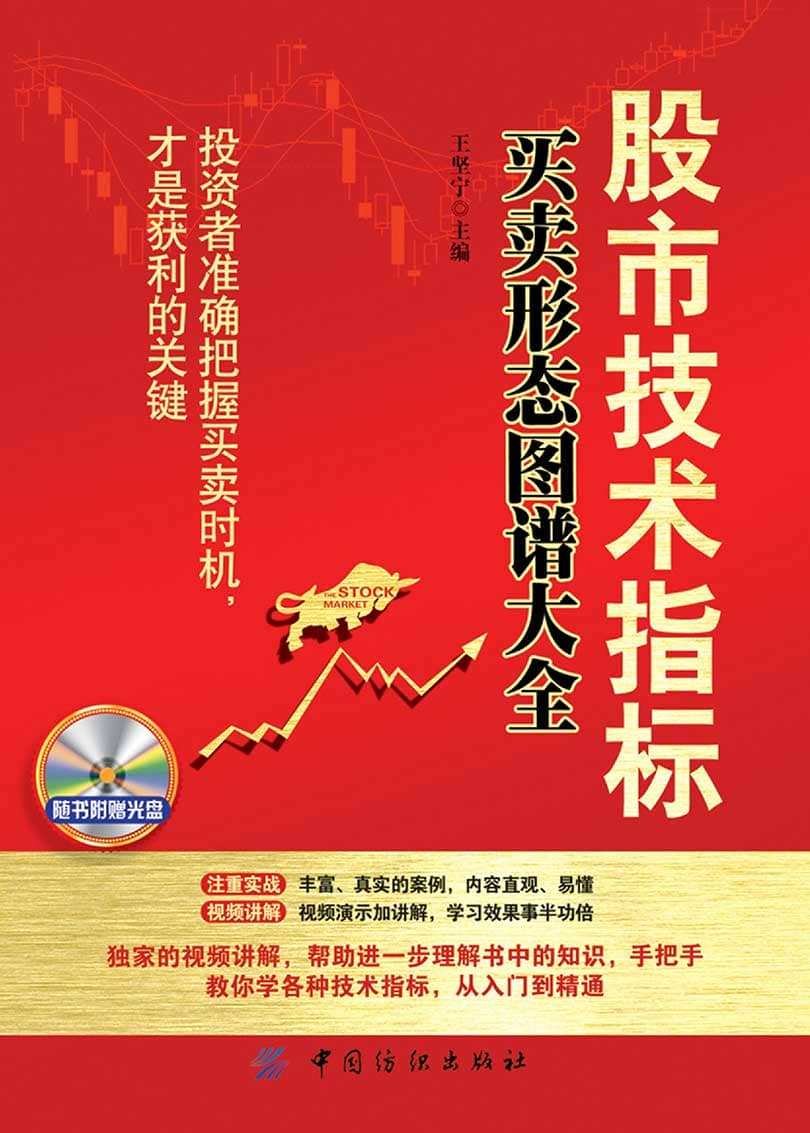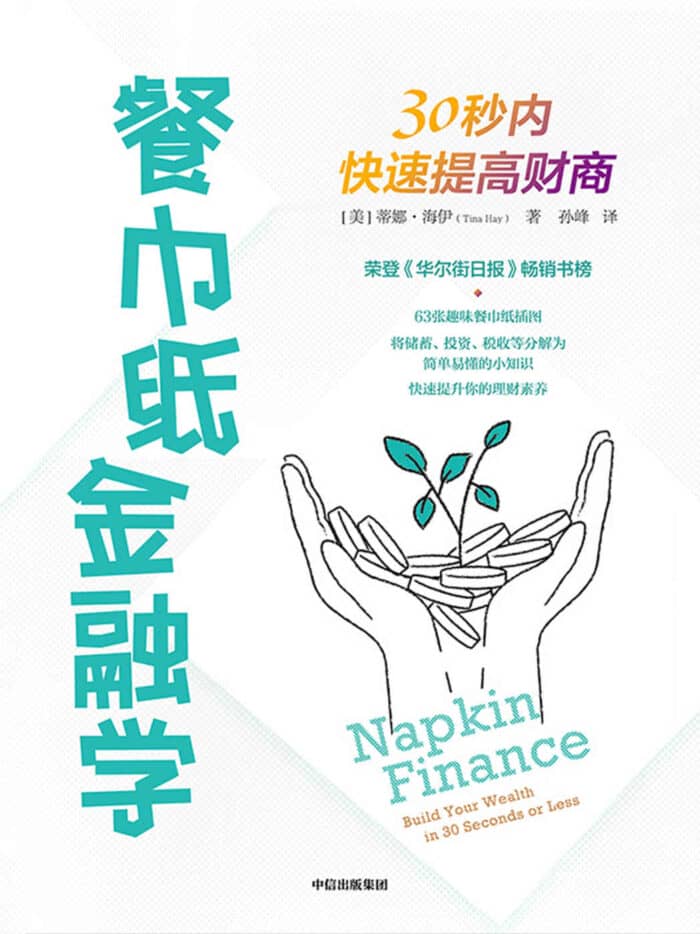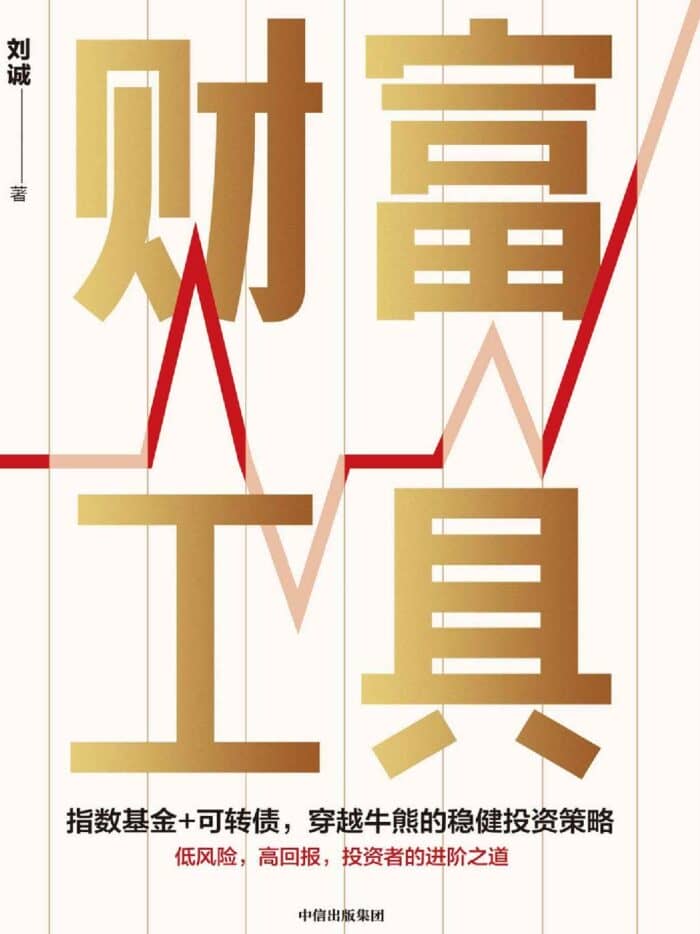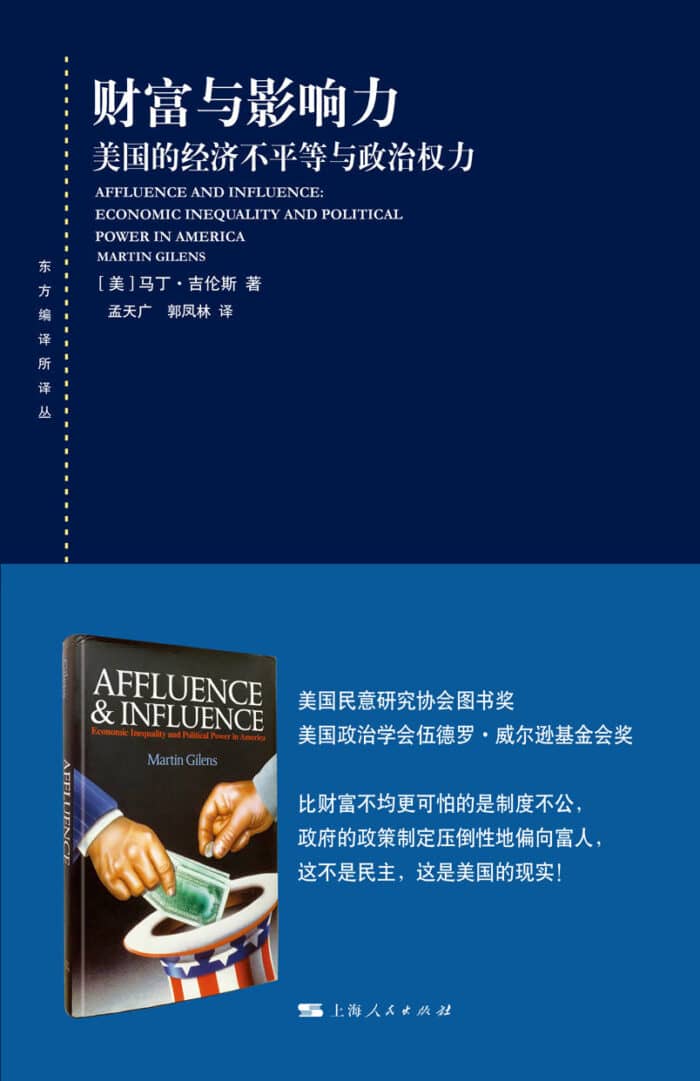内容简介: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是青年作者杨潇的新作,也是单读出版推出的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关于一个不无困惑的写作者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
1938 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2018 年,处在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作者杨潇重新踏上这条 1600 公里长路。这是一次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旅行,不时要与大货车擦肩而过,但沿途山色、水光、鸟鸣、人语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渐渐重叠、交织,乃至对话、共振,一个层累的、被忽视的“中国”缓缓浮现。
杨潇带着海量的史料积累与强大的问题意识,与沿途遇见的人交流,与西南的人文风光交流,与那个遥远的动荡时代交流。在两个不确定的年代,在国家与个人的危机时刻,我们用真实的生命体验,追问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开启一个全新的“寻路之年”。
作者:
记者、作家、背包客。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2013-2014哈佛尼曼学者。从2010年起周游世界,尝试一种融合时事、历史、智识讨论与人文地理的叙事文体。作品两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三次获腾讯华语传媒年度盛典单项奖。曾出版个人作品集《子弟》。
试读:
出发
公路徒步的意义
一路向西—传奇的起点—寻路之年—最有前途一省—徐霞客和林则徐—我并不认识自己的国家—尚能走否—历史的失踪者—真正的中国灵魂—冷暖空气—农妇走过田埂
这个42升的登山包比我想的要小,塞进一件冲锋衣,一条速干裤,两套贴身换洗衣物,一件防晒衬衫和一双拖鞋,就只剩下一小半空间。拖鞋不是非带不可,但不知为什么,当我想象接下来的公路徒步旅行时,眼前总会出现暴雨倾盆、溪河涨水,我卷起裤管、换上拖鞋、小心翼翼穿越被淹道路的画面。
我计划从长沙一路向西,以徒步为主的方式横穿湘西、贵州,然后到达云南昆明。这是八十年前一支特殊行军团的路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下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再迁云南,其中,由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五位教授包括清华的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如今西南联大早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人们熟知那些灿若星河的大师,熟知他们抱着讲义跑警报的轶事,甚至熟知他们的各种怪癖;同时人们也怀念着联大师生对学术自由的捍卫,怀念他们对知识和教养的尊重,怀念他们的理想主义——2018年1月上映的电影《无问西东》提醒着我们,八十年过去了,人们对传奇的热情并未消退,仍在借它找寻慰藉,或者浇胸中块垒。关于联大在昆明的八年(1938年4月—1946年7月),不论大众叙事,还是学术研究,都已汗牛充栋,这很好理解,因为这八年太重要了,也太长了,长到足够一所大学变成一座“民主堡垒”。比较起来,为什么要关心八十年前一次仅仅持续了两个月余的行军?
很简单,因为那是传奇的起点。旅行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曾经抱怨,为什么那么多书,从一开头就把读者放到异国他乡,却不负责带领他前往?How did you get there?没错,你是怎么抵达那儿的?当我面对“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时,问自己的正是这个问题:How did they get there?这所学校是如何在战乱中点滴成形的?迢迢长路,他们又是如何抵达昆明的?
每个人都对“路”有自己的记忆和情感,而抗战第一年正是中国人的“寻路之年”。平津沦陷后,大批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南下,以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家为例,他们从北平出发,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从天津起,一家老小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1]。等到战火在长三角延烧,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汉口、长沙又成了“后方的前方”,大批人口要向真正的大后方——西南的川滇黔三省撤退了。
西进从来不是坦途。长江水道有三峡天险,陆路方面,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路险难行,元初修筑的由湖广通达云南的“普安道”在很长时间内是沟通西南与中原最重要(有时是唯一畅通的)的驿路,当年朱元璋30万大军西征云南、徐霞客从贵阳西行游历(比湘黔滇旅行团的徒步恰好早了整整三百年)、林则徐两次入滇就职,走的都是这条路,更不必提往来的马帮、赴京赶考的学子和被贬谪边地的官员。甚至到了1938年,有时候为了抄近道,湘黔滇旅行团也要踩着坑坑洼洼的石头,走上一段驿路。不过在1938年,不论是林徽因梁思成,还是湘黔滇旅行团,和徐霞客们相比至少有一个优势:1937年3月,从南京到昆明的京滇公路已经全线打通。
京滇公路全线打通意味着国民政府“统一化”政策往前迈进一大步。中国大陆过往研究,多将“统一化”斥为蒋介石与半独立的西南军阀争夺权势,借追击红军之机修筑公路,将势力伸向西南腹地[2],但论者往往忽视了“统一化”对于国家认同及抗战所发挥的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时,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国民政府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长江下游诸省,在“统一化”政策的推动下,西南地方军阀势力逐渐削弱,或与中央政府加强合作,1936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3]。
1937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组织“京滇公路周览团”一行180人,包括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商界代表、新闻记者等等,乘坐近20辆汽车,从南京出发,沿刚刚全线通车的京滇公路,一路向西,开中央考察团访问西南边疆地区之先河。50天的行程下来,京沪地区掀起了解西南的热潮,云南被舆论视作“最有前途之一省”,而周览团沿途不断发表演讲,播放电影广播,也增强了西南各省民众的国家认同,“中央政府在云南人的心目中已不是虚无飘渺的幻影了”。此后,蒋介石和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云南尤其是昆明成为抗战稳固的大后方。[4]
1938年2月,湘黔滇旅行团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公路向昆明行进的。这次旅行是一大群久居平津的知识分子徒步穿过中国偏远贫穷的西南地区,美国学者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里说,“穿越内陆的想法吸引了渴望深入群众的民粹主义者,也吸引了准备以抗日的名义发动穷乡僻壤的群众的积极分子,还吸引了充满好奇心或热衷冒险和体能挑战的人”。[5]在这条公路上,他们会不断遇到平津书斋里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人,会同时看到京滇公路周览团和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迹,会与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部队和车队相向而行——这条公路(后与滇缅公路接通)也是战时运输最重要的动脉之一,最终他们会亲眼见证中国西南地区的(至少部分)真相,“……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这是出发前闻一多摇着头说的话,“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大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山区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6]
查询闻一多这句话的出处时,我恰好在重读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横越美国》,1960年,这位美国作家以58岁之龄开始他的穿越美国自驾之旅:“我住在纽约,或者偶尔在芝加哥或者旧金山蜻蜓点水式地稍作停留。我发现其实我并不认识自己的国家,身为一个书写美国故事的美国作家,事实上我写的全都是记忆中的美国,而记忆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残缺不全、偏斜不正的储藏所。我已经许久未曾听过美国说的话……我对所有变化的知识都来自书本与报纸,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感觉过这个国家了。我已经许久未曾听说过美国说的话,没有闻过美国青草、树木以及下水道的味道,没有见过美国的山丘与流水,也没有看到过美国的颜色与光线的特色了。”把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替换为北京、上海、深圳,把书本和报纸替换为微博和朋友圈,你会发现我们的处境并无不同。线上线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从微博热搜、刷屏公号和抖音快手里观看一个支离破碎的奇观式的中国——是时候换一种观看方式,用脚丈量一下广袤真实的大地了。
回到1937年的夏天,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最出色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对于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那一代人,他们可以不必选择南下西进去大后方,他们可以留在故都或者避入租界(事实上一些人就是这么做的),或者干脆出国。对于学生这一代,他们面临的是读书还是救国这一更困难的选择,而当他们为自己的苦闷心灵寻找出路时,去重庆/昆明/成都,还是去延安也是一个难解之题。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近300名学生,实际上是两次回答后筛选下来的结果(他们都选择了前者),就像易社强说的,“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7],但这不等于他们在当时没有纠结和困惑。我好奇,在传奇故事外,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爱好和偏见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和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他们的情感结构如何养成?在前往昆明的公路上,他们每天都在与西南各族民众接触,这又会与他们自己对“国家”与“人民”的理解(这种理解在1930年代北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不断发生演变)产生怎样的共振,乃至彼此影响?等他们到了昆明,被刷新的认知,连同他们的日记,以及陆续出版的散文、诗歌和回忆,又是如何构成某种不乏神话色彩的“文本”,进而注入西南联大这一精神共同体并绵延至今?
当然,对于出发,我还有更私人的原因。我热爱走路。走路,尤其是长距离的徒步,是我衡量自己也是挑战自己的一把尺子,对我来说,那个永远重要的问题不是“尚能饭否”,而是“尚能走否”。多年记者生涯,我已习惯写不出稿时下楼暴走一通寻找答案,走路是我和自己相处的重要方式,走路时我能清晰地感到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头脑也变得清明——哪怕在雾霾深锁的北京也是如此——我已经记不起多少次在行走中触摸到故事的内核,找到长文的结构。但是眼下,我36岁,迎来了第三个本命年,距离我辞掉工作、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了,我正陷入某种存在主义危机。原先的两个写作计划,一个被证明行不通,另一个因为近乡情怯迟迟无法推进。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越来越感到被奇怪的引力拖拽着漂移,生活像永远对不准的指针。我需要一次真正的长时间的行走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这也是我的寻路之年,我迫不及待地要和八十年前那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一同出发,激活曾经的简单、热忱与少年心气,同时,也冀望着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银线能牵起1938与2018这两个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年头——譬如,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
查看旅行团成员名单,你会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他们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作家、工程师,成为两院院士,我好奇他们最终找到自己的桃花源了吗?我也好奇旅行团中“历史的失踪者”,比如清华政治学系大三学生施养成。他1939年在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出版了《中国省行政制度》,钱端升、王赣愚为其作序,应该是颇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后来他赴美留学,1957年回国,根据我查阅到的新华社电文,他和几个同学3月18日抵达广州,逗留数日后分头前往北京、上海。此时距反右运动开始不到三个月,我也再未查到施养成的下落,直到翻阅了清华十级毕业50周年纪念刊(1938—1988),级友简况里有语焉不详的交代:(回国后)在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室任副研究员,1971年在河南南平该院五七干校受迫害含冤去世(时年55岁)。
所以,如果我们把视野再往后推一些,我还会好奇,他们的这次公路徒步经历,对他们之后人生的各种选择——譬如,走还是留,去国还是还乡——是否有过影响?对那些选择留下和回国的人来说,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是否让他们想起这次与“真正的中国的灵魂”的接触?“真正的中国的灵魂”这一表达来自旅行团成员、清华历史系大四学生丁则良1943年写的一篇文章[8],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专文回忆了这位杰出却早逝的同窗,“1949年秋冬之际接到他致我的最后一信,内中非常激动地说,英国费边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他已急不能待,放弃论文,马上就要回国报效了”[9]。
清华大学外文系大三学生查良铮也在旅行团中,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穆旦。在我所就读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小花园里,几年前立起了这位著名诗人的雕像,小花园也被命名为穆旦花园,听说,因为历史问题,雕像立得还颇费周折。2018年是穆旦诞辰百年,八十年前,20岁的查良铮在出发前购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每日坚持背单词和例句,背完就把那几页书撕掉,等走到昆明,刚好把字典全部背完。直到打包之时,我还想着带一本英文小词典向他致敬,最终不得不因为减负舍弃,一同舍弃的还有吹风机、护膝和护腰——我揣摩着,这一路虽然漫长,大概不至于艰苦?
这里是4月初的湖南,冷暖空气仍在纠缠较量,前几天气温冲到了34度,一夜间又陡降到非穿毛衣才好——全省都处在这种不稳定的天气中(我又往包里塞了一件羽绒背心)。根据预报,贵州的天气倒是非常稳定:稳定的无休无止的阴雨绵绵,到达云南之前有可能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再往包里放把雨伞和一个便携式干衣机),不要紧,反正我会在云南不限量供应的日头下把自己烤干。
我将要走的这条路,现在主要由319国道和320国道组成,它们大致和当年京滇公路湘黔滇段重合。人不可能踏上同一条公路,但公路之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联结历史与现实的载体。“重走”一条八十年前的老路,不必奢望见到多少往日景象,但若要解答我对寻路之年的种种好奇,没有比公路更好的空间了。
我塞进登山包里的最后一样东西是北大教授张寄谦所编,厚厚的一本《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这本书不算专著,但却是关于旅行团相对完整的史料汇集。书是时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秘书长曾骥才送我的,我们恰好是同乡,出发前我去未名园拜访他,他领着我进储藏室取校友通讯,那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很多东西都堆在箱子里,没来得及整理,包括曾骥才在内的校友会几位工作人员都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做不动了!”塞进这本书后,42升的包已经鼓鼓囊囊,估摸着有三四十斤,背起来颇有点吃力。我背着这个大包去吃早餐,要了最喜欢的杂烩粉和生煎包,大约是惦记着沉重的肉身,吃起来也不如前几天香。
在车站与家人道别,坐上开往长沙的高铁。这一天是2018年4月7日,大片的青灰色和紫色在窗外飘过,紫的是紫云英花,青灰的是刚刚结籽的油菜田,素色衣服的农妇走在嫩绿的田埂之上,白鹭浅浅翱翔,水塘泛着天光,我的旅行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