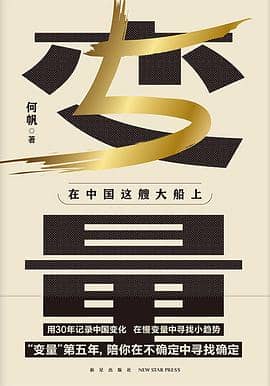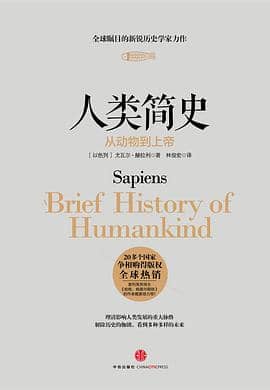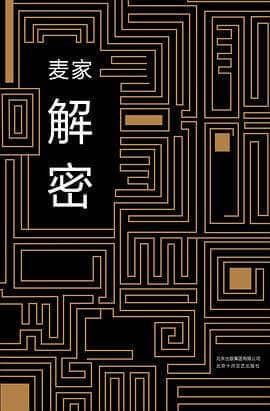作者:
沈大成,作家,文学杂志编辑,在《萌芽》杂志开设有短篇小说专栏“奇怪的人”。著有短篇小说集《屡次想起的人》与《小行星掉在下午》,作品两次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并以《小行星掉在下午》登上豆瓣2020中国文学小说类年度榜单TOP10。
内容简介:
这是青年小说家沈大成的新作品,新作中她秀异的想象又多朝前走了几步。
在星空剧场打瞌睡醒来却洞悉了宇宙奥义的人,早已废弃却始终与居民共生的小镇百货公司,世界上后一个移动部落缩小巨人,不满足在固定位置工作的人行天桥,负责看管星球大战战备物资的仓库值班员……
15个失去导航的“宇宙人”故事,看似魔幻奇诡,但却与我们的真实世界有着不绝如缕的联系。作家唐诺形容新书《迷路员》:“沈大成的想象文字不惊不乍。总是如博尔赫斯所说用平静的话语讲一个一个神奇的故事。神奇发生了,但人是真的、实的……”
作为同时代中独树一帜的青年小说家,沈大成再次以她专属的华丽想象描绘了我们时代的异样日常与生活困境,“这个真实世界也许并不值得人如此眷顾,但终究,这是我们真正有的。”或许在沈大成的文字中,想象能成为我们的“突围之路”,而非一阵烟花。
编辑推荐:
受广大上班族喜爱的沈大成继《小行星掉在下午》后作品集。以奇崛的构思、秀异的想象讲述十五个失去导航的“宇宙人”故事。
本书是作家沈大成新作品集。过去几年来她的作品持续引发广大上班族“打工人”的共鸣,发现这些看似荒诞的奇人奇事均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收录于前作《小行星掉在下午》中的故事《盒人小姐》甚至意外地“预言”了一个社交隔离、打疫苗成为常态的世界。
新作《迷路员》聚焦十五个失去导航的“宇宙人”故事,再次呈现我们时代的异样日常:在星空剧场打瞌睡醒来却洞悉了宇宙奥义的人,早已废弃却始终与居民共生的小镇百货公司,世界上后一个移动部落缩小巨人,在办公楼花园中躲藏数年的离职员工,不满足被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人行天桥,负责看管星球大战战备物资的仓库值班员……这些非科幻非外星非奇幻非魔幻的故事,关注的均是宇宙中的各种存在。
“我们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当然也有点知道在干什么,说我们不占有任何身份也不对,我们起码是迷路员。迷路员就像一个工种,得认认真真地干好它。”小职员作家沈大成有条不紊地想、仔仔细细地编织,又一次完成了非比寻常的想象之旅。
两次入围青年文学奖短名单。作家苏童、唐诺推荐,“我是沈大成的读者”。
沈大成以出版的两部小说集《屡次想起的人》《小行星掉在下午》两次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短名单,获得两届多位评委专家的肯定。她的作品在同代作家中风格鲜明、独树一帜,以专属的奇思妙想描写当代的生活现状和心理困境,关怀这个我们真正拥有的世界里那些“人”、那些物。
作家苏童认为《迷路员》“想象力放松、开阔,摸不到边”。作家、评论家唐诺为《迷路员》手写数百字推荐语:“……沈大成的想象文字不惊不乍,总是如博尔赫斯所说用平静的话语讲一个一个神奇的故事。神奇发生了,但人是真的、实的。仍保有几乎全部人的生命基本细节。因此,她的文字时时处处自成隐喻,给我们一种屡屡回首的感觉。这个真实世界也许并不值得人如此眷顾,但终究,这是我们真正有的。”“我是沈大成的读者。”
试读:
知道宇宙奥义的人
有一天,年轻的男女朋友在一个科学馆约会。科学馆的造型是这样的,两侧各有一个立方体,中间夹住一颗硕大的球体。立方体内部是展厅。球体内部有一座圆顶大剧场,人们叫它天象剧场,里面播放四维星空影片。看星空影片是科学馆的人气项目。
午后,年轻的男女朋友先到两个立方体里面,在各层楼看了各种标本、模拟实验、互动式展品,它们有关地球起源、生命进化和人类科技,涉及生物、物理、化学和气象等多个学科。在科学馆约会有很多好处,路无止境,不缺话题,顺便补充知识。这里情侣很多,很多有孩子的家庭也来这里度周末,以后这些情侣就可能变成这些家庭,因此还可以说在这里约会有预见未来的好处。后来到了预约的影片放映时间,男女朋友和同批观众排队进入大球内部。
天象剧场中,四百余人在绕圈排列的座位上坐好,视线投向斜上方,等一等,星象仪会把浩瀚星空投影到大家头上的圆顶天幕。剧场暗了,讲解员柔和的声音响起,提示影片即将开始。宁静的几秒钟缓缓过去,几枚流星从圆顶上倏忽滑过,巴赫的《C大调前奏曲与赋格》骤然响彻剧场。多年前,曾有两颗探测器携带铜质镀金唱片远航深空,向宇宙传递地球之声,巴赫的钢琴曲就在唱片收录的几十首名曲之中,它会在外星文明找到新的倾听者吗,也许吧。此时听着巴赫的四百余人,仿佛脱离地球,身随探测器,飘荡在外太空。人们看到一条扁的光带飞来,也像自己正朝它飞去,当光带越来越大,越来越靠近时,如同海里的蝠鲼悠闲地翻转身体,不再用相对薄的侧面对准人们,而是展示自己另一个极为庞大的面。人们怀着迷惑和敬意注视它:那个面上有一个大旋涡,组成旋涡的是无数颗发光的恒星,它是我们的银河!一认出来,观众席轻声哗沸,又安静了,因为人们与银河的距离更近了,银河开始填满整个剧场的上空。由于宇宙没有天然的上下概念,既像银河当头坠落,又像人们连同椅子朝它倒栽下去,不管怎么说,最终人与银河交汇了,星星几乎压在每个人鼻尖上。
男朋友在那时还很清醒,但是他昨天工作到很晚,随着银河在眼前变幻,过多的星体使他疲劳;巴赫之后,响起讲解员极具掌控力的声音,引导观众观测星象,过多的陌生名词也使他疲劳,他睡着了。
也有别的观众睡着了,每场星空影片都令一些人失去意识。人不可能对抗宇宙的威力对吗,人应该在宇宙中自觉虚弱对吗,睡觉或许是这种心理的体现。可别人不那么容易立刻打起呼噜来。在接下去的三十分钟里,女朋友一直负责地与他手牵手,一旦听到呼噜声,便抠他手心,帮他醒过来。他屡次在银河下清醒过来,可是他老是怀着对女友的歉意,马上又在银河下睡过去了。
其中一次醒来后,他先用两边肩膀交替着往椅背上蹭,使自己坐正,同时回握一下女朋友的手,又偏头向她看过去,尽管自己不争气地总要坠入睡梦中,可这样并排坐着牵住手,他确实感觉永恒而且甜蜜。他向她一笑,强撑着继续看影片。事先他已经从科学馆的图文资料上得知,星象仪能投影出1.4亿颗星,面前的星星正像灰尘一样多,但有几道活动的金光在为他摘出重点。金光从一些星流向另一些星,串联出若干个有人有兽的图案,他听见讲解员介绍星座名称。便在此时,他感到一股由太空发射来的力量将自己强行按在地球上科学馆的椅子里,他头一仰,肩膀撞击在椅背上,某个讯息霎时间进入身体。他心头震骇无比。他想分辨究竟:那是什么?可来不及了,睡魔的黑暗之嘴又靠拢过来,俯在他头顶,将神志从他身体里一口吸吮掉,那天它一遍一遍地吸吮他,他刚刚瞪大的眼睛又无力地缩小,闭住了。那是什么?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想。那应该是重要的事。但那是什么?
银河退远了,剧场的灯光重新亮起,大家又被允许自由交谈了,谈着对影片的体会,有秩序地撤出剧场。男朋友彻底醒来后,怔怔坐着,女朋友觉得他模样可爱,像瞌睡的家养宠物,他僵硬地扯动嘴角。他们差不多是最后离场的两名观众,依然紧拉着手,可女朋友觉得他手上失去了力气,麻木无情地被拉扯着,对刺激绝无反应。他们回到立方体中,草草再看了几件展品,走出了科学馆。天色刚近黄昏,别的情侣还在约会。
第二天,他整个人提不起精神,以后每一天都更消沉一点点。女朋友还用别的词描述他:懒洋洋,不振作了,萎靡,松松垮垮的。她对自己的朋友讲述了男朋友的变化。
“什么原因呢,从前不是很活跃的人吗?”友人不解。
“我说你有什么事,工作方面的事?钱的事?家里的事?——不就这几种事吗,哪里有问题?他不愿意讲,后来终于开口了,他说因为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宇宙,”女朋友说,“在科学馆里。”
“科学馆?我们也去过。科不科学的,说真的我没所谓,但当时我们两个都想表现好一点,我装作津津有味地看标本、骷髅、化石,假装爱它们,后来又看了一部无聊影片。”
“看完后,你男朋友没有变化吗?”
“好像没有,我们都没有变得更有智慧。”友人问,“他就是在那儿看了一眼宇宙?”
“对,就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
“神奇。”友人想了想,提醒她,那会不会是男人耍的烂招?表面包装成宏大叙事,里面极度可笑,“用地球、宇宙、银河鬼扯一通,说他好像感知到巨大能量,从此觉得人生意义不一样了,所以他反常、痛苦、消极,他克服不了,就从你身边慢慢退开。他们每部漫威电影都看,熟悉超级英雄的套路,你想想,可能是无耻地借用到他自己身上了。”
“这也太幼稚了,男的真是……”但女朋友不认为是这样,她觉得男朋友的表现更像应激反应。一个人经历过一件事,再次看到相关画面容易犯毛病,比如一个人经历过战争、车祸、大屠杀、暴力犯罪,多年以后还可能碰到新的事情引发他永不痊愈的心理创伤。不过她禁不起友人的连连嘲笑。
“他经历过什么,难道他打过宇宙战役?难道,你交往的人是一名宇宙老兵,看一眼剧场里的星星受到了刺激?”友人说。
“我不知道,”女朋友不确定地说,“也是有可能的吧。他那个样子你看了就会有自己的判断。”
这是哪里?他想了足够久才问出口:“这是哪里?”
他又问:“我在做什么?”
他得到一个嗡嗡声,过了一会儿,听出来是边上有人回答了他。按回答所说,这里是市民公园,眼前那片发光的平面是公园里的湖泊,水面闪烁的地方是夕阳正在下沉的倒影,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用面包喂鸟。他挨个往那些东西上看,大鸟嘎嘎叫着在头顶胡乱飞,没有错,都对上了号。
他又向身边看,他明白过来,是一个流浪汉回答了问题,自己几时与他为伍的呢?“谢谢。”他谢过他的信息。一阵黑风刮到手上,有只大鸟叼走了最后一点面包屑屑。“喔哦!”鸟振翅飞走后,他才不带感情地惊呼,后知后觉地垂下头,见到十指微卷掌心朝天,像两个空容器废弃在腿上,当他再抬头寻找鸟的踪迹时,那鸟早已与鸟群汇合,分辨不出来了。
“朋友你还好吧?”公园流浪汉问这位迟钝的新朋友。
流浪汉可能三十五岁,也可能五十岁。很瘦弱,不能算脏,叠穿好几件单薄的衣服御寒,半野外的生活晒黑了他,营养不良又造成苍白,黑与白最终调和出灰败的脸色。他才是需要关心的那一个,但是此刻关心着别人。
“我?”他说,他不知从何说起,“我刚才一直在这儿吗?”
“不,你在大树下走,在不同的大树下走。后来在桥上来来回回,不断往水中看。再后来走到了人家练习长跑的那圈小道上。再后来你到了儿童游乐区附近游荡,定定地看着几个孩子,警惕性高的父母都瞪着你,当然没有一直瞪着你,因为他们也瞪着我,所以我走上去把你带到这儿,给他们儿童乐园,给你一片面包。你都不记得了吗?”公园流浪汉指指自己的头,“朋友你这里是不是?……那你有没有监护人?”
“我没有监护人,我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缓慢地不卑不亢地说,“记起来了,你一说就全部记起来了。我没有傻,之前有一点儿失神。”
他还记起来,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他没有去上班,或许昨天也没,前天也没。是的,都没有。上午还很早的时候,手机在桌上振动,静止后,他拿起来看到公司来电。未接来电里有多次公司来电、客户来电、女朋友来电,女朋友的来电特别多。他很抱歉,对进行到一半的工作项目,对等待回复的客户,对曾给予自己永恒与甜蜜感受的女朋友,他都不感兴趣了。手机又开始振动,他把它收到抽屉里,而后走出房间,他对这个房间里的生活也失去了兴趣。来到外面,他对眼前的街道也没兴趣,便一直往前走,筛选自己尚感兴趣的事物,但是没了,都没了。世界已经从那天起与自己切断了亲密的联系,他感觉一切都是疏离的,麻木不仁地路过很多地方,路过很多人,最后到了公园。
“天黑了啊。”公园流浪汉说着撩起最外面的衣服,往内层衣服的口袋中掏了掏,拿出一片白色的东西,“前面给你的面包你给了鸟,吃了这片就回家吧。让我打个电话给你的监护人。”
“我没有监护人可以打电话。”他阻止流浪汉再一次撩起衣服往里面摸索,“请不要找硬币了。”
光线变暗,湖水变成深色,鸟已经不在空中乱飞,回到树上的巢中仍在大声喧哗,公园里散步遛狗带孩子玩耍的人们统统消失了,除了是夜跑者的道路,这里只是流浪汉的家园。两人站起来,他满不在乎地一面吃发酸的面包片,一面跟随流浪汉走向营地。路之漫长险阻几乎到了需要跋涉的程度,直入公园最深处,再往一片树林里面走,到了树林底部,一些树木之间拉着绳子,衣服和杂物挂在上面,它们起到了东方餐厅门口挂帘的作用,连续拨开几层后,若干露营帐篷、纸板卧室出现在面前,和任何一片住宅区一样,这里经过初期规划和使用中的自然发展,看来非常和谐,与公园融为一体。
流浪汉指向其中一处,是一个用多种材料拼贴过的帐篷。“你现在认识我家了。”
他待了一会儿,转身离开营地,逆向穿过树林。林中偶尔传出神秘的响动。那不是夜间动物,他想,就是别的流浪汉正在摸黑回家。
没过两天,他又去了公园。进一步变长变乱的须发使他从外形上比较接近流浪汉了,他坐在小帐篷门外,就像坐在自己家门口般自然。他把一个袋子递进去,裹在睡袋里的流浪汉伸出手接了,刚刚拧亮的露营灯照着礼物,是一整袋切片面包。
“你只拿走了两片,用不着特地来还那么多。”流浪汉说。
“还有这个。”他又递进去一瓶巧克力酱,接着是一瓶小红莓果酱。
它们连同面包都被摆在睡袋旁边,流浪汉的手缩回睡袋里了,他躺着,露出一张睡眠被打断后疲倦的脸,头发散落在地。现在是早晨四点多,顶多五点钟,天还很黑。所以流浪汉问:“你睡不着吗?”
“在家躺过一会儿,我现在对睡觉没兴趣了。”他说。
“那帮我关上门好吗?”流浪汉说。
他钻进帐篷里,拉好了门口牛津布上的拉链,随后蹲在地垫上抱住了自己的膝盖。地方那么小,他们近距离地看着对方。
“嗯?”流浪汉说。他们又无言地互看了一会儿。
两人喝上茶大概是在二十分钟以后。流浪汉被迫起来了,套上多层薄衣服,用一只汽油炉烧水,往杯子里扔进茶包,往面包上涂果酱,太早太早地吃着早饭。帐篷的门又打开了,他们的屁股挤坐在帐篷里,腿伸到寒冷的室外。他在流浪汉吃面包时,只喝了几口茶。别的帐篷里有人发出梦中呓语,有座纸板小屋有节奏地摇晃,因为蜷缩其中的人彻夜发抖。天还那么黑,星月的光辉从枝叶间朦胧洒落。
“这像野餐。”他说。
“这是啊。”流浪汉说。
“我本来会到得更早。”来野餐的客人诉说他今晚的经历,“我出门是想找人聊聊天,想到了你,猜想你和我一样醒着,假如你当时睡了,那么我猜想你将会醒过来。第一次,我走进树林中,离你不太远了,忽然回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父母不知为什么决定全家去野餐,我们一向缺少像样的家庭活动,那时候可能是春天,可能是秋天,地方不记得了,可能是山坡或河边,具体做了什么也忘记了,我最小的妹妹那时一起去了吗,想不太起来。可是,回忆虽然模糊,但是留下了非常有意思的感觉——大家都在笑的,甜津津的,风吹啊吹,后背全部湿掉的,那样的感觉。我站住了,想象与你待会儿一起野餐的画面,因为什么都没带,我又原路走回去了,走到树林外面,走到公园外面,但店都没开门,最后才找到了一家24小时便利店。”
“你第一次来是几点钟?”
“两点多,大概三点钟?”
“你的一个想法让我多睡了一个钟头,谢谢你朋友!”流浪汉吃着面包说,“现在你找回小时候的感觉了吗?”
“不,我找不到了,我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再也没有那种有意思的感觉了。”
流浪汉又一次仔细端详他的脸,见他比前两天明显地消瘦下去,神情平静淡漠。流浪汉问:“你有医保吗?我觉得你最该和医生聊聊,去关心一下抑郁症。”
“呵,不是生病。”他毫无快乐地笑了,把不久前和女朋友约会,去科学馆看星空影片的事情大致讲了,讲到偶尔瞥见宇宙中的一幕,他说,“这就是我被改变的原因。”
“具体是什么呢?”
“我忽然洞悉了宇宙。”
这时,借助露营灯和微弱的自然光线,流浪汉在这个凌晨第四次仔细看他,他不像在说笑。
“人们会说,那是星星投影在你买票就能进去的剧场里,同样的内容一天放五场,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确实是的。但是,宇宙就是用它为介质,在那时裂开一道缝隙,向我释放了信息,内容是宇宙的奥秘、真谛,或者说一种最深刻的道理。宇宙也可能一天五场、一年三百天向所有观众释放信息,只是恰好被我捕捉到了,我恰好把握了那样一个看见它的契机。离开剧场后,以宇宙为参照系,我看向身边任何熟悉的事物、人间的关系,都失去了感觉,一切变得没有意义了。我是这样被改变的。”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
“一个知道宇宙奥义的人。”
他们都不响了。流浪汉用勺子掏掏果酱瓶子,放进嘴里抿,整理着思路。“朋友,”后来他问道,“宇宙到底对你说了什么?”
回答是半声哼笑。紧跟着,一只鸟开始清晨第一声鸣叫,一串鸟都从林间回应它,天在这瞬间放亮了,晨曦射入公园树林。在越来越亮的光线中,流浪汉头一次看到他的新朋友脸上流露出情绪,那是遗憾。
“我不能说出来。”他淡淡地说,转一转手里的破搪瓷杯。但是他并未泯灭人性,马上修正了前面的话,为的是宽解忽然垂下头研究瓶子标签的流浪汉,“不是对你保密,是因为我无法进行表达。因为,在地球上,宇宙的奥义是不可描述的,我们竟这样狭隘,没有对应的语言,比如说一个名词或一个动词去……”
“翻译?”
“对,翻译它。没有标准线,去判断它在以上还是以下。没有一种图形可以画出它的形状。既无法对它定性,也无法用一个办法测量它。它是宇宙级别的奥义,即便向我慷慨揭示,我也不能将它转化为别的什么。”
“你掌握了那样一种东西,对它什么也做不了。”
“是的。”
“现在装作不知道也不行了。”
“是的,不行了。”
两人说到这里,别的流浪汉陆续起床了,由于大家在夜间住得那么低,此时仿佛集体由地穴的各个出口爬出来,起先站立有困难,打着晃,之后在舒展肢体的怪动作中勉强站直。他们在营地走来走去,轮流张望一下两人在做什么,新出现的人令他们面露狐疑。
这天以后,他经常来市民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