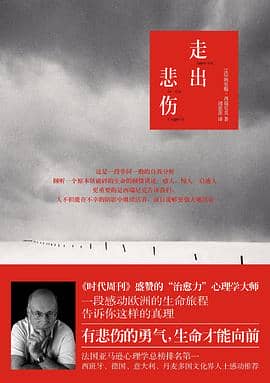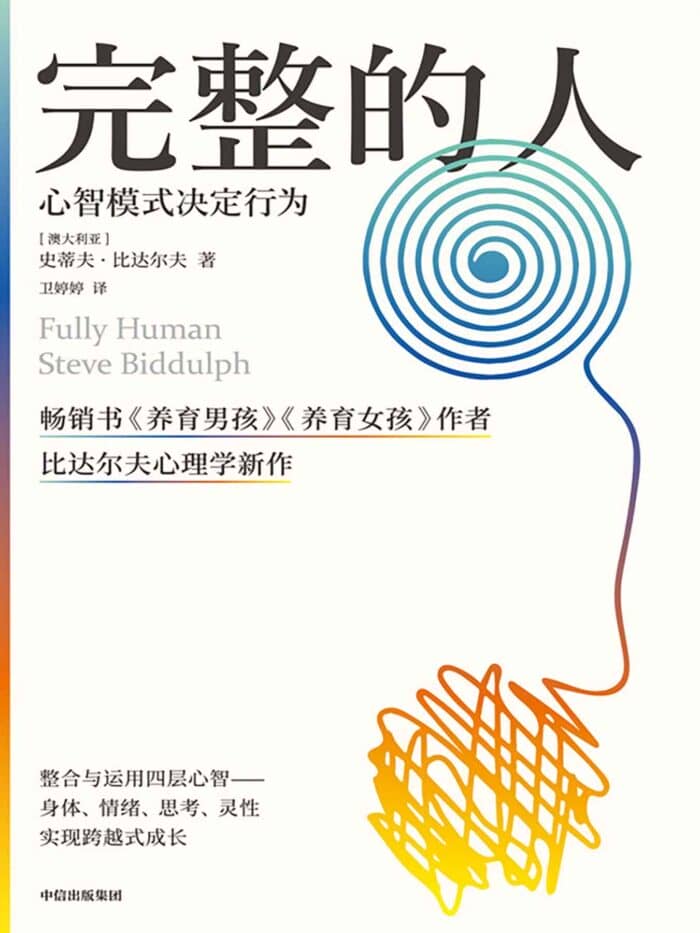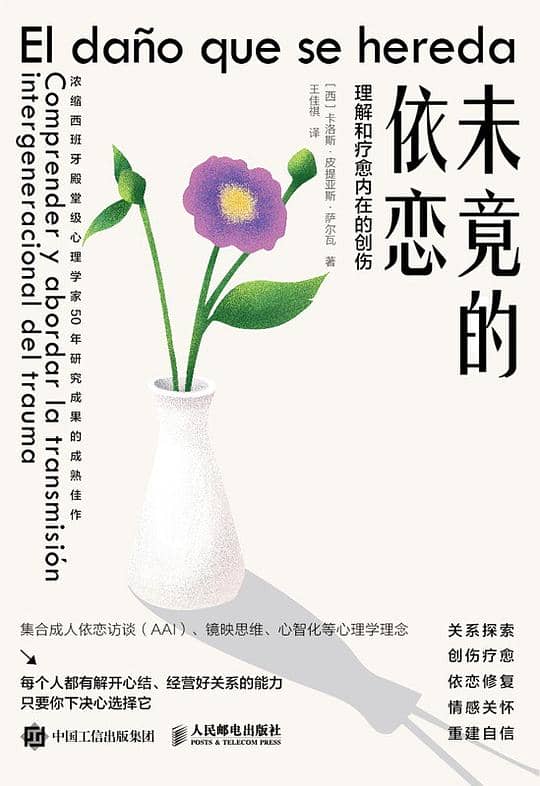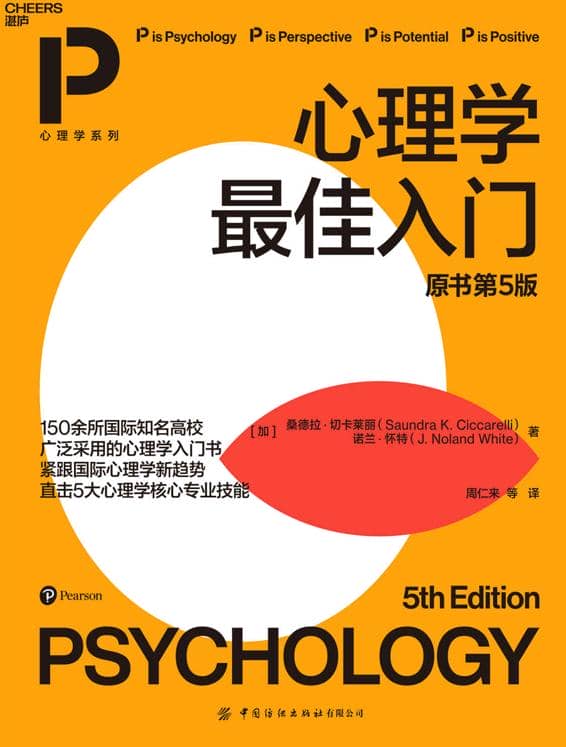内容简介:
幼童西瑞尼克从有记忆起,就被纳粹追杀,父母在1942年双双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心脏的位置上像是戳着一段木头,脑子像一堆稻草”,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可怕、骇人的怪物。直到一位女教师收留了他,庇护照料他整整一年。此后他逐渐开始走上心理学研究之路,进行系统学习,探究人类创伤后重建自我的秘密。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治愈了自己,最终成为了心理学家西瑞尼克。
这本书中,心理学家西瑞尼克不惧自我解剖,他努力搜寻那些已被埋藏的记忆,质问那些记忆的陷阱,并试图说出在重获安全和自由之后想说而无法说出的感受,探求走出悲伤的心路历程。他以自身经历告诉那些心中有伤的人,走出悲伤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和他人保持重要的良性联系,二是相信生命与生俱来的内在能量。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的悲伤和命运的曲折,是生活在这尘世中无法避免的修行,我们不能阻止和压抑自己的情绪,但可以选择与悲伤相处,克服悲伤的力量。
人不但能在不幸的阴影中继续活着,而且能够更强大地活着。
—— —— —— —— —— ——
《走出悲伤》,一位世界级心理学大师的生命剖析。
作者简介
【法】鲍里斯•西瑞尼克(Boris Cyrulnik)
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人类和动物行为学家,土伦大学教授,在欧洲领导着多个学术前沿的研究室。以在心理创伤方面的研究享誉世界。
身为一个犹太人,他童年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朋友,生活自此动荡,七岁的他作为孤儿还被特意安排越过敌军的封锁给法国军队送情报。直到二战结束,他的世界才得以静下来。
此后他接触到心理学,开始进行系统地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了自我,治愈平息了过去的回忆,并最终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心理学家。
试读:
CHAPTER 1 有一种谎言叫“别担心,我很好”
我有过两次出生。
第一次出生时,
真正的我并不在场,
出生的景象在我的记忆中一片空白。
波尔多,
1937年7月26日,
我来到这个世界。
大人们这样告诉我的,
不得不相信。
第二次出生时,
一切场景历历在目。
那天晚上,
一群男人来逮捕我,
他们围在我的床边,
想把我杀死。
我的故事从这个夜晚开始。
嘘,我是犹太人
那年我六岁,“死”这个词于我而言显得过于生涩,直到我被逮捕后的一两年里,我才对死有所了解——生命不可重来。
法尔热太太穿着长睡衣,一边往我的小箱子里塞衣服,一边说道:“如果你们放他一条生路,人们就不会以为他是犹太人了。”我很震惊,这些男人显然想取走我的性命。
听完法尔热太太这番话,我明白了他们用枪指着我的缘由——我是犹太人!
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我一无所知。但就在那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活下去,就不能说自己是犹太人。
他们把我弄醒,一只手拿着枪,另一只手拿着电筒,头顶着毡帽,鼻梁上架着黑色眼镜,上衣的领子向上翻起,多么可怕的一幕!难道枪毙一个小男孩,人们就要这么打扮吗?
一个看起来像长官的男人回应道:“立刻让这个孩子消失,否则他很快就会成为希特勒的敌人。”我被判了死刑,可我不知道wo 错在哪里。
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体里催生出一个扎根于我灵魂的人影——想取走我性命的手枪,夜色中的黑色眼镜,走廊里肩挎长枪的德国士兵,那句揭露我未来罪犯身份的话语……
我即刻明白了:这群成年人草菅人命,完全不顾惜生命的宝贵。
然而,你们一定难以置信,在经历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夜晚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我不过是个年仅六岁半的孩童。1944年1月10日,波尔多的犹太人突然被逮捕,而当时的我还无法对时局做出判断,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就发生了。
对于第二次出生的经历,少了记忆 [1]之外的点醒,我很难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去年,我被邀请到波尔多,去法语地区基督教广播电台录制一期文学节目。那日天气晴朗,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我感到神清气爽。我正朝出口走,这时,陪在我身旁的记者对我说:“第一条路左转,在路尽头你会看见有轨电车车站,乘上电车你就能到梅花广场,那里是波尔多的中心地带。”
他这么说着,某些情景闯入了我的脑海:那个夜晚,那条街道,沿着人行道用篷布盖住的卡车,把我卷走的黑色汽车,武装的德国士兵围追堵截……我暗自惊讶,是什么触动了回忆的按钮,为什么往昔遥远的回忆来得那么猝不及防?
也是在录制节目这天,我约了人在莫拉书店碰面。
我来到车站,看到一栋高大建筑的白石上刻着“儿童医院”。
记忆中,法尔热太太的女儿,玛格特的告诫猛然响起:“千万别去儿童医院那条街,那里人来人往,你可能会被揭发。”
我像是被什么套住了双脚,怅然若失,停下脚步时,我早已穿过了安德烈-比斯拉街,走过了法尔热太太家门口,却全然没有察觉。
1944年后,我和法尔热太太再未谋面,不过总有一些迹象,比如石子路间的草坪,再比如阶梯的风格,触发记忆,让我想起那幕被逮捕的场景。即便心情平和时,这样那样的迹象依旧会唤醒过去的种种。悲惨的经历往往经不住生活点滴琐事的引逗,哪怕一些蛛丝马迹,也会牵扯出回忆的千头万绪。我才发现,那些儿时的经历从未被遗忘,只是自觉忘记,自动屏蔽,仅此而已。
1944年1月,从未料到我的生活会卷入这个故事。诚然,我并非唯一在死亡边缘徘徊过的人。“我感受过迫在眉睫的死亡,死亡已成为我的一种人生经历 ……” [2]那时,我年仅六岁,所有发生的一切都留下了痕迹。死亡体验铭刻在记忆中,我成长的同时它也在慢慢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