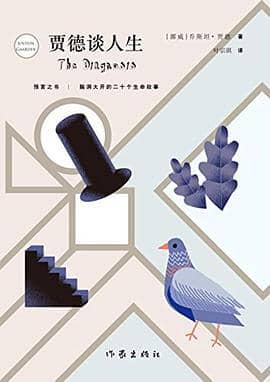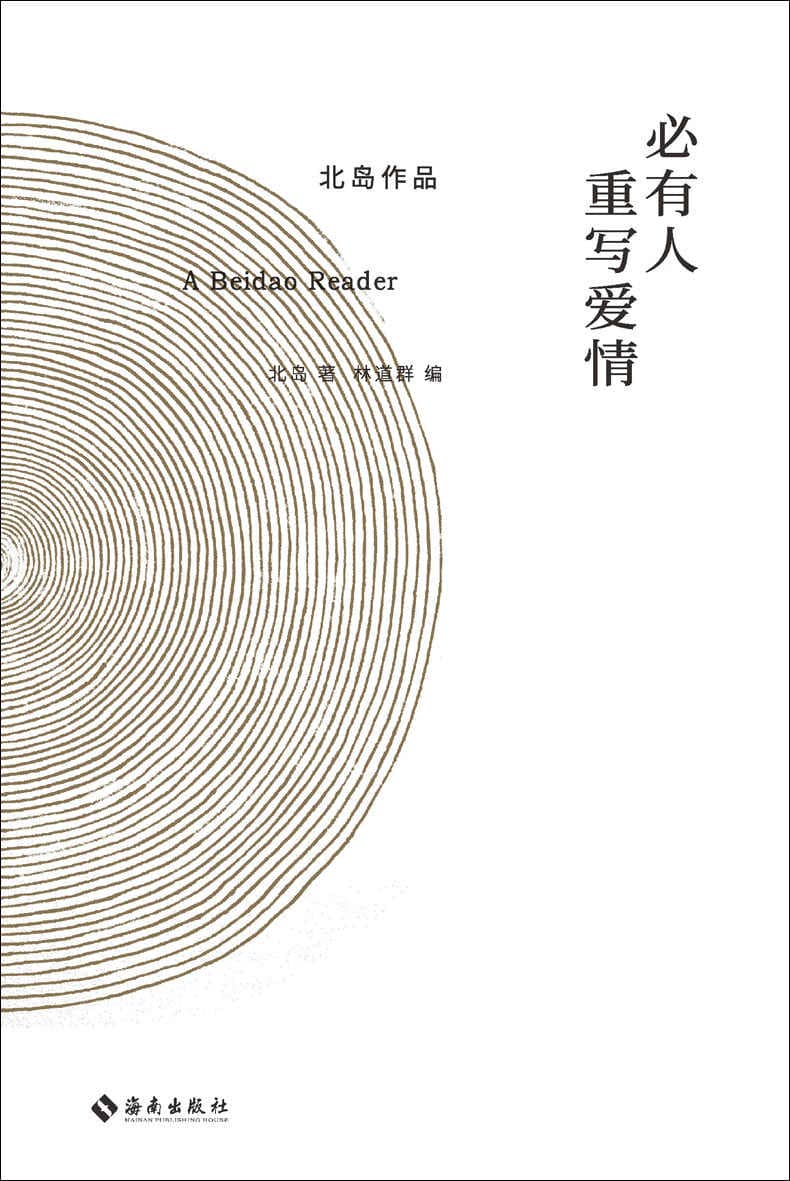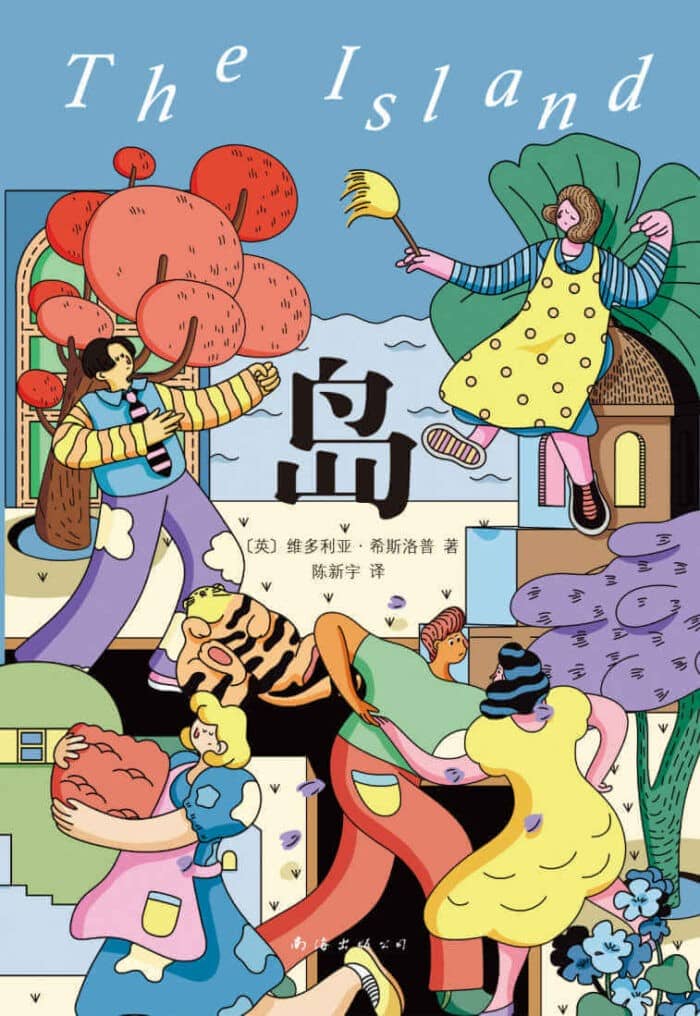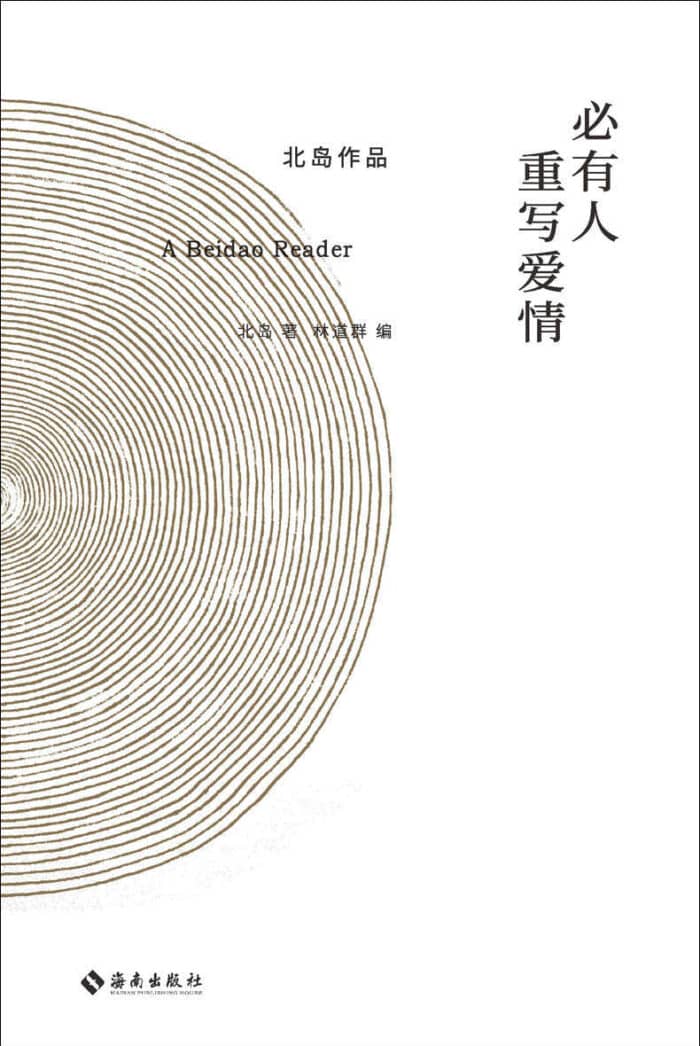内容简介:
《贾德谈人生》是一本令人脑洞大开的神奇之作,各种离奇的构想和故事发人深省。作者放任笔下的人物跨越了生与死、梦与现实、时间与永恒之间的藩篱,戏谑地逼近生命这个大课题,以富于同情、想象力十足且妙趣横生的笔调叙述故事,激励读者直面自身的存在。
《贾德谈人生》10篇有关生死的小说与10篇诗意盎然的哲思短章,交织构成了这部预言之书。作者精确预测到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三十多年间,网络时代电子科技对人类生活与文明产生的深刻影响。
与死亡相比,我们似乎更害怕活着。而害怕别人的恐惧之心似乎更大过浩瀚星辰所带给我们的惊骇。
不论我们是谁,不管我们做了什么,在几千几百年后都会被遗忘。从这个事实来看,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不要担负责任呢?我的意思是说,难道我们就不该把自以为是的这种举动,当作是自己的优点使用,使它更丰富些吗?
若生活上所有发生过的事,在未来都无法遗忘,毫无疑问,那一定会令人感到很不舒服;然而若是我们能这么想:明天——到了明天,所有的事都可以忘得掉吗?对我们而言,这不是也意味着一种几乎无法束缚的自由吗?
我并不是要呼吁大家不负责任,只是我们真的需要让自己没有忧虑;我们没有必要去想死后的讣闻要怎么写,这样便可以摆脱束缚,重获自由,活在当下。
试读:
时光扫描器
专断的意识
1.
很久很久以前,生命起源于旷野。寻求一处庇护的地方只是因为饥饿或寒冷。想要见到另一个人,必须身体力行去寻找。但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生命就在四面墙内进行时,为何我们还要往外去?
人的寿命只有八九十年,但从某一方面来看却持续永恒,因为它无法遁形于后代子孙。千年后必然有某个人可以看见我坐在荧屏前。然而我们无法经历八十年或九十年后的事,所以为何我们应该要离开房子?但人还是尽可能地想要经历所有的事。例如上星期我特别专注在越战上,一段恶心丑陋的历史,几年后又在阿富汗再度发生。但到下个月为止,阿富汗还有时间。
2.
二十世纪前半叶,一切都是从录音机开始的。一想到录音机引起当时的人何种选择时的战栗折磨,我就激动。转眼间即可以在家里接收世界各地的讯息。但如果人们当时知道日后会发生什么事的话……即使在当时,自己家中已经形成新的范围。与纽约或东京的火灾新闻比较起来,在本地酒吧或角落里的小酒馆里获得的消息到底是什么?
这倒是不言而喻。然而必须清楚分辨,录音机与现今时光扫描器之间存在着哪些引人注意的相似性?原则上可以在数百个国家中接收数千个无线电发射器。
当时有些人成为业余无线电者,意即他们购买或者设立自己的小型发射器,以便吸引世界的注意力。二十世纪八○年代初期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头的地方电台,更是说明了此种现象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地理距离却因此丧失了其重要意义。除了录音机之外,电话与电报机亦同为重要元素——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发挥了惊奇的发展力。
3.
早在录音机上市前,便开始了活动影像的实验。
众所周知的是,影片是种单面沟通的残暴形式。付钱坐进电影院,唯一可能的选择机会是在电影结束前起身离去。今天还可以估计世界对电影的兴趣到底有多大吗?
接着是电视。一九七○年电视网缠绕了大部分的世界,电影面临它的末日。每个人从此可以轻松地坐在自家的沙发上观看天下事。
二十世纪七○年代初第一批录影机也上市发行。就像以前将声音录在磁带上,现在也能同样处理活动的影像。
电视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许多旅馆房间内皆备有此项新式奇迹。电视机的进驻开启了居家生活的新纪元,每个家庭从现在开始可以自行决定收看何种影片。烟草店也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借录像带。犹不仅于此:数十年后,大部分的现代家庭都拥有自己的摄像机。
人类的生活与历史通过磁带记录储存。即使发生在街上、银行或其他有人的地方的可耻罪行也会被摄像机拍摄下来。自己的家成为最安全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做的事理所当然也比以前多得多。
与录像机齐头并进的当属所谓的有线电视,更重要的是环绕在地球周围愈见密集的电视卫星地带。二十世纪九○年代中期起,每位电视拥有者都能接收几十个电视频道,绝大部分的人有数百个节目可供选择。五十年后,电视已经赶上短波的洲际效力范围。
同此之际,录像带与电视节目的产量惊人地攀升,随时可透过电视接收数量可观的节目。就算兴趣索然——请注意我说的“就算”,架子上也会堆满没有时间观赏的故事片或纪录片。
勤奋的现实片断收集者眼前开展出一片极大的可能性。人们开始不再逗留在街道或广场上,这件事毕竟一点儿也不让人意外。那么街道还能提供些什么?
每个人在自己的房间内有个通往修身养性与启发心智的入口。
4.
二十世纪末崛起的数据革命,额外扩大了电视机的规模。
世纪末绝大多数的电视机同时具有电脑终端机的功能,电子网络的扩充将世界连接成单一通讯网。
二○三○年左右,服务业的酬劳给付、各式金钱流通与所有货物订购都可在自家进行。人类不再依赖私人录像机或录像带,也不再需要拥有自己的书籍,让它在架子上沾满灰尘。欲见欲知之事皆可使用家中或厨房里的机器,直接从资料库接收讯息。若想要报纸或百科全书上的文章、一首诗或一部小说,也可利用自己的激光打印机将之打印出来。
那时每个人可掌握过时或最新的新闻节目、老旧或新版的影片;整个艺术史以录像成品的方式流通观赏——简短地说,现在购置的特殊器材在二十一世纪前半期便已成了日常用品。
二十一世纪初期,影像电话将取代旧式的电话机。通过话筒交谈,与面对面的沟通方式仍有段差距。表情毕竟是谈话的一个重要成分。能看见喜欢的人是件好事——就像将他揽在怀里一般美好。然而荒谬矛盾的是,影像电话却反而拉远了人类的距离。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架设在全世界四千至五千个中心点的摄像机并不说明或评论外界发生了何事。想知道地球某个角落的天气概况,只须叫出相关的电台,坐在沙发上便能一览天下事。
令人惋惜的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逐渐减少——这正是问题的核心,离开房子意味着严重限制自身的视野。
5.
所有较古老的通讯方式,包括娱乐与各类知识传递的途径,至二十一世纪中期为止都是通过电视进行。每一种人际接触——洲到洲,世代到世代——从又称之为终端机的荧屏开始。
一切的资讯都集结在唯一的数据网络当中,每间屋内放置一个或多个荧屏已属常态。像现在一样,多半在客厅里摆个大荧屏,其他房间内则有不同的小荧屏。二○八○年,每个房间四面墙上都是荧屏的情形将早已司空见惯;但现在的人还是认为,在屋内装设太多的荧屏会剥夺居家气氛。另一方面,在厨房里切面包或者蹲厕所的时候,还是会想看点东西。最后,时间不容挥霍,天下事尽在你的视力范围内,世界就站在厨房的餐桌上。放着绝佳机会不加以利用简直是麻木不仁。
二十一世纪起,我们可以论及所谓真正的双边交流。借由网络,不仅能够从荧屏上取得各种形式的资料,亦可与任何一个人有所接触。二○五○年在家中遇见他人的概率为百分之八十五(今日为百分之九十七)。
那时人类已经永久远离街头与广场,终端机成为我们的休憩场所。想在城里散散步放松心情的人,必须像现在一样回家去买西红柿或与其他人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