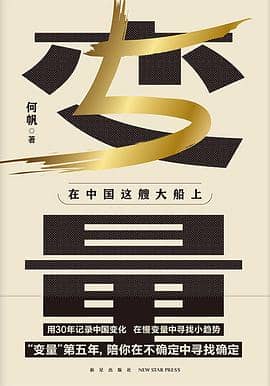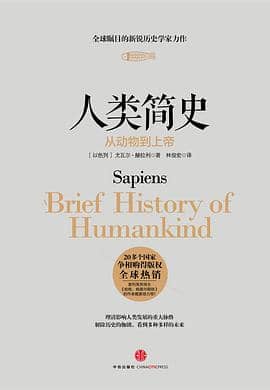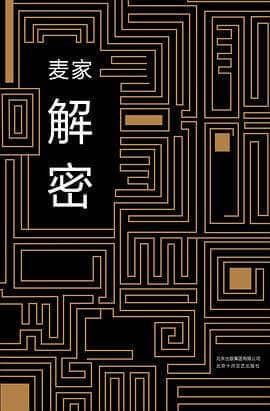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书完整收录了诺奖得主、科学顽童理查德·费曼的61篇经典自传文章,经过费曼的忘年密友拉尔夫·莱顿的精心编排,我们得以沿着生平时间重走费曼的冒险旅程:在麻省理工学院捉弄同学,在普林斯顿大学与爱因斯坦对话,研发原子弹的同时开遍保险柜,学敲鼓并加入桑巴乐队,在诺贝尔奖晚宴的趣事,学画、卖画、办画展,靠冰水和夹子解密航天飞机事故……费曼的这些文章,展现了他对科学、教育和人生的独特观念和态度,也告诉我们:做一个有趣的人比获得诺贝尔奖更难,也更重要。
作为费曼的好友,编者拉尔夫·莱顿为本书增加了新的注释,这些着意补充的细节为费曼的叙述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同时收录包括费曼的照片、绘画作品、手稿在内的的30多张图片。此外,本书还特别收录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弗里曼·戴森所作的前言,并以知名演员、导演艾伦·艾尔达在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庆典上的演讲作为后记,为这本精彩的自述辅以他人视角,更能让读者看见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费曼。
作者简介
理查德·P.费曼(Richard P.Feynman)
1918年,费曼出生于纽约的法洛克威镇并在此长大,17岁进入麻省理工学院,1939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随后他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加入原子弹研究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曼任教于康奈尔大学物理系,后于1951年 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在此执教至1988年去世。1965年,费曼与朱利安·施温格及朝永振一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拉尔夫·莱顿(Ralph Leighton)
拉尔夫在加利福尼亚的阿尔塔迪纳镇长大,与费曼的家乡相距不远。他的父亲罗伯特曾与费曼合著《费曼物理学讲义》。拉尔夫和费曼是忘年好友,两人都喜欢敲邦戈手鼓,本书讲述的故事大多是拉尔夫和费曼在敲鼓的时光中共同记录下来的。
试读:
科学家是怎样炼成的
我有一位艺术家朋友,有时候他的观点令我无法赞同。他会拿起一枝花,然后说:“看,多美啊!”我会表示同意。但接下来他会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能看到一朵花的美。但你这个科学家会把它拆分一番,事情就变得索然无味了。”我觉得他这么想有点傻。
首先,他看到的美,其他人也看得到,我相信也包括我。虽然我可能不像他那样精于审美,但我可以欣赏一朵花。不仅如此,我在一朵花上看到的东西比他多得多。我可以想象其中的细胞,细胞也具有美感。美不仅存在于厘米见方的尺度,也存在于更小的尺度。
那里有复杂的细胞活动和其他进程。花进化出颜色是为了吸引昆虫为自身授粉,这个事实很有趣:这意味着昆虫能看到颜色。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拥有的这种对美的感受是否也存在于更低等的生命形式中?科学知识可以引出各种各样有趣的问题,这只会增加一朵花带给我们的兴奋、神秘和敬畏。只会增加。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减少。
我一向单方面地专注于科学,在更年轻的时候,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科学中。在那段时间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学习所谓的人文学科。即使必须学习大学里某些人文课程才能毕业,我也尽量避而远之。直到后来我年纪渐长、更有闲余时,才扩展了一些兴趣。我学习了绘画,也读了一些书,但我仍然是一个片面的人,我并不博学。才智有限,我选择把它用在特定的方向上。
————————
在我出生前,父亲告诉母亲:“如果生个男孩,他会成为科学家。”[3]当我还是个坐在高脚儿童椅里的小孩时,父亲拿了一堆不同颜色的小块浴室瓷砖(次等品)回家。我们在一起玩,父亲把瓷砖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竖直摆在儿童椅的桌板上,然后我会推动一端让所有瓷砖都倒下。
玩了一段时间后,我也会帮忙摆瓷砖。很快,我们开始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摆瓷砖:两块白色一块蓝色,两块白色一块蓝色,如此这般。母亲看到这个情景,说道:“别难为可怜的孩子了。他想放蓝色的就让他放吧!”
但父亲说:“不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模式和模式的有趣之处。这是一种初等数学。”可以说,他很早就开始带我认识世界,告诉我世界多有趣。
我们家里有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在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父亲总是让我坐在他的腿上,给我读《大英百科全书》。比如,我们会读关于恐龙的内容。在讲到霸王龙时,书里会写“这种恐龙有25英尺高,头有6英尺宽”。
这时父亲会停下来对我说:“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吧。这就是说,如果恐龙站在我们的前院,它的身高足以让它把头伸到这里的窗户。”(当时我们在二楼。)“但是它的头太宽了,因此没法把头伸进来。”他会尽可能把读给我的所有东西“翻译”得现实一点儿。
想到世界上曾经有这等庞然大物,我非常兴奋,十分感兴趣。不仅如此,这些动物还都灭绝了,而且没人知道原因。我不害怕会有一头恐龙从窗子钻进来,但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翻译”的能力:努力搞清楚所有我读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说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过去经常去卡茨基尔山,这是纽约人夏季经常去的地方。所有的父亲都是工作日待在纽约,然后周末返回这里。周末,父亲会带我在林中漫步,然后告诉我曾经在树林中发生的趣事。别人的母亲看到我们后,觉得这样很不错,认为自家的丈夫也应该带着儿子散步。她们开始说服丈夫们这样做,但起初毫无进展。随后她们又想让我父亲带着所有孩子散步,但是他并不愿意,因为他只与我有特别的关系。结果就是,下个周末别人的父亲也要带着自己的孩子散步了。
到了下周一,父亲们都回去工作后,我们这些孩子在田地里玩耍。一个孩子问我:“看见那只鸟了吗?那是什么鸟?”
我说:“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鸟。”
他说:“那是一只褐喉画眉。你爸什么都没教你!”
但事实恰恰相反。父亲是这样教我的:“看到那只鸟了吗?”他说,“那是斯潘塞莺。”(我知道他也不知道这鸟的真名。)“意大利语里叫‘Ciutto Lapittida’,葡萄牙语里叫‘Bom da Peida’,中文里叫‘钟隆达’,日语里叫‘Katano Tekeda’。你可以用全世界所有语言说这种鸟的名字,但是完事之后,你对这种鸟依然一无所知。你只知道不同地方的人怎么称呼这种鸟。我们来看看这只鸟,看看它在做什么——这才有意义。”(我很早就明白了知道一个东西叫什么和了解这个东西之间的区别。)
他说:“比如,看那只鸟一直在啄自己的羽毛。看到了吗?它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啄自己的羽毛。”
“看到了。”
他说:“你觉得鸟为什么要啄自己的羽毛?”
我说:“它们可能在飞的时候把羽毛弄乱了,所以它们啄羽毛是为了梳理整齐。”
“好吧。”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刚刚飞过之后应该啄得更勤。那么它们在落到地上一阵子后,就不会啄得那么勤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他说:“我们来看看它们刚落地时会不会啄得更勤。”
不难发现,已经在地上走了一阵的鸟和那些刚刚落地的鸟没有太大区别。于是我说道:“我放弃了。鸟为什么要啄自己的羽毛?”
“因为虱子正骚扰着它们,”父亲说,“虱子会吃从鸟的羽毛上掉落的小片蛋白质。”
他继续说:“每只虱子的腿上都有一些蜡状物,小螨虫会吃这些蜡。螨虫无法完全消化这些食物,因此它们会从尾部分泌一种糖类物质,而细菌就以此为生。”
最终他说:“所以你看,哪里有食物源,哪里就会有发现它的某种生命。”
现在,我知道实际上可能不一定有虱子,虱子的腿上也不一定就长有螨虫。这个故事在细节上未必正确,但父亲告诉我的事情在原则上是对的。
还有一次,当我大一点的时候,父亲从树上摘下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有个缺口,我们通常不会关注这种东西。叶子受到了某种损坏,它上面有一条棕色的C形细线,从中间某处开始一直弯曲着延伸到边缘。
“看看这条棕色的线,”他说,“它在起始处很窄,延伸到边缘时逐渐变宽。这些都是因为一只苍蝇,一只黄眼睛绿翅膀的蓝色苍蝇来到这里,并在叶子上排了一个卵。然后当卵孵出了蛆(一种像毛毛虫一样的生物),蛆就一直吃这片树叶,它就是这么获取食物的。它一路吃下去,就在叶子上留下了这条棕色痕迹。蛆不断生长,痕迹也越来越宽,直到蛆在叶子边缘长得够大了,它就会变成苍蝇(一只黄眼睛绿翅膀的蓝色苍蝇),飞走后在另一片叶子上产卵。”
我依然知道这些细节并不完全准确,叶子上的虫子甚至可能是一只甲虫,但是父亲努力向我解释的概念正是生命的有趣之处:整件事情的意义就是繁殖。无论生命这件事有多复杂,它的重点就是“再来一遍”!
如果不是和父亲多多相处,我就意识不到他有多么非凡。他如何学到科学的深层原理并感受到对科学的热爱?他如何知道科学背后的东西并相信科学值得我们为之努力?我从来没有真正问过他,因为我一直以为这就是父亲们都知道的事。
父亲教我学会观察。有一天,我在玩一辆“快递货车”,这是一辆带环绕轨道的小货车。车里有一个球,当我拉动货车的时候,我注意到球的移动方式。我找到父亲,问他:“嘿,爸爸,我注意到一些东西。当我拉货车的时候,球会滚到货车的后部。当我一直拉着车然后忽然停止时,球又会滚到车的前部。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嘛,没人知道。”他说,“总的原则是,移动的东西趋向于一直移动下去,而静止的东西趋向于一直静止,除非你使劲推动它们。这种趋向叫‘惯性’,但没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次他给了我一个深刻的见解。他没有仅仅告诉我名字。
他接着说:“如果你从侧面看,你会发现是你拉动的货车后部与球摩擦,而球则静止不动。事实上,球由于摩擦力相对地面向前移动了一点儿。它并没有向后移动。”
我回到小货车那里,重新把球放好,开始拉车。从侧面观察,我发现父亲说的确实没错。相对于路面,球果然向前移动了一点儿。
父亲就这样用举例和讨论的方式教育我,没有压力,只有令人愉快的有趣对话。这在我余生中一直激励着我,让我对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充满兴趣。(只是我刚好更擅长物理而已。)
可以说,我被深深吸引住了,就像有人在孩童时期得到一件很棒的东西,他就会永远想着如何再得到它。我总是像孩子一样,寻找那些待我发现的奇妙事物,可能不是每次都有,但隔段时间就有所发现。
————————
大我三岁的表哥那时正读高中。他学习代数非常吃力,因此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当家庭教师给我表哥讲代数的时候,我可以坐在角落。我听他说起x。
我对我的表哥说:“你要做什么?”
“我想解出x是多少,比如在2x+7=15里。”
我说:“你是说4。”
“是的,但你是用算术方法解的。必须用代数方法来解。”
幸运的是,我不是在学校里而是通过阁楼里找到的姨妈的旧课本学会的代数,我明白了代数的整体思想就是解出x是多少,怎样求解并没什么分别。对我来说,无所谓“用算术解”还是“用代数解”。“用代数解”就是一套规则,如果你盲目遵从这些规则,就能得出答案——“等号两边同时减7;如果x有系数,两边就同时除以系数”,以此类推。即使你不理解自己在做什么,也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步骤得到答案。之所以有这些规则,是为了让不得不学习代数的孩子可以通过考试。这也是我的表哥一直都不会解代数题的原因。
在我们本地的图书馆里有一系列数学书,包括《给实用主义者的算术》,还有《给实用主义者的代数》以及《给实用主义者的三角学》(我就是从这本书上学到了三角学,但是我很快就忘光了,因为当时我没有很好地理解)。在我13岁时,图书馆收入了《给实用主义者的微积分》。那时我已经通过百科全书知道微积分的重要和有趣,我必须学习微积分。
当我终于在图书馆里看到那本微积分书时,我非常兴奋。我到图书管理员那儿办理借阅手续,但是她看着我说:“你只是个孩子。你带走这本书做什么呢?”
这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感觉尴尬和撒谎之一。我说书是给父亲的。
我把书拿回家,然后开始看书学习微积分。我认为微积分比较简单直接。父亲也开始读这本书,但是书中内容让他感到很困惑,他无法理解。因此我就试着给他解释微积分。我从没有意识到他的能力如此有限,而这让我有点困扰。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某些方面我学到的东西比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