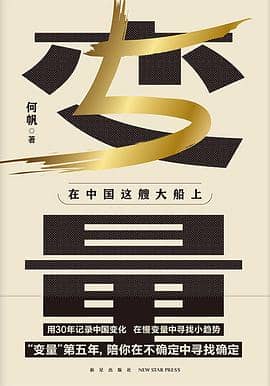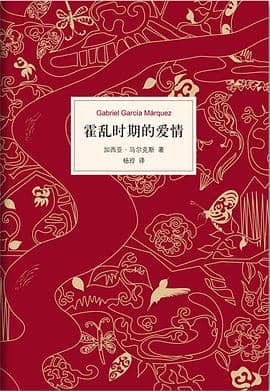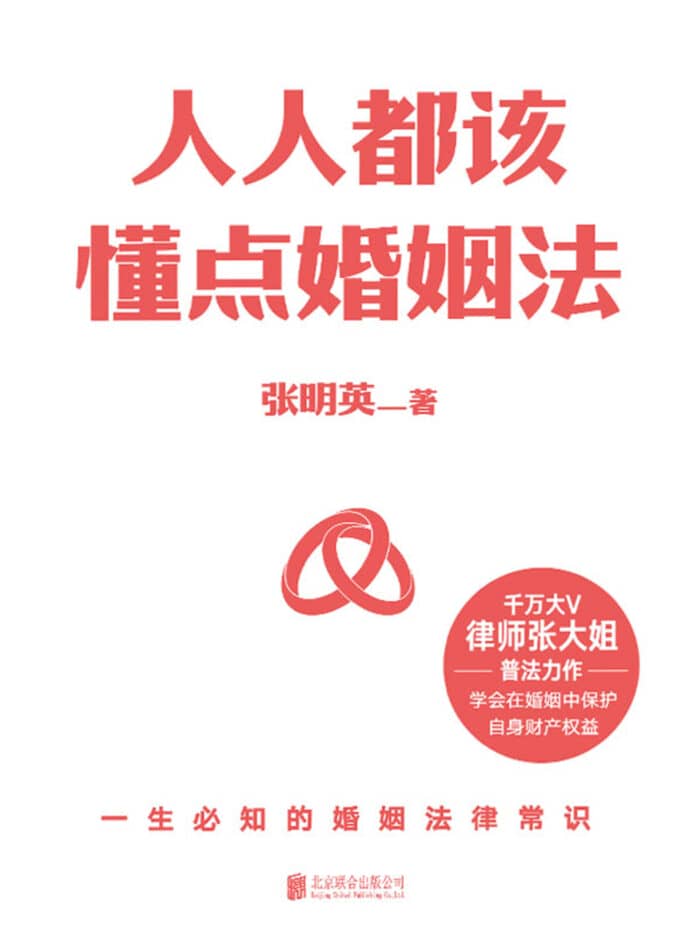作者:
村上春树
1949年生于日本京都。凭处女作《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由此出道。后续著作不断,涵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纪实文学、随笔等多个类型。其中有闻名世界的《挪威的森林》、深度纪实的《地下》、被誉为“新千年日本文学的里程碑”的《1Q84》、谈及战争反思的《刺杀骑士团长》《弃猫》等。
曾获得谷崎润一郎奖、每日出版文化奖、卡夫卡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等世界范围内的诸多奖项。其短篇小说构思精巧,余韵悠长,给读者留下丰富的解读空间。
烨伊
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日语系。曾留学日本,并在当地孔子学院教授中文课程。凭着一点点执念走了一段不太短的路,没承想执念竟慢慢成了信念。
译著有《弃猫 当我谈起父亲时》《人间失格》《潮骚》《起风了》等。
简介:
睽违六年!村上春树2021全新短篇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11.18全网现货发售!
当世界不断变迁,唯有故事留住刹那光景。
8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重现村上式奇幻青春物语。
再不相见的男女···名为村上春树的角色···偷人姓名的品川猴···夏日气息与摇滚乐……
★村上回归第一人称叙述,代入感强。尽显故事的魔力!
村上作品中《挪威的森林》《且听风吟》《寻羊冒险记》都以第一人称写成,作家更善用“第一人称”叙事写作。8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重现村上式奇幻青春物语。村上回归初心之作!作家本人直言“再一次站在最初的位置上,迎接全新挑战”——村上春树
★暌违六年!村上春树2021全新短篇小说集,村上春树回归之作!
继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6年之后!继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3年之后村上春树正式小说作品。一经上市引发读者热评:“在疫情时代,还得是村上的书。读村上的小说能让人获得治愈。”马家辉微博点评:这书是短篇小说集,干净利落的故事,似回到了《挪威的森林》的笔调风格。
短篇小说,是一个世界的无数切口。
“第一人称单数”是截取世界某个片段的“单眼”。这样的截面越来越多,“单眼”就成了无穷交错的“复眼”。到那时,我便不再是我,你也不再是你。到那时,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欢迎来到“第一人称单数”的世界。
八篇小说中《石枕上》忆起大学时与打工相遇的文学少女偶然间的情感交流。
《奶油》写出无法在生活中获得解释、不合逻辑却又扰乱心灵,脱离现实的质疑,耐人寻味。热爱爵士乐的村上也写下这篇似真似幻的音乐小说《查理·帕克演奏波萨诺瓦》,故事中音乐报导的写手虚构了一张梦幻专辑,却因此衍生出如梦境与真实世界的奇异接轨。《和披头士一起(With the Beatles)》和披头士的专辑同名,是充满往日夏日气息与摇滚乐的初恋青春纪事……
值得注目的还有《养乐多燕子队诗集》,除了洋溢着对棒球的热爱,更结合了诗作、散文体裁,也是继《弃猫》后再次难得揭露少时与双亲的生活回忆。令人印象深刻的《狂欢节Carnaval》谈论丑陋,也等于谈论美丽,更兼论善恶,引人反复思索在生活这个面具底下的素颜,究竟是恶灵或是天使?《东京奇谭集》中非常受到读者喜爱的《品川猴》,此猴再次登场于续篇《品川猴的告白》,揭露品川猴启人疑窦的身世之谜与极致的恋情,极致的孤独。同名篇章《第一人称单数》,在春夜满月里的酒吧中发生了一段质疑自我的邂逅,故事结束了却余韵未了,彷佛跌入晦暗的酒吧空间,以小说开启一个不眠的微醺之夜。
八个题材视角各异的精彩短篇,可以说是迈入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村上春树,回望人生爱与死主题的珠玉之作连发。结合了短歌、散文、音乐与小说,展开村上风格的全新复眼小说。阅读村上小说,徜徉文学世界,活着不就是一首对于青春、爱与死亡的追想曲!
试读:
在石枕上
我要写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不过,我对她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就连她的名字和长相也想不起来。而且她恐怕也一样,不记得我的名字,也不记得我的长相。
和她见面的时候,我读大学二年级,还不到二十岁,她大概二十五岁。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之后偶然共度过一个夜晚,再后来就一次面也没见过了。
十九岁的我,对于自己的心思几乎全无了解,当然,对别人的心思也浑然不知。话虽如此,我自认还是懂得何为喜悦何为悲伤的,不过是对喜悦和悲伤之间的诸多状况,和它们彼此的关系之类还看得不够透彻罢了。而那件事却屡屡令我坐立难安,颇感无力。
不过,我还是想讲一讲那件关于她的事。
关于她我知道的是——她创作短歌(1),还出版了一本歌集。说是歌集,其实不过是用类似风筝线的东西把纸张订在一起,再粘上简单的封面,做成一本极为朴素的小册子,连自费出版都很难算得上。但收在集子里的几首短歌,不可思议地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创作的大部分短歌都与男女之爱,以及人的死亡有关。仿佛想要昭告天下,爱与死是一对毅然拒绝分离、分割的事物。
你/和我/离得远吗?
在木星换乘/能否抵达?
耳朵贴上/石枕/听到的是
血液流过的/寂静、无声
“那个,高潮的时候,我说不定会喊其他男人的名字,你介意吗?”她问。我们赤裸着身体躺在被子里。
“倒是不介意。”我回答。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这点小事应该不成问题。反正不过是个人名。没有什么会因为一个人名而改变。
“可能会喊得很大声。”
“那可能有点麻烦。”我慌忙说。我住的那间老旧木制公寓的墙壁,就像过去常吃的威化饼干一样,又薄又脆。再加上夜色已深,若是真闹出那么大的响动,只怕会让隔壁听个一清二楚。
“那,我到时候就咬一条毛巾。”她说。
我从厕所挑了一条尽可能干净而结实的毛巾,放在枕头旁边。
“用这条可以吗?”
她像试新辔头的马一样咬了那条毛巾好几次,然后点点头,意思是这样可以。
那顶多是一次顺水推舟的结合,我并没有特别渴望她,她(应该)也没有特别渴望我。我和她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工作了半个来月,但工作内容不同,所以几乎没有正经的机会交谈。那个冬天,在四谷站附近的一家平价意大利餐厅,我做着洗碗、帮厨一类的工作,她是大堂的服务员。除了她,在这家餐厅打工的都是学生。这也许就是她的举止让我感受到一丝超然的原因。
她决定十二月中旬辞职。之后有一天,餐厅打了烊,她和几个人到附近的小酒馆喝酒,我也被邀请同去。那不是一场送别会规模的酒局,不过是一起在酒馆待了一个来小时,喝了些生啤,吃了点儿简单的下酒菜,天南海北地闲聊了一阵子。那时我才知道,她到这家餐厅工作前,曾在一家小的房地产公司工作,还做过书店店员。她说自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和上司或管理层处不好关系。“现在这家餐厅,我虽然和谁都没有矛盾,可薪水给得太少,很难长期这样生活下去。所以尽管打不起精神,还是得找个新的工作。”她说。
“那你想做什么工作呢?”有人问。
“什么都行吧。”她的手指摩挲着鼻子侧面(她的鼻翼上有两颗小痣,像星座一样排列着),“反正也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工作。”
那时候我住在阿佐谷,她住在小金井,所以我们从四谷站一起坐中央线快速列车回家。我们俩并排坐着,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那是一个吹着刺骨寒风的夜晚,不知不觉间,需要手套和围巾的季节已经悄然到来。列车接近阿佐谷,我起身要下车的时候,她仰起脸来望着我,小声说:“那个,方便的话,今天能不能住你那里?”
“能。为什么?”
“因为离小金井还很远。”她说。
“我的屋子很小,而且挺乱的。”我说。
“这些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说,然后挽住了我大衣的袖子。
她来到我那间小而穷酸的公寓,我们在屋子里喝了罐装啤酒。等酒慢慢喝完,她利利索索地在我面前脱下衣服,转瞬间赤裸了身子,钻进被窝,仿佛一切是那么理所应当。我随后同样脱掉衣服,钻进被窝。灯虽然关了,但煤油炉的火光照亮了屋子。我们在被子里笨拙地温暖着彼此的身体。有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这突如其来的赤裸一时令我们无言以对。不过,我们真真切切地亲身感受到彼此的身体逐渐暖和、不再僵硬。那种亲密感难以言喻。
“那个,高潮的时候,我说不定会喊其他男人的名字,你介意吗?”她就是在这时向我发问的。
“你喜欢那个人吗?”准备好毛巾后,我这样问她。
“嗯,很喜欢。”她说,“特别特别喜欢。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他。但他没这么喜欢我。而且,他还有个正儿八经的恋人。”
“但是你们在交往?”
“对。他啊,想要我身体的时候,就会找我。”她说,“就像打电话点外卖一样。”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于是不再说话。她的指尖在我背上描摹着,好像在画某个图案,或者潦草地写了些什么。
“他说:‘你的脸没什么意思,但身子超棒。’”
我不觉得她的长相无趣,但要用“美女”形容则的确有些勉强。至于她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如今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所以无法细致地描述。
“但他叫你,你就会去?”
“我喜欢他嘛,有什么办法。”她轻描淡写道,“无论别人怎么说我,我偶尔还是想被男人抱一抱的。”
我试着思考她的话。不过,那时的我还不是很明白,对女人来说,“偶尔想被男人抱一抱”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如此说来,我好像到现在都不太理解)。
“喜欢一个人啊,就好比得了什么不在医保范围内的精神疾病。”她的语气平淡,像在读墙上写的文字。
“原来如此。”我佩服地说。
“所以呢,你也可以把我当作别人。”她说,“你有喜欢的人吧?”
“有啊。”
“这样的话,你在高潮的时候也可以喊那个人的名字。我也不会介意的。”
可我没有喊那个女人——当时我喜欢一个女人,但出于一些原因无法与之加深关系——的名字。也犹豫过是否要喊,但做着做着觉得喊出来傻乎乎的,于是一言不发地在她体内射了精。她确实想要大声呼喊一个男人的名字,我不得不匆忙将毛巾用力塞进她口中。她的牙齿十分坚固,牙科医生见了一定会感动不已。那时她口中喊的是什么名字,我也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不是一个亮眼的名字,反而随处可见。印象中我曾暗暗感叹:这样一个无趣的名字,对她来说竟也意义非凡。原来在某些时刻,一个名字的确能激烈地摇撼人心。
第二天早上我有课,必须在课上提交一份重要的报告,相当于期中考试,但自然被我弃之不顾(后来我因此没少遇到麻烦,不过这是另外的事了)。我们睡到上午才醒,烧水喝了速溶咖啡,又烤了吐司来吃。冰箱里还有几个鸡蛋,也煮着吃了。晴朗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午间的阳光十分炫目,让人懒洋洋的。
她嘴里嚼着涂了黄油的吐司,问我在大学读什么专业。我说在文学系。
“你想当小说家吗?”她问。
其实没有这个打算,我诚实地回答。当时的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小说家,这样的想法压根儿就没出现过(尽管班里公开立志成为小说家的家伙数不胜数)。她听到这样的回答,似乎对我失去了兴趣;虽说可能本就对我没有多少兴趣,但情绪变化着实明显。
在白天明亮的光线下,看到清清楚楚留有她牙印的毛巾,不免令我惊讶。想必是下了相当大的力气来咬的。在午间的日光下见到的她,也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实在难以想象,眼前这个面色苍白、娇小而骨感的女人,竟然和窗外照进的冬夜月光下,那个在我怀中叫得魅惑而欢愉的女人是同一个人。
“我在写短歌呢。”她几乎是唐突地说。
“短歌?”
“你知道短歌吧?”
“当然。”就算知识再匮乏,我至少也知道短歌是什么,“不过,这好像是我第一次遇到真正写短歌的人。”
她开心地笑了。“不过啊,世上这一类人可有的是呢。”
“有参加什么同好会吗?”
“没,不是你想的那样。”她说着,微微耸了耸肩,“短歌一个人就能写得来呀。对吧?又不是打篮球。”
“什么样的短歌?”
“你想听?”
我点头。
“真的?不是随口附和我?”
“真的。”我说。
此话不假。我是真心想知道,几小时前还在我怀里喘息着大喊其他男人名字的女人,究竟会咏出怎样的短歌。
她犹豫片刻,说道:“现在当场出声读给你听,还是太难为情了,我做不来,更何况是大早上的。不过,我出了一本类似歌集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想读,我回头送给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和这里的地址吗?”
我用便笺写下名字和地址递给她。她看了看,将便笺对折了两次,放进大衣口袋。那是一件浅绿色的大衣,穿得很旧,圆领的位置别着一枚铃兰花形状的银色胸针。我记得它在朝南的窗子射进来的阳光中闪闪发亮。我对花草并不熟悉,唯有铃兰花,不知为何是从前就喜欢的。
“谢谢你让我在这里过夜,昨天实在不想一个人坐到小金井去。”她离开房间前说,“有时候啊,女人是会这样的。”
那时我们十分清楚,彼此今后应该不会再见了。那天晚上,她只是不想独自坐着列车回小金井去——仅此而已。
一星期后,她的“歌集”寄到了。说实话,我几乎没指望过它真能寄到我手上。我坚定地以为,她与我分别,回到小金井的住处时,就已经将我忘得一干二净(或者巴不得尽快忘得一干二净)。至少将歌集装进信封,写上我的名字和地址,再贴好邮票,特意扔进邮筒——说不定还要去一趟邮局——这么麻烦的事,她是绝对不会做的。因此,某个早上,当我看到公寓的邮箱里塞着的那只信封时,着实惊讶了一番。
歌集的名字叫《在石枕上》,作者的名字只写了个“千穗”。无从确认那到底是她的本名还是笔名。打工的时候,她的名字我肯定听到过好几次,此时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唯一确定的是,当时没人叫她“千穗”。办公用的茶色信封上没有写寄件人的地址和姓名,也没有夹带信或卡片,只有一本用类似白色风筝线的东西装订的薄薄的歌集,沉默地躺在其中。好歹是以铅字工整印出来的,而不是那种用手工刻蜡纸印的东西,纸也厚重,很上档次。恐怕是作者将印好的纸张按顺序排好,再贴上厚厚的封面,用线一本一本耐心装订成书的吧——为了节省装订成本。我试图想象她一个人默默做这种手工活的情景(但无法想得具体)。第一页上用号码机印着数字28。大概是限量的第二十八本吧,一共做了多少本呢?册子上找不到定价,可能本来就没有定价。
我没有立刻翻开这本歌集,而是将它在桌上放了一会儿,不时瞥一瞥封面。不是没兴趣,而是觉得读某个人创作的歌集之前——更何况是一个星期前曾与我肌肤相亲的人——必须做好相当的心理准备。可能算是某种礼节吧。将歌集拿到手中翻开,是那个周末的傍晚。我靠在窗边的墙上,在冬日的暮色中阅读。整本歌集收录了四十二首短歌,一页一首,数量绝不算多。前言、后记之类的东西全都没有,也没标出版日期,只是在白纸上直截了当地用黑色铅字印好一首首短歌,并留下大片的余白。
我当然不曾期待从中发现优秀的文艺作品。前面也说过,我仅仅出于一丁点个人的兴趣,好奇那个曾一面咬着毛巾,一面在我耳边喊出某个陌生男人名字的女人,到底会写出怎样的短歌。不过翻看歌集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被其中的几首短歌吸引了。
我当时对短歌几乎一无所知(现在也差不多同样无所知)。因此无法客观地判断这些短歌作品哪些优秀,哪些不够优秀。但抛开优秀与否的标准,她创作的短歌中的几首——具体来说,大约是其中的八首——具备直抵我内心深处的某些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