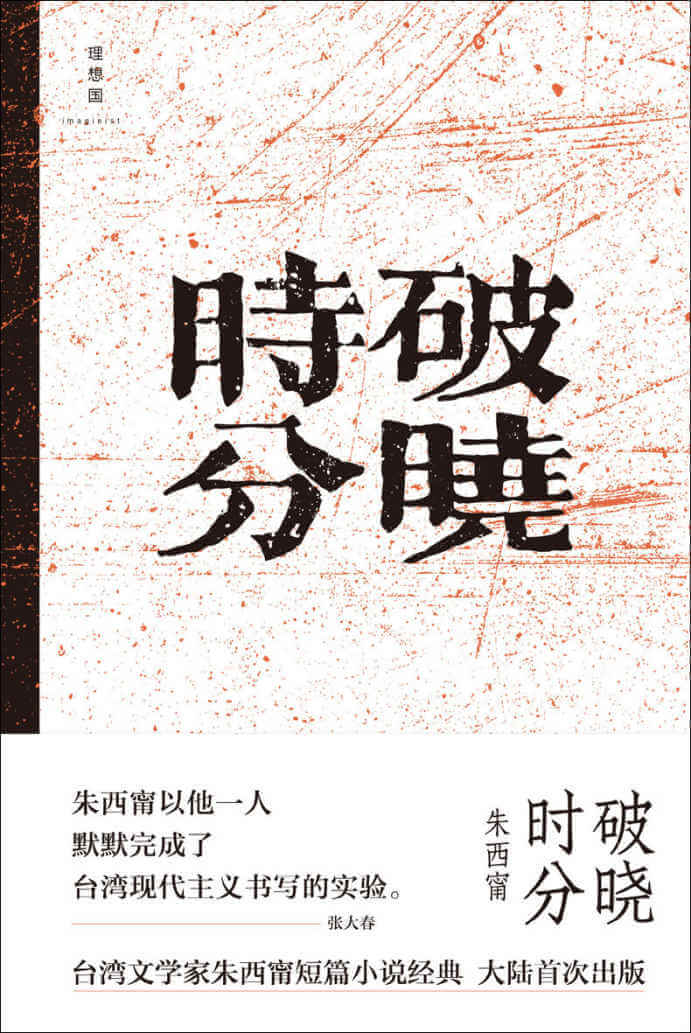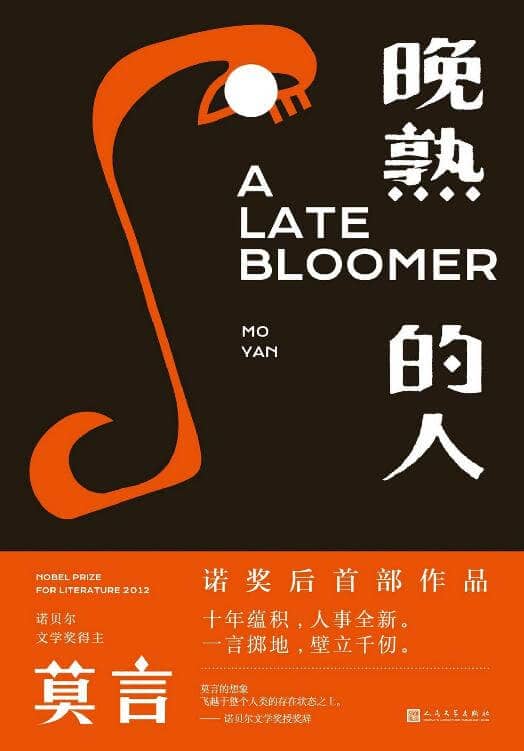作者:
朱西甯(1926—1998),台湾小说家,作家朱天文、朱天心之父。
生于江苏宿迁,祖籍山东临朐。本名朱青海,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肄业。一九四九年随军赴台,曾任《新文艺》月刊主编、黎明文化公司总编辑、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一生专注写作,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及散文、评论。著有短篇小说集《狼》《铁浆》《破晓时分》《冶金者》《现在几点钟》《蛇》等;长篇小说《猫》《旱魃》《画梦记》《八二三注》《猎狐记》《华太平家传》;散文集《微言篇》《曲理篇》《日月长新花长生》等。
◎ 理想国·朱西甯作品
铁浆
旱魃
破晓时分
狼
华太平家传(即将推出)
内容简介:
◎ 作品看点
★ 台湾文学家朱西甯短篇小说经典大陆首次出版,彰显人之存在,人之欲念,人之性灵。——从《铁浆》中的北地乡野传奇延展至台湾市镇风情,古希腊式悲剧演变为普通人琐细日常与内心战场,呈现更为现代的深邃风景。破晓时分,天地不仁,欲与悔、罪与孽,纠结消长,彰显人之存在 、人之欲念、人之性灵。“人如何靠着某些古老的信仰,不致使那世界整个虚无垮掉? ”
★ 张大春、唐诺、王德威、虹影 致敬:“朱西甯以他一人默默完成了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实验。” ——朱西甯被称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冶金者”“台湾第一位新小说家”。作为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开拓者,他在《破晓时分》中首次展露多向度的现代书写探索,穷究语言而乐之不疲的兴味,以及高度成熟的现代意识。
★ “堕落的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如何开始的?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所能承受的最沉重的主题。”同名短篇《破晓时分》改写自宋代话本小说《错斩崔宁》,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破晓时分,天地幽冥,一场误判生死的官非重演了最原始的代罪仪式。朱西甯以现代手法重写经典悲剧,直指人与荒谬命运之间的纠葛,震慑人心。
*
◎ 内容简介
听这索链,多少罪!多少孽!和多少冤苦,在一片黑森里摸索而来,在冰霜上滑来。
《破晓时分》是台湾文学家朱西甯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收录十三部短篇经典,首次在大陆出版。人物从《铁浆》中的血气英雄扩展至普通市民,北地乡野传奇与台湾市镇风情相映照,古希腊式悲剧演变为普通人琐细日常与内心战场,呈现更为现代的深邃风景。《春去也》写春日里剿丝师傅的绵绵情思,《白坟》缅怀英雄的陨落,《偷谷贼》悼念正直的衰亡,《也是滋味》写已婚男子的意识流遐想。《福成白铁号》分别以一家四口人的视角,述说牢笼般滞闷的都市日常与生之疲倦。同名短篇《破晓时分》改写自宋代话本小说《错斩崔宁》,直指人与荒谬命运之间的纠葛,一幕震慑人心的悲剧,追问“堕落的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如何开始的?”
破晓时分,天地不仁,欲与悔、罪与孽,纠结消长,彰显人之存在、人之欲念、人之性灵。在《破晓时分》中,健朗悲壮的北地文风仍存,同时进行丰富面向的现代主义叙事探索,开启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实验。
*
◎ 名人推荐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来到新世纪,才回过头来讨论朱西甯在四五十年前的作品,使我不免有迟到的歉然之感。朱西甯以他一人默默完成了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实验。和任何一位当代台湾小说家相较,朱西甯都有一个独特的标记——他穷究语言而乐之不疲的兴味。
——张大春
朱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写出来这样优秀的作品,可惜我读得太晚。若能早些读到他这几本书,我的《檀香刑》将更加丰富,甚至会是另外一番气象……
——莫言
纯粹从文学的角度讲,我依然认为朱西甯是1949年至今台湾最优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多了几层徘徊,不会把恶与善分得那么清楚。他对世界充满了同情,总是会对一般所谓的“恶”多看两眼,给它们一点点的机会。
——唐诺
《破晓时分》之所以让我们震撼,更在于朱西甯对人之所以为人,对人与荒凉也荒谬的命运间的纠结,所作的无情剖析。破晓时分,天地幽冥,一场误判生死的官非重演了最原始的代罪仪式。这个故事最终要追问的,是人在时间的一个模糊焦点上,对生命的有限领悟,以及随之而来的无限惶惑。朱西甯已经显出他是个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作家。文字才是他最后的原乡。
——王德威
这就是他,写过吞吃铁浆而争霸道的民族灵性,写过为生存而助恶的民族弱质,写过横扫中原的战乱腥风。我总认为他是个刚烈汉子,至少是见过太多流血和残酷的硬心人。可是,此刻坐在我身旁,却是睿智、自然,而令我倾服的是他的安宁慈祥: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世上尚存极少数极少数的大慈悲者,是我多少年来都在苦苦寻找的那种人。
——虹影
朱先生的短篇不论题材如何,其实都可以看到相当自觉而精巧的形式实验,不论是限制观点的运用、意识流、时间配置还是语言腔调上的自觉转换,成绩当相当可观。包括了《铁浆》《狼》《破晓时分》中的大部分作品,而不仅是《冶金者》。
——黄锦树
堕落的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如何开始的?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所能承受的最沉重的主题。
——英国汉学家白芝
对我而言最重要、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就是朱西甯先生的作品。我可以确定地说朱西甯是我认识的六〇年代里最好的纯文学作家。
——舞鹤
编辑推荐:
受广大上班族喜爱的沈大成继《小行星掉在下午》后作品集。以奇崛的构思、秀异的想象讲述十五个失去导航的“宇宙人”故事。
本书是作家沈大成新作品集。过去几年来她的作品持续引发广大上班族“打工人”的共鸣,发现这些看似荒诞的奇人奇事均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收录于前作《小行星掉在下午》中的故事《盒人小姐》甚至意外地“预言”了一个社交隔离、打疫苗成为常态的世界。
新作《迷路员》聚焦十五个失去导航的“宇宙人”故事,再次呈现我们时代的异样日常:在星空剧场打瞌睡醒来却洞悉了宇宙奥义的人,早已废弃却始终与居民共生的小镇百货公司,世界上后一个移动部落缩小巨人,在办公楼花园中躲藏数年的离职员工,不满足被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人行天桥,负责看管星球大战战备物资的仓库值班员……这些非科幻非外星非奇幻非魔幻的故事,关注的均是宇宙中的各种存在。
“我们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当然也有点知道在干什么,说我们不占有任何身份也不对,我们起码是迷路员。迷路员就像一个工种,得认认真真地干好它。”小职员作家沈大成有条不紊地想、仔仔细细地编织,又一次完成了非比寻常的想象之旅。
两次入围青年文学奖短名单。作家苏童、唐诺推荐,“我是沈大成的读者”。
沈大成以出版的两部小说集《屡次想起的人》《小行星掉在下午》两次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短名单,获得两届多位评委专家的肯定。她的作品在同代作家中风格鲜明、独树一帜,以专属的奇思妙想描写当代的生活现状和心理困境,关怀这个我们真正拥有的世界里那些“人”、那些物。
作家苏童认为《迷路员》“想象力放松、开阔,摸不到边”。作家、评论家唐诺为《迷路员》手写数百字推荐语:“……沈大成的想象文字不惊不乍,总是如博尔赫斯所说用平静的话语讲一个一个神奇的故事。神奇发生了,但人是真的、实的。仍保有几乎全部人的生命基本细节。因此,她的文字时时处处自成隐喻,给我们一种屡屡回首的感觉。这个真实世界也许并不值得人如此眷顾,但终究,这是我们真正有的。”“我是沈大成的读者。”
试读:
春去也
收蚕茧的节令又到了,那总是满地桃花落红烂醉的时候。
缫丝房这一忙就要忙上一个月的光景。年年总是这样的,甚么活儿都得先放下,总共两个师傅、一个学徒,就是三头六臂也不够用。邱师傅照例得捎信下乡去把老丈母娘请来家,顺便带个派上用场的人手,哪怕只能给丝锅添添煤,或是蚕茧堆上不时洒洒盐水甚么的。
院子实在不多大,半铜盆的洗脸水就够从西屋泼到东墙。院子里一担一担等着上秤的蚕茧,挤得没有下脚的空儿。那么多的嘴巴讨价钱,争斤两。天上掠过布谷鸟那样急切匆忙的叫声,桃花瓣儿给吵闹得纷纷打旋想再飞回树梢儿。
邱师傅的丈母娘带着小姨子搭人家的骡车来了。一进门,包头来不及解下,就喳喳呼呼地招呼这,招呼那,不知多少机要等她老人家来裁定。小姨子扶着她,搀瞎子一样地在那些箩子筐子的隙缝里找路走。
“今年哪,收成真没说处!”丈母娘抄起一捧雪团儿般的蚕茧说,“又胖又白漂,鹁鸽蛋儿也没这么匀净!”
白花花的肥蚕茧就如白花花的银链子,逗人打心底儿往外乐。老岳母忙不迭这就坐到丝锅灶门口,把正在添煤上火的小外孙女儿搂到怀里,心肝宝贝地叫着。
“乖呀,引弟儿中用了嘛!七岁的丫头!”一连就在孩子腮帮儿上嘬了几个嘴儿。“快去找找斗子里,看姥姥给你带甚么吃的来了!”
“我说他姑爷,这样子好的茧子!今年价钱怕要上了点儿呗?”
灶底下用不着再上煤,丈母娘关上铁灶门,跟丝锅上的大女婿搭谈起来。
“您老去歇歇腿儿罢,擦把脸。引弟儿,给姥姥舀盆洗脸水去!”
邱师傅肚子抵着灶台,手脚都闲不出空儿;一手使着两只炸油条一样的长筷子,一手调理丝锅里捞起的丝胚子头儿,脚底下还须一刻不停踩动丝的飞轮踏板儿。
“还是老价钱。光是咱们一家想提价,那不惹同行的骂!”
邱师傅瞥上一眼站在一旁的小姨子——丈母娘带来的人手。有两年没见,好像吹气似的陡然间大起来,出脱得一个大姑娘了。
“小姨也去擦一把脸罢,一路上风沙醭土的……”
大姑娘脸一红,赶忙望着别处,身子扭了扭。
这个做姐夫的邱师傅不知甚么缘故,一时有些儿心慌。转过脸来,丝锅上四条丝头儿只剩一条了,忙着挑来挑去地找头儿接上去。
他不认这个账的:三十出头的人了,甚么事还值得心慌?活见鬼!便加紧踩蹬脚底下踏板儿,想把那点儿恼人的心慌给蹭开。
打算捎信下乡的时候,他女人很想叫他小姨子一起上城来。他女人打定主意要给窦师傅做个媒,让两下里先都相相,看中意不中意。
“你挑甚么时候不好,专挑这个时候?房子就够匾窄的,加上收茧子,三间西屋都腾出来堆货,你让引弟儿她小姨来了,给抹上浆子贴到墙上?”
“来谁也得安个铺儿罢!横直要请娘带个帮手来,倒不如请她小姨来了,这张大炕上咱们娘儿四个还怕挤不下呀?”
邱师傅一时想不出甚么作借口。
“嘎咕卡咕——”布谷鸟没日没夜地啼叫。远处近处,飞过小城的天边。黑苍苍春夜里,黑苍苍到处布种“布谷播种——布谷播种——”然而邱师傅的种子瞎了。拉骆驼的相他有五子登科的命,他可一子儿也不子儿。引弟儿,引弟儿,弟弟没引来,连妹妹也没引得到。
老婆似睡未睡的,又被他摸弄醒了。
“当真要她小姨来呀?”一手指的滑腻腻生发油。夜半凉月爬上来,窗口染上青艳艳的雪光。
他女人含含糊糊应了他,应了些甚么也没有听清。
“不大便利,姑娘家!”
“又不用你驮着抱着,有甚么不便利!”
“抱着?我这做姐夫的……”
他老婆冷笑笑。“那有甚么,小时候你还不是抱过她看庙会?”
“小时候是小时候,那还说甚么!”
“想抱还不容易!压两天就送上门来了。”
邱师傅就觉得落了个没滋味。他拦着不让小姨子来,心里只有一个疙瘩,反说不出口,也万万说不出口;他可不情愿把小姨子提给窦师傅。连他自己也茫茫糊糊弄不清是个甚么道理。他对窦师傅可没有一点儿歹意,他们这个手艺少谁都行,单单就是少不掉姓窦的这样又能干又勤快的师傅。可怎么行呢?他着恼地跟自个儿嘀咕:怎该她要便宜了窦师傅,要做窦家的人!
能防一手的,都挺无耻地防着了。可小姨子是来定了,打着今年桑肥茧子丰收这个名目,借用对门李家客栈院子一角搭个篷,支了座丝锅给窦师傅在那边缫丝,两下里能少见就少见。也算自个儿费尽心机了。
小姨子跟在她娘后头走进房里去。乌油油的大辫子那么长,细腰大身子,肉墩墩儿一步一耸动。他两口子枕一个枕头打商量的那会子——那个春夜里,布谷鸟好像懂得甚么似的,加紧叫着,他可还没有把小姨子想作这个俏模样。要不的话,他还得多想那么几个借口,拦住不让他小姨子来。反正窦师傅说定这一季帮过了忙就回去自己开缫丝房了。那就等明年再接小姨子来也不迟。
要说让这两人相相,没有谁看不中谁的道理。一个是生得水葱儿似的,要多标致,有多标致;跟她姐姐好似不是一母所生。那另一个,白白净净的少年郎,生就笑脸庞儿,一手的好手艺,就快自己开缫丝房了。想到这儿,邱师傅就会有被冷落的感慨——那把我放到甚么地方了?这样非分的馊念头,会使他惶愧得连忙想瞒着,连自己也不让知道。
也只那一瞥呢,一眨眼仿佛又记不清那副小模样有多俏了。邱师傅勾过头去,从烟筒的一侧盯了一眼挺直站在房里的他一个人的小姨子。瞧那侧脸儿,小嘴唇不知有多可怜见的。那乌油油辫子直垂下来,衬出一掐掐儿细腰,凹进去有一拳深呢。邱师傅的小拇指给锅边儿烫了一下,长筷子掉进了翻滚的丝锅里。
看着长大的,真是了不得,这岁月,好似这丝锅的飞轮呜啦呜啦老转着不停,谁也不等的,谁也留不住那么地抽走多少蚕吐的血丝。人也把这血丝织成锦缎,编成绦子,人也用这丝绣龙又绣凤。多美多好也终不是蚕的了。
三十二寸大丝锅里,大半锅滚腾腾的沸水,跳上跳下汤圆儿似的蚕茧子。随着蒸气喷散出到处都是半腐的、河腥的,又仿佛是阴雨天气返潮的陈汗迹子气味。
不多一会儿工夫,小姨子就把那一点儿生疏给忘了,又恢复小姑娘时候那种不知避嫌的亲热。邱师傅可还不行,倒不是生疏,夹在他们中间的该是另一些说不出的甚么,大约是小姨子的这种“大”罢!“这一锅不是要丧掉几百条命!”
“嘿,何止啊……”
一根丝头断了,这一打岔,丝头接上了,话可接不上去。何止几百条?成千上万的性命。不能拿这个逞英豪,冲鼻子的气味,又是这样子杀生害命的,小姨子语气里又似取笑他,又似瞧他不起,弄得他有点无地自容地没滋蜡味。上十年的手艺,头一回疑心当初怎么挑上这么一份在小姨子眼里一点也不显得体面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