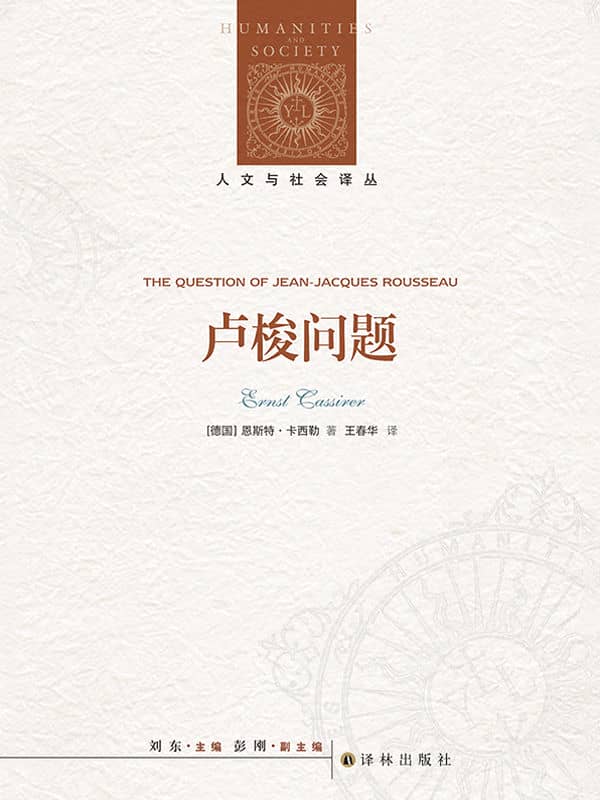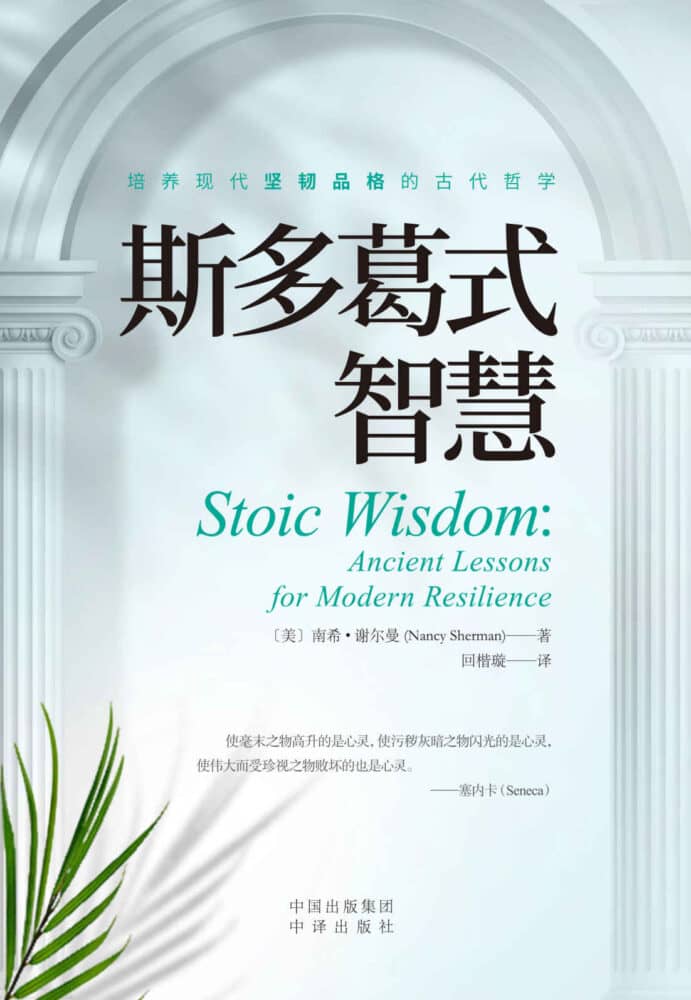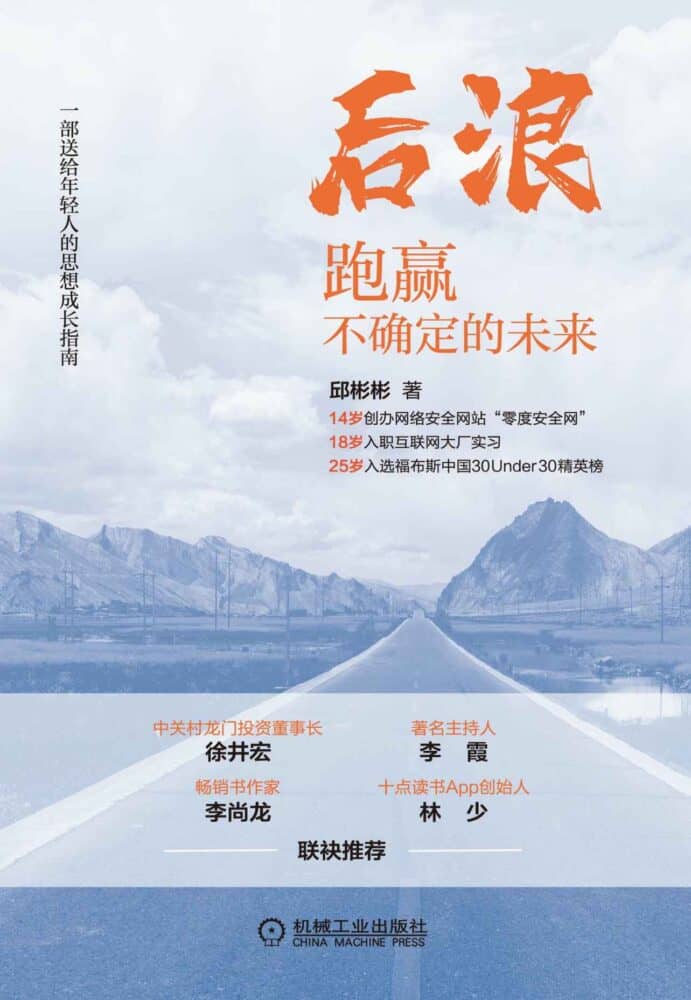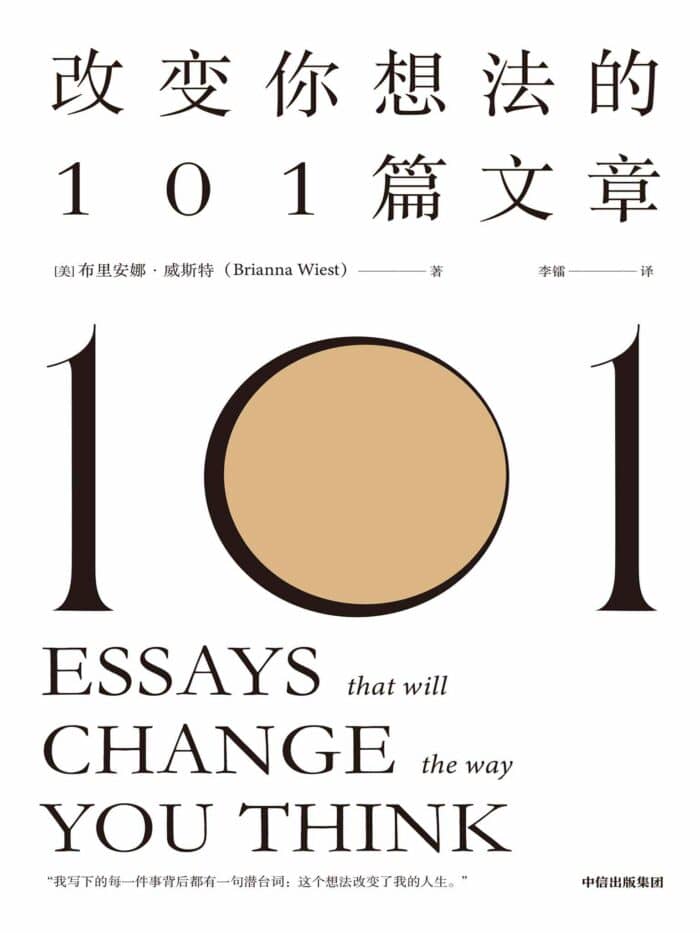作者:
陈年喜,矿工诗人。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是其首部非虚构故事集。
他的作品重振了《诗经》的民间叙事传统,以苍凉细腻的笔触,呈现了中国人悲怆又炽烈的生命力。
茅盾文学奖评委张莉评论说,陈年喜的散文和那些名家放在一起毫不逊色。“天赋好,语言好,靠一种天性。”
简介:
本书是矿工诗人陈年喜首部非虚构故事集,由真故图书出品。
获得
✭6月新浪好书榜
✭7月华文好书榜、《中华读书报》好书榜、绿茶书情好书榜
✭8月文学榜好书榜
✭深港书评2021“年度十大好书”年中榜
作为巷道爆破工,陈年喜深潜于大地5000米深处,用炸药和风镐轰开山体,凿出金、银、铜、铁、镍。
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是王二、德成、小渣子等同样低微的命运。后来有的人在爆炸中跑成一蓬血雾,有的被气浪削成了两半,只有他相 对幸运,只留下颈 椎错位,尘肺病,还有一只失聪的右耳。
翻开《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这些悲怆炽烈的生命逐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艰辛的劳绩,无常的生死,每一个故事,都像陈年喜在矿山深处敲下的石头一般坚硬,炫黑。
【编辑推荐】
1,矿工诗人陈年喜首部非虚构故事集。作者应邀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巡回演讲。《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媒体重磅报道。
2,重振《诗经》的民间叙事传统,挖掘中国人悲怆又炽烈的生存力。震得人头皮发麻。
3,茅盾文学奖评委张莉:陈年喜的散文和那些名家放在一起毫不逊色。天赋好,语言好,靠一种天性。
4,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张慧瑜:《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见证了他二十多年流离西北、西南的颠沛生活,既是一本从秦岭腹地到昆仑山脉的天地之书,也是亿万新工人从劳动中萃取的生命之书。
5,随书附赠陈年喜最新诗集《炸药与诗歌》。
6,你买1本书,我捐1块钱。本书与专注尘肺病救助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合作,你每买一本书,我们捐1块钱,给尘肺病患者子女提供助学金。
7,本书带你辗转中国边荒,遍见奇异风情。一路穿过长江、黄河、叶尔羌河,踏遍新疆的萨尔托海,内蒙的戈壁滩,大兴安岭的茫茫雪山……
试读:
两年前我就想写陈年喜。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题材,早在2015年,爆破工陈年喜就因为写作诗歌《炸裂志》受到媒体关注,已经有了许多报道。编辑问我为什么想做,我记得当时给的理由是,“在矿洞里写诗很浪漫”。
“浪漫”是个主观的词,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个概念,对我也是。那时我二十三岁,见过一些悲惨的人与事,只凭直觉,想象一个人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中写作,有种残酷的、顽强的美。后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轻浮,那些被人称许的诗意背后,是沉重、极强的疼痛,血和泪刺激出来的灵感。
2019年的年尾,我如愿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陈年喜。他早已离开了矿山,远离了曾经滋养他写作的土壤,可他还在写,也因此痛苦。我记录下他的故事,有关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轻,有关人的最大幸福与不幸。写完之后,我再次想起“浪漫”这个词,觉得在这个故事里,它指向一种生的勇气。在极其平凡、遍布枷锁的日常里,偶尔闪现的各类灵光——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感受,我对那种经历就一无所知”
K508从遵义开往渭南,十五个小时车程,硬座售价一百七十元。在沿途的三线小城,工人们登上列车,趴在桌子、箱子上,坐在自带的塑料桶上,铺一张报纸睡在地上。他们的嘴唇多是紫红色,手上有冻疮。指甲泛白,凹凸不平,有时是黑色——那种和泥土、水泥或是煤矿结合而成的黑色,窝藏在眼角、耳朵和指甲的缝里。热水和肥皂对它们毫无办法,每个清晨,黑垢会从皮肤深处像结霜一样泛出来。
“我坐过飞机,也坐过高铁。”几天前,陈年喜在电话里说,前者和慢火车上的人群差别如此之大——人们的穿着、皮肤、面色都不一样,甚至是眼神。五年前,陈年喜接受了一项颈椎修复手术,因为术后无法再承受劳力工作,他告别了矿山。我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他。
距离农历鼠年还有五天,我和陈年喜一起登上了K508。此行的终点是他的陕西老家。
硬座车厢里没有充电插座。我来回地走,观察车厢里的每一个人:有人背着看不出颜色的麻布袋,有人穿着布鞋,有人握着非智能手机,整晚对着空气发呆。我记下他们的样子,第二天对陈年喜提起。听到一些细节时,他能够准确地分辨出这些工人来自哪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川渝地区的人有洗澡的习惯,通常会带着一只水桶,火车非常拥挤的时候,人可以坐在桶上。爆破工的肤色常是没有血色的白,他们常年在矿洞里劳作,晒不到太阳;出渣工的手格外粗糙,一排炮爆下三四十吨石头,全靠人力运出,人们喝下很多的水,排出很多的汗,汗湿在衣服上,结下厚厚一层汗斑;还有管道工,因为常年暴晒,营养奇缺,他们的头发异常枯焦,面色像炭一样黑……
对了,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随身携带锅碗瓢盆,那是打工失败的象征,伴随的常是沮丧和忧虑的眼神。
谈起这些,陈年喜滔滔不绝。眼前的场景一下子将他带回小煤窑的打工生活。这是他最擅长,也最愿意书写的人群。
红色窗花贴在车窗上。又是一个春运。铁老大给他的回忆太多了。有一年,他买了站票到喀什。人与人贴背立着,三十九个小时,他不敢吃饭,因为没法上厕所——厕所也站满了人。
一天一夜后,有的年轻姑娘满脸泪水,站崩溃了。
“我依然觉得我和他们是一个群体,同一个命运层次。”他指的是这个国家三亿的农民工群体。
2015年的岁末,北京东五环外的新工人剧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以工人诗歌为主题的朗诵会正在进行。几盏照射灯的聚焦和几十个观众的注目下,爆破工陈年喜走上台,背诵他在矿山里创作的诗歌。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炸裂志》)
学者、记者、工友都在台下,有人眼里噙满泪水。朗诵会激起不少讨论,甚至引起了国际汉学家的关注。陈年喜因此成名。之后的上百场采访里,曾有一个记者问陈年喜,为何要坚持写诗。他说: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今天仿佛哪里不同。三年前,一个老板为他在贵州提供了一份文职工作。这几年,陈年喜很少写诗了,“冲着稿费”,他在业余时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他必须不停地写,以供养还在上大学的儿子和承受来自家庭的经济负担。
多数写作还是围绕打工生活与矿工题材,可落笔时,画面不再清晰地浮现,没有了“想要诉说的感觉”。
2019年10月,我代表杂志向陈年喜约稿。他写了一位朋友远赴中亚矿山的打工经历,后来他评价这次写作“充满隔阂”——“没有感受,我对那种经历就一无所知。”
2019年,陈年喜书写的一个矿工故事得了非虚构写作比赛的奖。颁奖词肯定文章具有“细腻诗性的文本”和“质朴苍凉的蛮荒气息”。
同为陕西人的作家袁凌却在私下里对他说,你的文笔不错,但是写故事很弱。
“他说得很对。”陈年喜说,他对技巧没有概念,“我全是凭感觉写的。”
凌晨三点,列车开始穿越秦岭。驶过的地方一片漆黑,像极了陈年喜十六年的矿洞生活——有时帽上的顶灯灭了,只有靠触摸岩壁上的钻痕才能分辨方向,人就像这列钢铁之兽,要在黑暗中挺进几千米。
漫长的岁月里,陈年喜曾走在蜿蜒至渤海底的竖井之中,距离地面几千米的地心深处,走过陕北、河南、青海、新疆……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
在南疆的喀喇昆仑山某处,曾有一个河南的爆破工决定离开。老板说,茫茫四百公里的戈壁滩,你走吧。河南人赌气,徒步走了。三天以后,人们在路边发现了河南人的尸体——被捅了两刀,死在路边,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陈年喜写下这个故事,因为这段记忆挥之不去,某种牵挂在心里,“不吐不快”。
他怀念这种感觉。
宿命感
秦岭腹地,一个接一个的弯道通往峡河深处。过了丹凤,两旁的山上长满橡子树,据说国内酿造红酒的木桶都来自这种木材。现如今当地人已不准私自砍伐了。春天的山岭很绿,冬天很秃,四季分明。柿子在树顶冻成黑色的干。
车前经过一个老汉,袖子空着挑一担水桶。“那个人是在山西曲沃县,”陈年喜指着他,曾经也是位爆破工,“一条手臂被炸没了。”
道路两旁林立着各式的墓。墓的主人多是青壮年。陈年喜能就着每一座墓室说出背后的故事。这一座,矿上塌方,失血过多死了;那一座,上山摘蘑菇,中毒死的;最显眼的那一座,在河南灵宝金矿,洞子垮塌,兄弟三个同时被砸死了。按照本地的风俗,在外死的人不能进家门,三口棺材摆在家门口,大雨倾盆下了一个月。
类似的故事每年都在发生。消息总是散播在各类工地的饭间。兔死狐悲,人心里异常地悲伤。可还是不说一句话,各自散开,默默上班,自求多福。
七年前的一个夜晚,河南灵宝的矿山深处,陈年喜得知了母亲患病的消息,食道癌晚期。身无分文,也没有自由,坐在床上,他瞥到床边的炸药箱——他写下了《炸裂志》,写下自己“岩石一样,炸裂一地”。
爆破工的生活在轰鸣中度过。风钻机在岩石上打出两米深的洞,用铁管把炸药抵进最深处,留一根引线在外——引爆,震耳欲聋。放工后的生活却出奇地安静。
克拉玛依的萨尔托海永远是晴天。人烟稀少,信号不通。哪怕山上跑过一只羚羊,工人们都凑一堆,瞧上半天。宁静的生活只剩饮酒、麻将和扑克。
为了逃避某种麻木,每天下班后,陈年喜都会去一个废弃的工房,那里的墙上贴满了《克拉玛依日报》和《中国黄金生产报》。所有的墙面读完了,他用脸盆往墙上泼水,一张张揭下来,再读另一面。
读多了,工作时抱着风钻,思想却飘到很远,一些句子浮现出来,赶紧用笔记下。宿舍的床垫用的是废弃的炸药箱,床头放着笔,离开时卷起铺盖,密密麻麻,写了满床。
纸板在离开工地时都被丢弃了。陈年喜从没有想过,那些文字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甚至刻意隐瞒着工友,“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很特殊”。坚持写作的理由很简单,那时他“感觉自己活着”。2011年,陈年喜开通了博客,一些深夜,他会在手机上按下白天想好的句子,互联网上,寥寥几十个阅读已经让他满足。
2014年,纪录片导演秦晓宇第一次在陈年喜的博客中读到《炸裂志》,当即决定要与诗的作者见面。他正在筹备一部工人诗典,《炸裂志》“一看就是一种中年写作”,带有强烈的沧桑感。他于是直奔矿山寻找诗的作者。
在火车站,远远地,秦晓宇看到一个人从台阶上走上来: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像秦始皇兵马俑一样,”他说,“这硬汉形象和诗歌里的力量感一致。”那天,他兴奋地给搭档吴飞跃打去电话,他们正在筹备的纪录片找到主角了!
纪录片《我的诗篇》之后,秦晓宇又跟拍了陈年喜两年。接触久了,秦晓宇才发现,陈年喜诗歌里的那种力量感只是表象——诗歌涵盖了他所有愤怒的表达,现实生活中,陈年喜几乎从不发怒。“他对命运一概接受,并不想要,或者说不相信能够改变什么。”秦晓宇概括这是一种“宿命感”,强烈的悲剧意识。
2017年的正月里,北京五环外,皮村的剧场,陈年喜瘫坐在舞台上,边上坐着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周围散布着空酒瓶子。
“孙恒,”陈年喜大着舌头,“我尊重是尊重你,欣赏是欣赏你,但我不认同。”2005年以来,孙恒和朋友们创立了北京工友之家,他所倡导的新工人文化主张用“新工人”代替“农民工”的称呼——“让新工人留在城市,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他总这样说。
“我觉得新工人文化没戏。”陈年喜摆摆手。
那时人在北京飘荡。为了每场二千元的辛苦费,陈年喜参与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为知名歌手的演唱写诗作词。有整整三个月,他什么也写不出来。
新春佳节,陈年喜窝在皮村的宿舍里,在电脑上玩蜘蛛纸牌。十六年的爆破生涯只留下了耳聋、胃病和颈椎错位,手术掏光了他所有积蓄,赖以谋生的本领再无处施展,“回到现实中,好像什么都不会了”。
孙恒在那时为他提供了一份志愿者的工作,随车队去北京各地运回社会捐赠的衣物,月薪七百。微薄的薪水无法养家,焦虑时,陈年喜总是对孙恒诉说。那天,借着酒劲,他再一次倾诉。
“陈年喜,”孙恒苦笑,沉默了一会儿,“三吨炸药没有把你炸醒,它把我炸死了。”
三年过去,孙恒离开了皮村,在京郊平谷的一处基地一个院子里继续办工人大学。他不再坚持“让农民工留在城市”,将目标改成了“帮助年轻人返乡创业”。在电话里,我们谈起他和陈年喜醉酒后的那番对话。
“现实是复杂的。”孙恒谈起这些年的无力感,他参与创办的、为农民工子女解决教育问题的同心实验学校今年只剩下三十个学生,随着各个工厂从皮村撤出,曾经聚集到一起的“新工人”又逐渐散开。
“我越来越理解陈年喜为什么会那样说,”孙恒说,“理想主义并不一定都能成功实现,我追求的是这个探索的过程。”
那个夜晚的最后,陈年喜留给孙恒一句话:“我走了,去贵州给景区吹牛了。”
第二天,他踏上了去往南方的列车。
目录:
代序:一个矿工诗人的下半场 / I
炸药与诗歌
确诊尘肺病后的日子 / 002
从疆南到甘南 / 014
我的朋友哈拉汗 / 025
小渣子 / 046
德成 / 057
萨尔托海 / 062
在玲珑 / 070
铁厂沟的饺子 / 082
水桶席地而坐 / 086
乡关何处
父子书 / 097
父亲和摩托车 / 102
母亲 / 106
扶杖的父亲 / 110
父亲的桃树 / 114
岳父 / 119
司命树 / 126
病中一年记 / 133
理发 / 141
我的春节回乡路 / 145
赶路的人,命里落满风雪
媒事 / 157
洞穴三十年 / 168
填埋垃圾的人 / 180
断链的种菇户 / 191
关山难越上班路 / 195
无处胎检 / 199
我的精神家园
生活,真相,书写 / 204
香椿 / 211
挖苕记 / 214
生活有味是清欢 / 219
慵懒 / 222
年 / 227
代后记: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