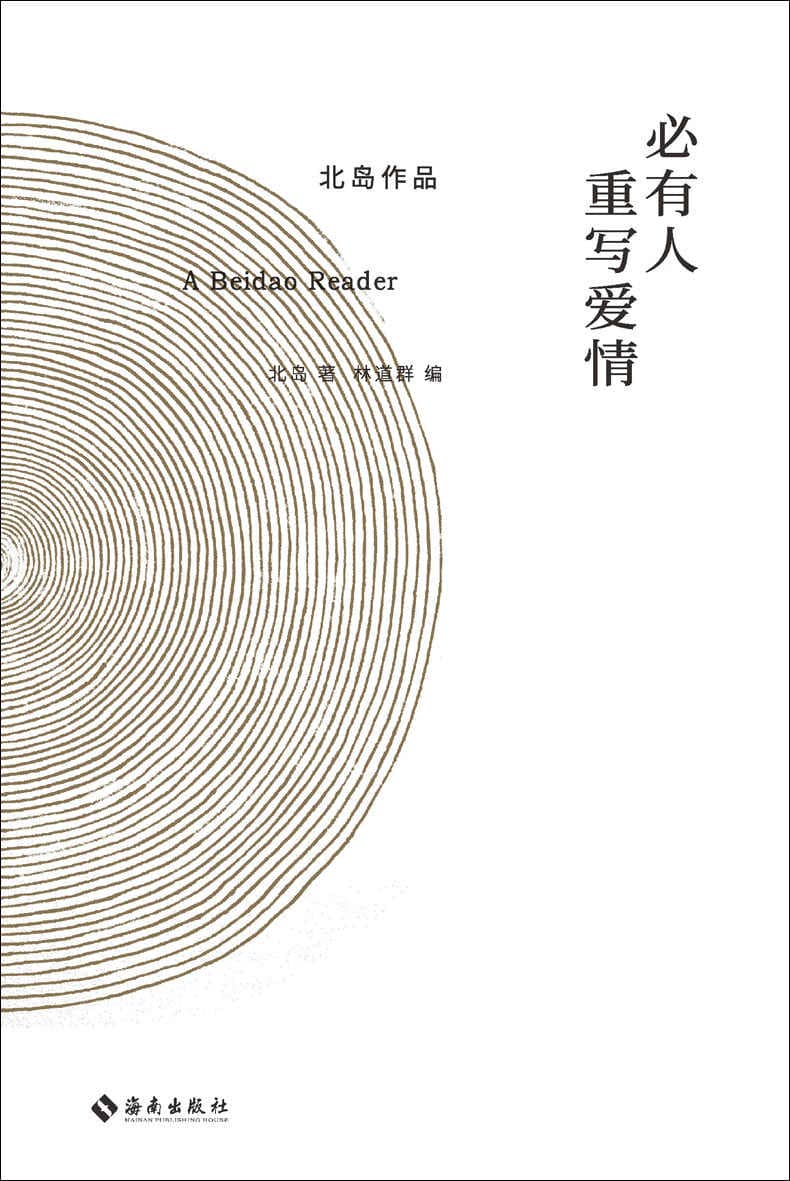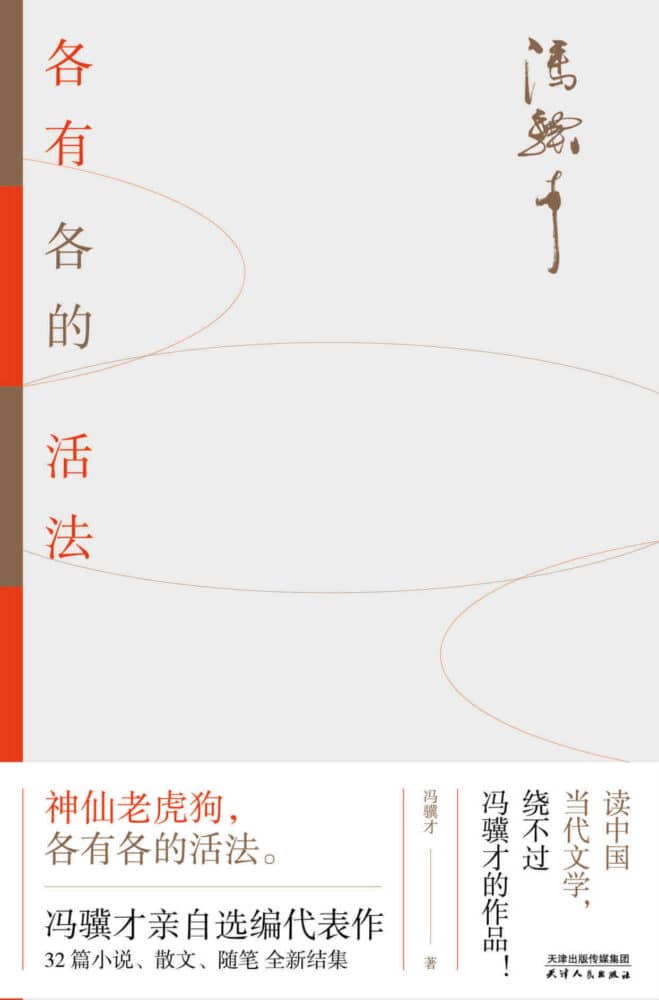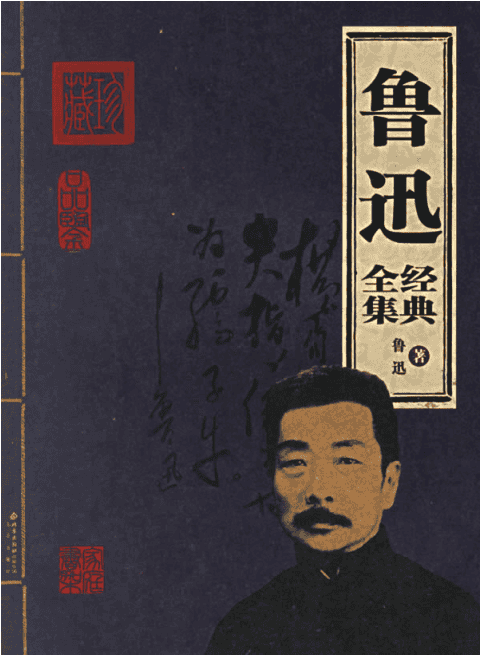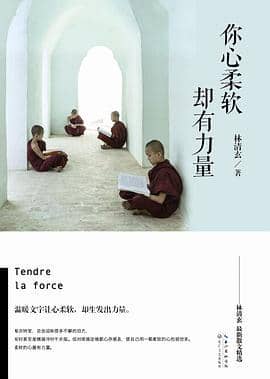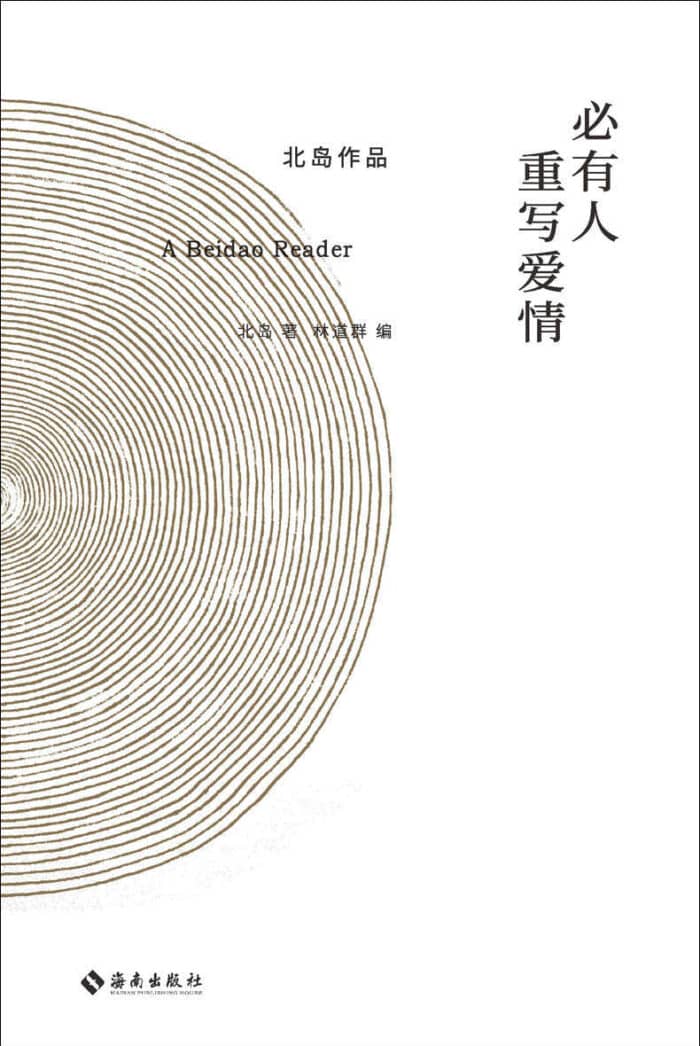内容简介:
《梁晓声文集》尽可能完备地辑录了梁晓声迄今为止创作的全部作品。依据体裁,我们将这些作品厘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卷。基于这些作品的丰赡多姿和规模宏大,我们审慎编校,分期出版。这里辑录的是散文,分作15卷编排。这些作品大多曾发表过,辑入本集时,作者亲自作出选择和修订,对文章的语言和内容作了适当改动与调整,使之更加恰切。散文的分卷和编排顺序也由作者亲自审定,大体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将相同或相近主题的文章编排在一起。 梁晓声的散文创作时间跨度很大,创作背景复杂多样。在编校中,我们尽量保持作品最初发表时的原貌,对一些作家用语习惯和具有时代特色、地域特色的语汇皆予以保留,同时根据国家现行出版编校规范订正了少许文字和标点。 梁晓声的散文首次发表时都是各自独立的。此次结集,为使体例一致,我们对散文的篇章布局,文中的数字用法、引文格式等作了大致统一;确实无法做到全部统一的,各卷保持统一。 《梁晓声文集》内容博大,文采斐然。虽然我们尽可能地认真审校,但限于学养和经验的不足,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谨致诚挚的谢忱。
作者简介
梁晓声,男,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荣城市泊于镇温泉寨。汉族。原名梁绍生。现在居住于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文学专业。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
当过知青,1968年下乡赴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厂长。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人文学院教授。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浮城》《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近年发表有长篇小说《生非》,其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文章《慈母情深》(《母亲》的节选)被选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第9册。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短篇小说集《年轮》等。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为了收获》《学者之死》《一只风筝的一生》《双琴记》分获《小说月报》百花奖。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
试读:
复旦与我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感激》。
在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讲到了当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我的关爱。在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他们的关爱还体现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护。非是时下之人言,老师们对学生们的关爱所能包含的。在当年,那一份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爱,铭记在一名学生内心里,任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凝重的。
我还讲到了另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
那么他是复旦哪一个系的老师呢?
事隔三十余年,我却怎么也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了。
我所记住的只是一九七四年,他受复旦大学之命在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也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据说那一年复旦大学总共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他肩负着对复旦大学五六个专业的责任感。而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中的一个,万分幸运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为了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到一名将来或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他在兵团总部翻阅了所有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当年,兵团总部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创作成果编为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与时政评论六类集子。一九七四年,兵团已经培养起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分散在各师、各团,直至各基层连队。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基层连队抬木头。兵团总部编辑的六类集子中,仅小说集中收录过我的一篇短篇《向导》。那是我唯一被编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
《向导》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职工的率领下进山伐木。那老职工在知青们看来,性格孤倔而专断——这一片林子不许伐,那一片林子也坚决不许伐,总之已经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到的树,一棵也不许伐。于是在这一名老“向导”的率领之下,知青离连队越来越远,直至天黑,才勉强凑够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回连队也难以劈为烧材的那一类。而且,他为了保护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还被倒树砸伤了。即使他在危险关头那么舍己为人,知青们的内心里却没对他起什么敬意,反而认为那是他自食恶果。伐木拉到了连队,指责纷起。许多人都质问:“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么木头?劈起来多不容易?你怎么当的向导?”而他却用手一指让众人看:远处的山林,已被伐得东秃一片,西秃一片。他说:“这才几年工夫?别只图今天我们省事儿,给后人留下的却是一座座秃山!那要被后代子孙骂的……”
这样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是比较特别的。主题的“环保”思想鲜明。而当年中国人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环保”一词。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
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却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于是他要见一见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那是那一条铁路的终端,往前已无铁路了,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团。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他,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
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内心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分之想。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而且,说来惭愧,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一名北方青年,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一向不会发生兴趣的。但有人和我谈文学,我很高兴。
我们竟谈了近一个半小时。
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宣泄。
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问我看过没有,有什么读后感,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问题”,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会对你不利”。这是关爱。在当年,也是保护性的。后来我知道,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
我入学几年后,就因为转氨酶超标,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
至今想来,点点滴滴,倍觉温馨。进而想到——从前的大学生(他似乎是一九六二年留校的)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不同。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但却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系的老师。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他这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和我谈到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这是耐人寻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皆一命,是谓生日。但有人是幸运的,能获二次诞辰。大学者,脱胎换骨之界也。“母校”说法,其意深焉。复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学府;所育桃李,遍美人间。是复旦当年认认真真地给予了我一种人生的幸运。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师身上所体现出的认真,我认为,当是复旦之传统精神的一方面吧!我感激,亦心向复旦之精神也。故我这一篇粗陋的回忆文字的题目是《复旦与我》,而不是反过来,更非下笔轻妄。我很想在复旦百年校庆之典,见到一九七四年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生的那一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