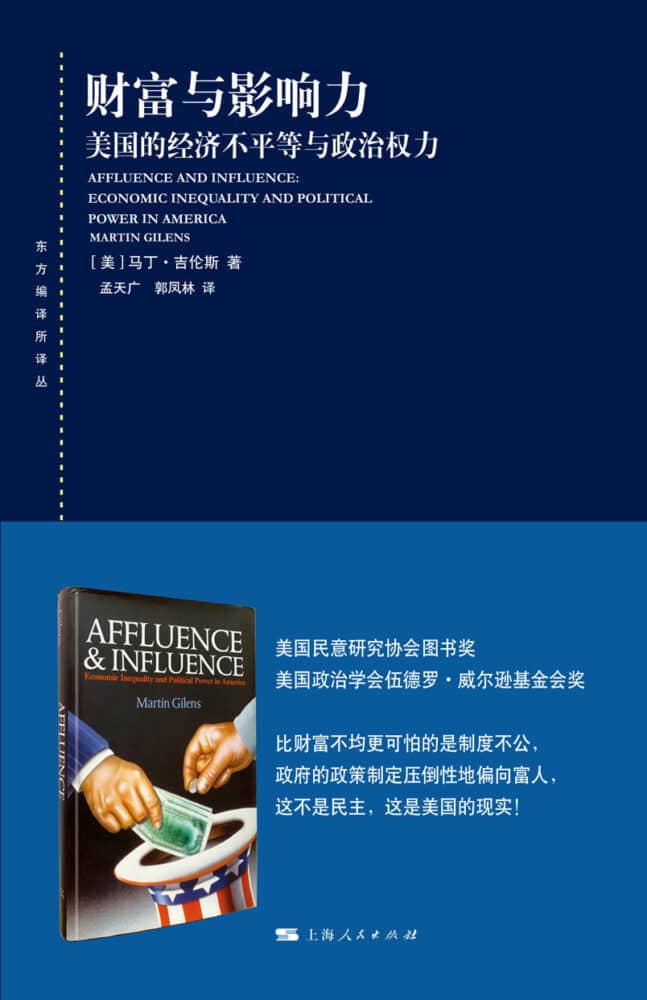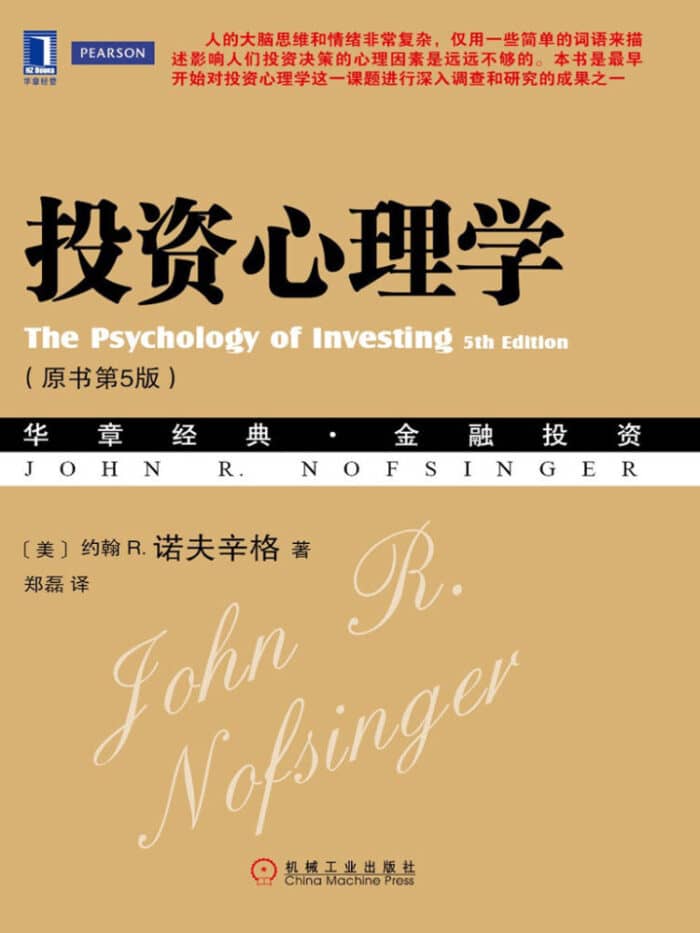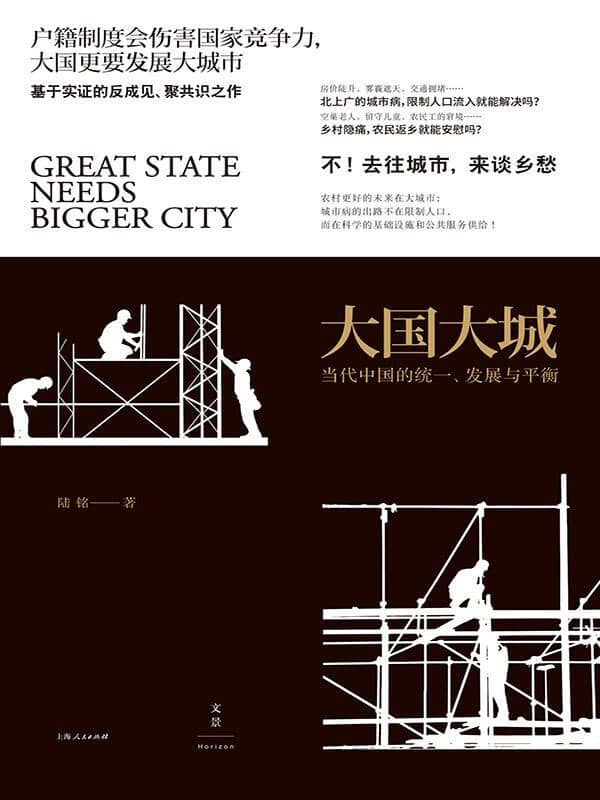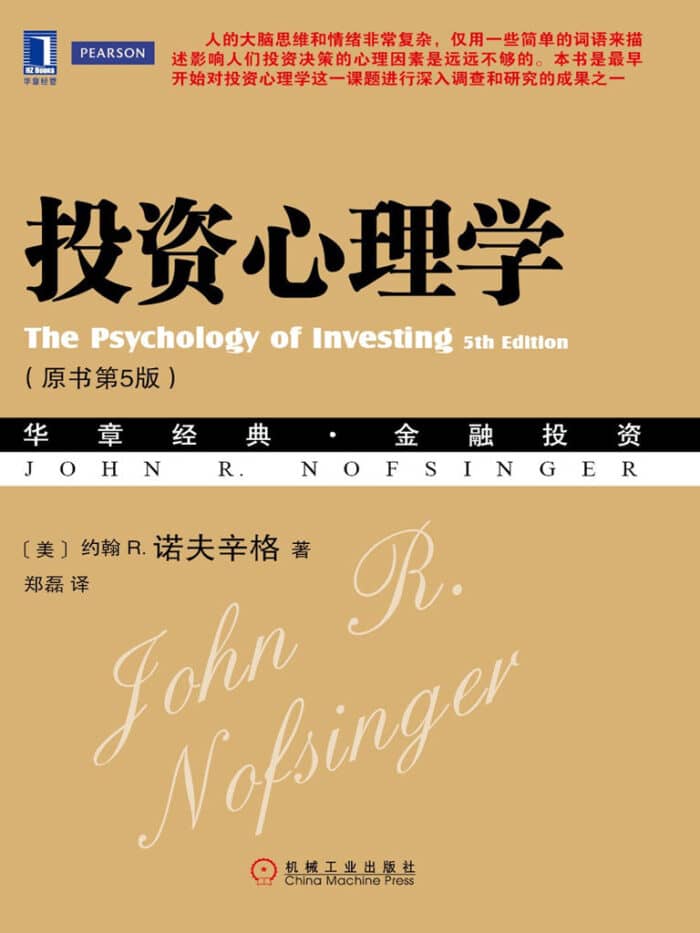作者:
梁鸿
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有非虚构文学著作《梁庄十年》《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
简介:
从失去声音的农村女性到返乡的打工者
梁鸿蕞新非虚构作品
展现急速变化时代下中国村庄的变迁
【作品看点】
★ 横跨十年,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梁鸿重审故土,构建更为完整、曲折的农村变迁史。
2010年和2013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相继出版,前者以梁庄和生活其中的人为切入点,勾勒出中国乡村的内部结构;后者则将目光投向离开了梁庄的人,讲述了背井离乡、散布全国的梁庄打工者们的故事。两部作品接连问世,令读者们将目光集中到了梁鸿的家乡——一个普通的河南村庄:梁庄。梁鸿成功地向读者们展现了真实的乡村图景,并以此映射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以及农村面临的转型困境。十年后,梁鸿再次将梁庄带回我们的视野,接续前两部的主题,重新审视故土,为读者们构建了一部更为完整、曲折的农村变迁史。
★ 再访逃离村庄的年轻人、背井离乡的打工人,记录时代转折下真实的个体命运。
十年间,梁庄整体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梁庄人也在时代转折中迎来各自不同的命运。本次返乡,梁鸿再一次走访那些当初离开家乡的打工者:当初怀揣一百万现金、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万敏,在北京漂流许久之后返回故乡的梁安,唯一一个移民西班牙的打工者学军,吴镇的第一个千万富翁秀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故乡,一些人誓死不归,一些人则遭逢了意想不到的变故。时间飞逝,站在他乡与故乡、梦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少小离家的人们又将何去何从?
★ 穿过偏见与歧视、流言与恶意,传递梁庄那些“消失的女人们”最真实的声音。
“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在梁庄,生而为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人们却常常忽视她们的存在:她们刚一出生就面临歧视性的环境;稍长大之后,又在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进入青春期;蕞后在婚后成为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蕞终失去自己的姓名。此次返乡,梁鸿寻回了村庄中“消失的女人”,久别重逢,畅谈她们从小到大面临的种种不为人知困境:家暴、偏见、歧视、流言蜚语……“我想把她们聚拢在这本书中,让她们重新在梁庄的土地上生活,尽情欢笑、尽情玩耍。”
★ 贾樟柯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主要讲述者,文学联动影像,重构消逝的故土。
“我初次阅读的梁鸿老师的“非虚构”作品是《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这两本书所写的,一部分是乡村内部的结构,一部分是出去打工的人群,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熟悉的。我自己在县城里面长大,但也有大量乡村生活的记忆经验……透过梁鸿老师的书,我衔接的就是我的记忆。
……在拍摄梁鸿老师的时候,这部电影的结构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跟梁老师坐在裁缝店里面访谈,听她谈自己的生活时,我脑子里面第一次出现了结构意识……可以说是她贡献了电影的结构。”
【内容简介】
2010年,《中国在梁庄》首次出版,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下的中国村庄的变迁。十年之后,作者梁鸿再次回到故乡,重访当年的书中记述的人和事。十年当中,一切都在发生改变,又似乎全无变化:一些人永远离开了这里,一些在外漂泊的人重返此地,村庄的面貌、河流和土地都与从前不同。而人事变幻之中,梁庄和梁庄人所透露出的生机和活力却不减当年。此次回归,梁鸿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家乡,以细腻的描写和敏锐的洞察,将梁庄的人们再次带回我们的视野,并借由对他们生活的追溯,描摹出一个普通村庄绵长而有力的生命线——这生命线既属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人们,也属于身处同一股时代洪流的人们。
【名人推荐】
梁鸿的确是一个“五感全开”作家。她的捕捉能力就像一个音乐家听到一段音乐,能分辨出每种乐器的音色;当她进入到生活场景里面的时候,能捕捉到任何一种独立的气息,并且能把它写出来。
——贾樟柯
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梁鸿
试读:
第一章 房屋
梁庄的新房在不断增加,老房也迟迟不愿离场。它们以日落西山的姿势顽强地支撑,几面破败的山墙,一段残垣,腐朽断裂的屋架,点缀着梁庄的风景。新房和旧房,共同造就了梁庄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混乱的内部空间。
如果只是一个旅行者,他所看到的,完完全全是一个杂乱无序的北方村庄。
小字报
2020年7月,在连续十几天的暴雨之后,和其他任何一个年份的这时刻一样,湍水又涨了。
只不过这一次,湍水有鱼。在前面将近三十年间,湍水一直重度污染,大鱼几近消失,只有在一些分散的小水洼里,才能见到像小梭子一样的野鱼苗。一段时间后,这些野鱼苗也将消失不见。这几年,湍水渐清,站在水边,经常能看到水中大鱼跃起的身影。
湍水的水位暴涨到河道中那条沙土主路的位置,浩浩荡荡,一路翻滚下去。梁庄的男人们非常兴奋,举网提桶,几人结伴,从村庄后面的路下去,到南水北调大河和湍水交叉的那个大桥下面,布网逮鱼。那个位置沙少石子多,易于站立,也易于逃跑,万一上游涨水过来,几十步远就是护河堤,可以很快爬上去;而其他地方,是一望看不到边的平坦河坡。
技艺高超且胆大的人很快就抓到了鱼。大鱼足有五六斤,小鱼也有尺长,鲜嫩无比。一般情形是,大家抓到几条鱼后,回村聚在其中一家,煎炒烹炸,吃着鱼,喝着啤酒,聊着大天,到下午四五点钟,又到河里去抓鱼。一时间,村庄人声鼎沸,简直像过节一样。
一天早晨,韩家一个年轻媳妇清晨起来洗脸,洗完脸,端着脸盆往院子门口泼水,突然发现门口的电线杆子上贴了一张传单。她以为又是上面出了什么通知,就凑过去看。这一看,她给吓住了。家里男人已经下河抓鱼,一时找不来人商量,她就撕下那张传单,急匆匆往村口红伟家那边跑。[1]红伟家是梁庄的新闻交流中心,从早上六七点钟到晚上八九点钟,都有人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在路上,她又碰到另外一个年轻媳妇,也一脸慌张,还有点莫名兴奋,手里拿着同样的传单,说是在她家门口的电线杆子上发现的。她们两家都在梁庄村中心的主路上,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她们一路往村前跑,边跑边注意观察路边的电线杆,沿路没有发现同样的传单。
红伟家门口,一群人围在一起,正聚精会神地看一条鱼。
那天早晨,红伟在河里抓到一条二十来斤重的大草鱼,大家都赶过来参观。那条大草鱼躺在水泥地上,翻着白眼,大张着嘴巴,艰难地一呼一吸;但是,鱼尾仍用力扑扇,试图把身体带起来,但只徒劳地搅起了水泥地上的灰尘。人们啧啧感叹。有多少年了,湍水没出现过这样大的鱼了。
红伟家隔壁的凤嫂家门口,石凳四角已经摆上茶杯,中间放一副扑克牌。几个老牌友坐在那里,正慢悠悠喝茶,等着牌场开始。
两个人拿着传单,一头扎进人堆里,嘴里嚷着:赶紧来看,这是咋回事啊。其中一个小媳妇眼尖,看到张香叶坐在凤嫂家的牌场边,就跑过去,说:“香婶儿,你快看,这说哩都是啥啊?”
张香叶拿起传单看,约有两分钟的样子,脸色突然变得煞白,身子晃了晃,有点站不住似的。她把传单揉成团,装到口袋里,眼睛垂着,扒开人群,往外走。快走过红伟家门口时,另一个年轻的媳妇追过去,把另一张传单递给她,她默默接住,也揉成团,装进口袋里,往家的方向走。
人们目送着张香叶,直到她走过村口的那条拐弯路,人不见了,才像突然醒悟过来似的,争相说起话来。
另外有两个人,从口袋里各掏出一张传单,和刚才那两张一模一样。
人们头挨着头,碰在一起,开始认真研究传单上的内容。那条大草鱼被遗忘在一边,它的尾巴早一动也不能动了,两只眼睛还偶尔翻一下,露出里面的白眼。
揭发信
你张香叶干了什么事,不要以为过了这么多年大家忘了就当没事了。
当年你和韩天明的丑事全村人都知道,你不守妇道,和韩天明眉来眼去,在家苟合,你的三儿是谁的孩子,大家都清楚。
你看韩天明家里有钱,你好吃好喝好沾光,就往人家身上贴。1974年冬天,你和韩天明在你家做的啥事村里人都知道,你丈夫不在家,你就天天领人回家,你叔伯哥知道了,堵了好几次门,把你们堵在床上,打得你鼻青脸肿。你说你改了,以后再也不会了。你丈夫从部队回来,看见你给韩天明做的衣服、鞋,跑去找韩天明,韩天明都承认了,你还不承认。后来,部队上要定性你是破坏军婚,你害怕了,还写了保证书,这事×××、×××都知道,当年,他们都是证人。现在,他们都死了,死无对证了,你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人道德败坏,就该叫大家知道,别想着老了就变好人了。
张香叶,今年七十五岁。在梁庄,她以无可挑剔的品行,大家闺秀般的举止,干净整齐的装扮,多年来助人为乐的精神,而为大家所赞颂。她是村里为数不多懂得婚葬礼仪的老人,无论哪一家嫁姑娘,她都会默默在场,帮着装箱,准备各种礼仪所需的东西,教姑娘怎么应对。从准备出嫁到把人送走,张香叶一直都在,而且每天最早到,最晚离开。如果梁庄的老人去世,张香叶更是从开始到结束,全程在场。每天半夜离开,早晨四五点就来。她教亲属怎么清洗老人的遗体,老人的寿衣,她也一层层帮着穿,孝子的孝布怎么叠、怎么戴,老人口里放的东西,手里攥的东西,她都帮忙去做,让亲属不落下任何礼数。有她在,大家的心就不慌。
听村里年龄稍大一些的人讲,早些年,张香叶家里有缝纫机,她会剪衣服做衣服,一到春节,去求张香叶的人排成长队,张香叶基本上不拒绝。曾经住在她家隔壁的霞子妈说,每年那时候,她家的缝纫机咔嗒咔嗒彻夜响,但是,她从来没收过谁家的钱。
至少就我而言,小字报里所说的事情,我从来没听说过。韩天明作为梁庄的传奇人物,我们倒是从小到大一直听说。他的女儿和我同岁,小时候一起上学放学,我很小就知道她父亲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不要她妈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和张香叶的事情。
那天,我和霞子一边顺着韩家那条路往村里走[2],一边数着旁边坑塘上盖的新房。在梁家和韩家交界处的那两个坑塘早已被填满,左右两个坑塘盖了七座新楼。
在我少年时代,一到夏天暴雨季节,水涨得很高,这两个坑塘中间的那条路会被完全淹没,人们都小心翼翼地从中间蹚过,坑塘的一边有一个沟渠,水往河坡方向排。据老人讲,这条沟渠一直就有,得亏它连通了村里六七个坑塘,否则,村庄早被淹没了。
现在,这条沟渠上面,也盖上了房子。
远远地,张香叶沿路走过来,低着头,往左边自己家方向拐。我刚要扬手打招呼,霞子妈赶紧拦住,说:“别叫了。”
在霞子家老屋的前面,是韩万杰家——梁庄最神秘的一家人。他们一家很少和村庄里的人交往,好像自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院子,虽然这里离我家只有五十米远。韩万杰的妈妈,传说中梁庄最厉害的婆婆,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据说她家的五个儿媳,在她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从清晨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一整天都不停忙碌,屁股从来都不敢沾一下凳子。
张香叶是这家的四儿媳。她丈夫韩万胜早年被送养给别人,长大后才自己回来,所以兄弟情谊并不是很深。张香叶早早和大院分了家,在大院前半部分挖出一个正方形,盖了房子。
霞子妈突然朝大院方向努了努嘴,示意我看。韩万杰家的院门大开着,有人正从院子里往外走,看见我们,那人吃惊地“啊”了一声,说:“早啊。”
霞子妈说:“哟,清辉啊,啥时回来了?”
“前天。招待几个朋友。”
“小清,你还记得吗?”霞子妈指了指我。
他看了看我,摇摇头,笑着说:“还真没印象,太多年不在家了。”
“光正家四闺女。”
清辉做恍然大悟状,但看表情,其实还是没什么印象。
我也不认识他。韩万杰家的孩子从来不和村庄的其他孩子玩。记忆中,他们每天从院子里出来,去上学,放学再回到院子里,从来没有在院子以外的地方出现过。即使是一家之长韩万杰,也只是偶尔在晚饭之后,从院落里踱步出来,看见人,微微笑着点头,并不多说。在极少的时刻,我从他家院落外经过,透过开着的院门,能看到院落里面盛开的月季,一畦畦碧绿的青菜。那里面的空间很深,很静。
清辉邀请我们进屋坐一会儿,话里话外透着客套,我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就进去了。我太想看看了。
一栋两层楼房结结实实矗立在院落的左后边,楼房前面的空地做了水泥硬化,院子里摆着朱红实木的圆桌、椅子、柜子,还有棕色皮质沙发,有工人正在忙着安装。院落的右后边,是一栋老房子,这座当年威严无比的青砖大屋,被楼房挤得像个佝偻失势的老人。老屋前面,是一方菜地,茄子、西红柿、苋菜、小青菜,长得正旺,可以看出主人精心打理过。再前面,是张香叶家的后墙。后墙左侧,一条窄窄的小路,通往张香叶家的院落。
清辉已经退休。这次回来,是想把院子好好收拾一下,把屋里的家具、设施再完善一下。他打算以后每年都回来住几个月。
从清辉家出来,霞子妈发出感叹:“都是有钱烧的。年轻时一次都不回来,老了老了说要回来住,还不是想显摆一下?我要是有地方去,我是一天都不住这儿。”
霞子在一旁反驳说:“就让你去街上我那儿住两天,你都不去。连夜都不隔,吵着要回来。”
大家都笑起来。霞子妈牙尖舌利,活跃异常,可也是一个死硬派,除了自己的那座老院子,两儿一女,谁的家都不去。
霞子妈低声说:“院里的菜园子,是张香叶的,清辉上次回来让张香叶把菜园平掉,张香叶不愿意。别看张香叶、韩万胜是清辉的四婶四叔,可他们关系很不好,他爹韩万杰那时候对他四弟都不好,到他们这一代,也看不起他四婶四叔。”
梁庄的年轻一代对小字报的内容感到震惊,在他们心目中,张香叶是梁庄的道德楷模,是最理想的老人形态。那些年轻的小媳妇都渴望自己的婆婆有着张香叶的性格,而男孩则想着要是自己的亲妈有张香叶那么能干、那么明理就好了。现在好了,一记重棒击过来。他们追着老人问当年的事情,或往老人堆里凑,想多了解一星半点真相。
老人们则一心只追问一个事情:谁写的小字报?
老人们掰着手指头算谁家和张香叶有仇,也大约拼凑和还原出了当年的事件经过。
在1967年或1968年,张香叶嫁给梁庄的韩万胜,当时,韩万胜在部队当兵。在那个时代,姑娘嫁给当兵的男子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少一个人的口粮不说,隔几个月还能寄点钱或军装什么的回来。张香叶个子高大,白白净净,不爱和村里其他妇女家长里短,转年就生了大儿子,也是本本分分下地干活挣工分,闲时在家剪衣服做衣服。
她和韩天明什么时候开始偷情的,没人知道。但是,有蛛丝马迹可寻:韩天明在吴镇上班,回来后没事就爱往张香叶家钻。“寡妇门前是非多”,虽然张香叶有丈夫,但也形同没有。其他男人也瞅,也想往张香叶屋里钻,可是都被张香叶轰出来,只有韩天明进去了,好久才出来。
当时,韩天明在吴镇供销社上班,吃商品粮,手握各种生活资料,在计划供应的年代,那是绝对权威。张香叶一人带两个孩子,挣不来工分,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有“留心”的人发现,韩天明经常往张香叶家去,进去时手提包鼓囊囊的,出来时手提包干瘪瘪的。一天晚上,韩万胜的三个哥哥埋伏在墙头,韩天明进去不久,三个人就破门而入,抓了个现行。其中,韩万胜的大哥韩万杰狠狠踹了张香叶裆部几脚,二哥拽着张香叶的头发扇她的脸,韩天明趁人不备,溜之大吉。
韩天明的老婆赵梅枝早就忍不下这口气,这下逮住机会,绕着张香叶的门口,直骂几天几夜。张香叶关门闭户,自始至终没有应战。可有眼尖的人发现,这件事情过去后不多久,韩天明就又开始出入张香叶家。这一次,韩万杰拉着张香叶去了韩万胜所在的部队,逼韩万胜和张香叶离婚,并且上告到部队领导,说张香叶是在破坏军婚。据说,张香叶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再犯错。
事情传回梁庄,赵梅枝又到张香叶家门口狠骂了几天,说部队替天行道,替她出了口恶气。韩天明到张香叶家门口,拖赵梅枝回家,赵梅枝不走,两个人在张香叶家门口打了起来。张香叶一直没出来。韩天明赌气离开梁庄,到山西一个亲戚的矿上干活。
如果细究的话,也只有赵梅枝和张香叶是死敌。韩天明到山西后,很快又有新的女人,并且,坚决要和赵梅枝离婚。
但是,贴小字报这件事不可能是赵梅枝做的。首先,她不可能懂得到街上打印这些东西,她老得都快走不动了。她本来就不爱和人交往,自从和韩天明离婚后,更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其次,她儿媳也不可能帮她去做这件事,赵梅枝和儿媳的关系向来不好,虽然同住一个院子,但从来都是各吃各的。
“那就捋捋现在村里七十岁往上的人,看有哪些。”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除了生病躺在床上的,村里七十多岁的人大部分都在现场。
“要不是有深仇大恨,谁会翻出五十年前的事情来恶心人?”
峰叔踌躇着说:“也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清辉这次回来有啥变化没?”
大家问:“有啥变化?”
“往常清辉回来,都会到前院他万胜叔家借电动车,这次好像没有?”
倒是啊。确实没借,他每次出来都是骑自行车。
峰叔对旁边的霞子妈说:“你还记得不?上次清辉回来,咱们去他院子看,张香叶在那个院子里种的菜被他毁了一半,打的隔断也被推倒了。你说,清辉一年就回来几次,他毁人家张香叶的菜园子干吗?”
“回来几次?一次也不会回。要不是为让他奶奶有个落棺材处,那个楼房应该也不会盖。”
这个事情梁庄的人都知道。清辉奶奶是这个大院的第一代女主人,韩万杰去世后,她跟着清辉又住了好多年。活到九十三岁那年,老太太终于扛不住了,随时都有可能过去。她告诉孙子,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回梁庄,她要在梁庄办丧事,要埋在梁庄。可梁庄的房子早已坍塌,无法住人,更无法办丧事。奶奶又极不喜欢韩万胜这个儿子,不愿意把棺材停在他家院里。贤生的棺材最终放在野地里的事情成为全村人的教训[3],许多长年在外地的人都因此又回来盖房。于是,几个孙子一商量,赶回梁庄盖房。房子落成,又紧赶着把老太太接回来。回梁庄三天后,老太太去世。这件事在村里传为美谈。
“那可说不准。房子一盖起,他就当个事儿了。你没见清辉这几年回来更勤了,退休了,没事了,也想回来住,他看院子里的菜当然不舒服了。”
人们像打开了一个新思路,纷纷发现清辉这次回来不同于往常的地方。譬如这次院子常常开着,和过往的村人聊天时,会提到他要把这院子抹平,再盖三间平房。譬如他这次回来根本就没去张香叶家;往常,除了借电动车,他还会在她家吃饭、喝酒。不管怎样,在梁庄,他们血缘关系最近。
是啊是啊。所有人都恍然大悟。
“我猜啊,早年清辉爹他们打过张香叶,结有仇气,这两年,因为清辉又回来盖房子,要收回院子,还要再盖,估计又闹矛盾了,张香叶也在其中说啥难听话了。清辉就生气了,写了这个小字报。不然,谁会费恁大的事做这件事。再说,他平时都住在大城市里,家里肯定有打印机之类的,自己就可以打印,连儿女都可以不知道。”
是啊是啊。霞子妈分析得头头是道,所有人都点头称是。
这件案子算有了眉目。所有人都默认是韩清辉贴的小字报,目的就是为了再盖几间房子。
“万胜和清辉虽是亲叔侄,可是,在房子的事情上,清辉那可是牙撕口咬、毫不留情的。再说,万胜是从小送给别人家,长大之后才回来,大家一直不亲,早年张香叶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个由头,当时就是想把他们赶走。”
不管怎样,七十五岁的张香叶,在生命最末段,经过一生的漫长赎罪之后,突然间,又回到了年轻时代的原点。她大概要背着这沉重的包袱入土了。
“不检点就是不检点,也不怪别人。这种事,从头到尾就不应该做。”按照老人们的议论,那时候都穷得要命,张香叶家实际上还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不至于为点粮食出卖自己。更何况,像韩天明这样的溜光蛋,哪家媳妇会随随便便和他说话,让他进屋?还是自己不检点,谁也不怨。
也有人埋怨那两个年轻媳妇不懂事,像这样的事情,看见了就看见了,把它撕掉就行了;不撕掉就算了,还专门拿到人堆里让人看;拿到人堆里也就算了,看到张香叶在那儿,还专门让张香叶本人看,这不是专门添乱吗?那两个小媳妇有口难辩,转过头来骂自己家男人:“都是你嘴贱,欠吃鱼,大早起就往河里跑,逮住啥鱼了?!”
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张香叶又开始出现在文哥家的门前。她安静地坐在凳子上,面带微笑,和大家在一起聊天、喝茶、打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大家觉得张香叶平白受了这么大的磨难,反而对她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