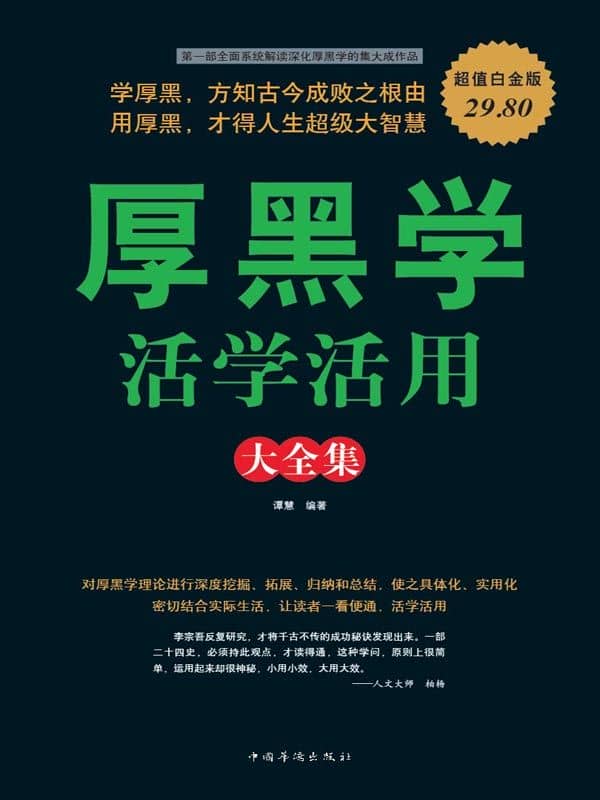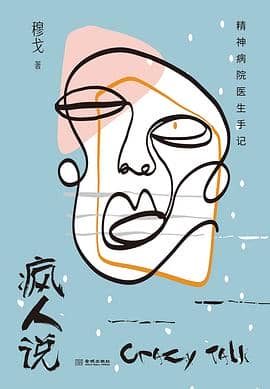内容简介:
《我的精神家园》是王小波的一部杂文集。话题大多涉及他对生活方式、电影等媒体的看法以及国外见闻的思考。他从身边小事入手,以犀利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电光石火般让人幡然惊醒。我们在他的精神家园中穿行着,感受着他对思想,对自己,对写作的真诚,领悟着他思考的姿态、深切的人文关怀、平实豁达而宽容的理性精神。徜徉其中,我们分明听见了他从天堂里发出的笑声和他充满机智妙趣的耳语。
作者简介:
王小波(1952—1997)
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到云南插队。后在山东转插,做过民办教师。1973年在北京当工人。
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1986年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回国,曾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
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从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数不清的赞誉和追捧,从没有人像他那样有无数青年自愿充当其“门下走狗”。他的小说为读者贡献了现代汉语小说的阅读快感,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别样的世界;他的杂文,幽默中充满智性,为读者打开一条通向智慧、理性的道路,被一代代年轻人奉为精神偶像。
他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亦是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
代表作有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小说《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其中《黄金时代》《未来世界》分别获第十三届、第十六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编剧奖。
试读:
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从男人的角度谈女人的外在美,这个题目真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绝对的命题。从远了说,海伦之美引起了特洛伊战争;从近了说,玛丽莲·梦露之美曾经风靡美国。一个男人,只要他视力没有大毛病,就都能欣赏女人的美。因为大家都有这种能力,所以这件事常被人用来打比方——孟夫子就喜欢用“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个例子来说明大家可以有一致的意见,很显然,他觉得这样一说大家就会明白。谁都喜欢看见好看一点的女人,这一点在男人中间可说是不言自明的。假如还有什么争议,那是在女人中间,绝不是在男人中间。
当年玛丽莲·梦露的三围从上面数,好像是三十四、二十二、三十四(英寸)。有位太太看这个小妖精太讨厌,就自己掏钱买了一套内衣给她寄去,尺寸是二十二、三十四、二十二,让她按这个尺寸练练,煞煞男人的火。据我所知,梦露小姐没有接受她的意见。这是说到身材,还没说到化妆不化妆、打扮不打扮。这类题目只有在女人杂志上才是中心议题,我所认识的男人在这方面都有一颗平常心,也就是说,见到好看的女人就多看一眼,见到不好看的就少看一眼,仅此而已。多看一眼和少看一眼都没什么严重性。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这里,这问题在女人中比在男人中敏感。
大贤罗素曾说:人人理应生来平等。但很可惜,事实不是这样。有人生来漂亮,有人生来就不漂亮。与男人相比,女人更觉得自己是这种不平等的牺牲品。至于如何来消除这种不平等,就有各种解决的办法。给梦露小姐寄内衣的那位太太就提出了一种解法,假设那套内衣是她本人穿的,这就意味着请梦露向她看齐;假如这个办法被普遍地采用,那么男人会成为真正的牺牲品。
在国外可以看到另一种解决不平等的方法,那里年轻漂亮的小姐们不怎么化妆,倒是中老年妇女总是要化点妆。这样从总体上看,大家都相当漂亮。另外,年轻、健康,这本身就是最美丽的,用不着用化妆品来掩盖它。我觉得这样做有相当的合理性。国内的情况则相反,越是年轻漂亮的小姐越要化妆,上点岁数的就破罐破摔,蓬头垢面——我以为这是不好的。
假如有一位妇女修饰得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是很高兴的。这说明她在乎我对她的看法,对我来说是一种尊重。但若修饰不得法,就是一种灾难。几年前,我到北方一座城市出差,看到当地的小姐们都化妆,涂很重的粉,但那种粉颜色有点发蓝,走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尚称好看,走到了暗处就让人想起了戏台上的窦尔敦。另外,当地的小姐都穿一种针织超短裙,大概此种裙子很是新潮,但有一处弊病,就是会朝上收缩,走在街上裙子就会呈现一种倒马鞍形。于是常能看到有些很可爱的妇女走在当街叉开腿站下来,用手抓住裙子的下摆往下拉——那情景实在可怕。所以我建议女同志们在选购时装和化妆品时要多用些心,否则穿得随便一点,不化妆会更好一点。
对于妇女在外貌方面的焦虑情绪,男人的平常心是一副解毒剂。另外,还该提到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她们说:我们干吗要给男人打扮?这话有些道理,也有点过激。假如修饰自己意味着尊重对方,还是打扮一下好。
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
罗素曾说,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这种概括的魅力在于简单,但未必全面。举例来说,一位象棋国手知道自己的毕生事业只是改变棋子的位置,肯定会感到忧伤;而知识分子听人说自己干的事不过是用墨水和油墨来污损纸张,那就不仅是沮丧,他还会对说这话的人表示反感。我靠写作为生,对这种概括就不大满意:我的文章有人看了喜欢,有人看了愤怒,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但话又说回来,喜欢也罢,愤怒也罢,终归是情绪,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我还可以说,写作的人是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影响直至千秋万代——可惜现在我说不出这种影响是怎样的。好在有种东西见效很快,它的力量又没有人敢于怀疑:知识分子还可以做蛊惑宣传,这可是种厉害东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德国人干了很多坏事,弄得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有个德国将军蒂佩尔斯基这样为自己的民族辩解:德国人民是无罪的,他们受到希特勒、戈培尔之流蛊惑宣传的左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有人给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做了一番统计,发现其中每个字都害死了若干人。德国人在二战中的一切劣迹都要归罪于希特勒在坐监狱时写的那本破书——我有点怀疑这样说是不是很客观,但我毫不怀疑这种说法里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总而言之,人做一件事有三种办法,就以希特勒想干的事为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动手去干,这样他就是个普通的纳粹士兵,为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别人去干,这样他只是个纳粹军官;最后,他可以做蛊惑宣传,把德国人弄得疯不疯、傻不傻的,一齐去干坏事,这样他就是个纳粹思想家了。
说来也怪,自苏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识分子拿自己的正派学问教人,都没人听,偏偏纳粹的异端邪说有人信,这真叫邪了门。罗素、波普这样的大学问家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些成分发表过意见,精彩归精彩,还是说不清它力量何在。事有凑巧,我是在一种蛊惑宣传里长大的(我指的是张春桥、姚文元的蛊惑宣传),对它有点感性知识,也许我的意见能补大学问家的不足……这样的感性知识,读者也是有的。我说得对不对,大家可以评判。
据我所知,蛊惑宣传不是真话——否则它就不叫做蛊惑——但它也不是蓄意编造的假话。编出来的东西是很容易识破的。这种宣传本身半疯不傻,做这种宣传的人则是一副借酒撒疯、假痴不癫的样子。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旧俄国有种疯僧,被狂热的信念左右,信口雌黄,但是人见人怕,他说的话别人也不敢全然不信——就是这种人搞蛊惑宣传能够成功。半疯不傻的话,只有从借酒撒疯的人嘴里说出来才有人信。假如我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仅没人信,老农民还要揍我;非得像江青女士那样,用更年期高亢的啸叫声说出来,或者像姚文元先生那样,带着怪诞的傻笑说出来,才会有人信。要搞蛊惑宣传,必须有种什么东西盖着脸(对醉汉来说,这种东西是酒),所以我说这种人是在借酒撒疯。顺便说一句,这种状态和青年知识分子意气风发的狷狂之态有点分不清楚。虽然夫子曾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但我总觉得那种状态不宜提倡。
其次,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纳粹的千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些德国人爱听;“文革”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说,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当然,这种快感肯定是种虚妄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这道理很简单,要想获得现实的快乐,总要有物质基础,嘴说是说不出来的:哪怕你想找个干净厕所享受排泄的乐趣,还要付两毛钱呢,都找宣传家去要,他肯定拿不出。最简单的做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
最后,蛊惑宣传虽是少数狂热分子的事业,但它能够得逞,却是因为正派人士的宽容。群众被煽动起来之后,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有些还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希望这种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宽容它——纳粹在德国初起时,有不少德国人对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这种非理性的狂潮成了气候,他们后悔也晚了。“文革”初起时,我在学校里,有不少老师还在积极地帮着发动“文革”哩,等皮带敲到自己脑袋上时,他们连后悔都不敢了。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些人喜欢受蛊惑宣传时那种快感;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头,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感;不唯如此,有些人还像瘾君子盼毒品一样,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轮新的蛊惑宣传——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惑宣传。我别无选择。
*载于1996年第22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题为“蛊惑与快感”。
有关天圆地方
现在我经常写点小文章,属杂文或是随笔一类。有人告诉我说,没你这么写杂文的!杂文里应该有点典故,有点考证,有点文化气味。典故我知道一些,考证也会,但就是不肯这么写。年轻时读过莎翁的剧本《捕风捉影》,有一场戏是一个使女和就要出嫁的小姐耍贫嘴,贫到后来有点荤。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小姐死后进天堂,一定是脸朝上!”古往今来的莎学家们引经据典,考了又考,注了又注,文化气氛越来越浓烈,但越注越让人看不懂。只有一家注得简明,说:这是个与性有关的、粗俗不堪的比喻。这就没什么文化味,但照我看来,也就是这家注得对。要是文化氛围和明辨是非不可兼得的话,我宁愿明辨是非,不要文化氛围。但这回我想改改作风,不再耍贫嘴,我也引经据典地说点事情,这样不会得罪人。
罗素先生说,在古代的西方,大概就数古希腊人最为文明,比其他人等聪明得多。但要论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想法就不大对头——他们以为整个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么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这时就闹地震。古埃及的人看法比他们正确,他们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埃及人还算过地球的直径,居然算得十分之准。这种见识上的差异源于他们住的地方不同: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蚁爬上篮球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说地是个球。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上,往四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他们那里还老闹地震,所以就想出了沙盘鲸鱼之说。罗素举这个例子是要说,人们的见识总要受处境的限制,这种限制既不知不觉,又牢不可破——这是一个极好的说明。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天圆地方,人在中间,堂堂正正,这是天经地义。谁要对此有怀疑,必是妖孽之类。这是因为地上全是四四方方的耕地,天上则是圆圆的穹隆盖,睁开眼一看,正是天圆地方。其实这说法有漏洞,随便哪个木匠都能指出来:一个圆,一个方,斗在一起不合榫。要么都圆,要么都方才合理,但我不记得哪个木匠敢跳出来反对天经地义。其实哪有什么天经地义,只有些四四方方的地界,方块好画呀。人自己把它画出来,又把自己陷在里面了。顺便说一句,中国文人老说“三光日月星”,还自以为概括得全面。但随便哪个北方的爱斯基摩人听了都不认为这是什么学问。天上何止有三光?还有一光——北极光!要是倒回几百年去,你和一个少年气盛的文人讲这些道理,他不仅听不进,还要到衙门里去揭发你,说你是个乱党——其实,想要明白些道理,不能觉得什么顺眼就信什么,还要听得进别人说。当然,这道理只对那些想要知道真理的人适用。
*载于1996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