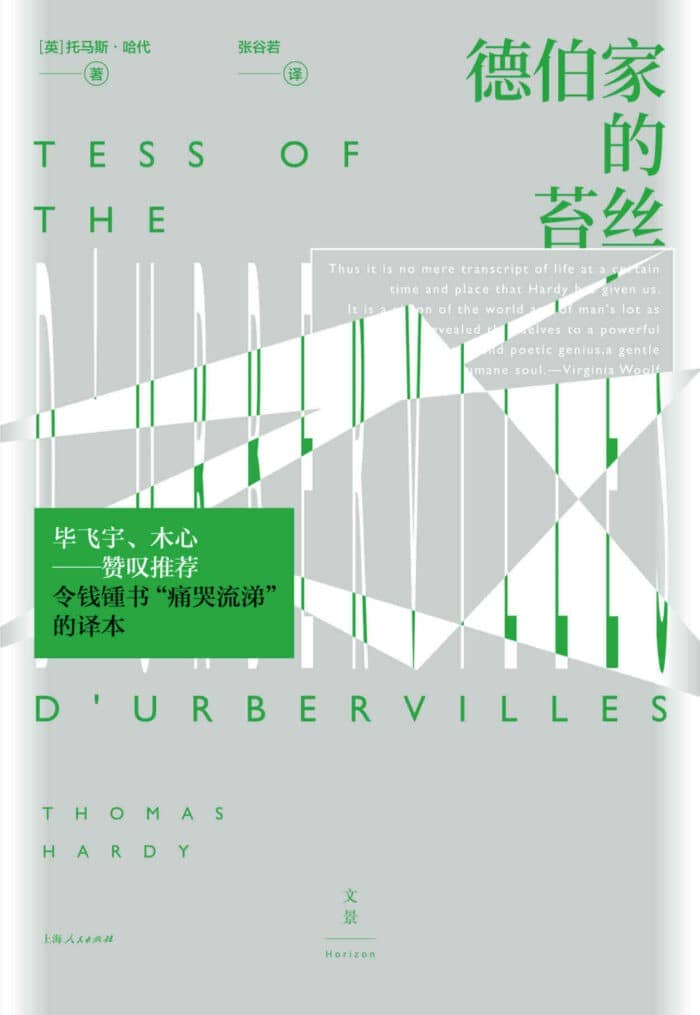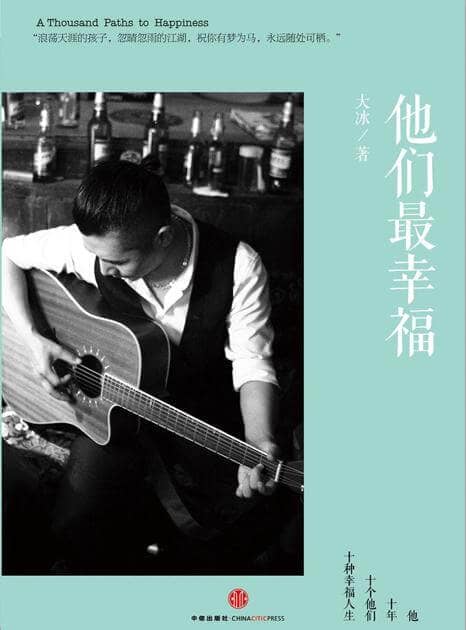内容简介:
《德伯家的苔丝》(1891)是托马斯·哈代所写最后两部重要长篇小说之一,这部作品不仅在作者本国,而且在世界范围,久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为专业研究人士所瞩目,为电影、戏剧界的艺术家们所礼遇,一百多年来早已被公认为哈代最优秀的代表作品,被列入世界文学经典阆苑。读者和评论界大多认为,这部作品最突出的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苔丝这一女性形象。苔丝的父亲是贫苦的乡下小贩,生性怠惰,愚昧无知;母亲过去是挤奶女工,头脑简单,图慕虚荣,他们都是听凭时代风雨恣意摧残的小人物。
苔丝作为这样一个家庭中的长女,接受了当地农村小学最初步的教育之后,从十四五岁就开始在饲养场、牛奶场和农田劳动。这样一位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实际面临的却是环境的愚昧、经济的贫困、暴力的污损、社会的歧视、爱人的遗弃,她面对种种有形无形的势力摧残,经历了对世俗成见的怀疑、否定和抗争,最终仍成为可怜的牺牲。哈代为苔丝设计的人生舞台时限极短,从她在家乡村野舞会上出场,到她在标志死刑的黑旗下丧生,历时不过五六年,但她那短暂一生中的种种遭遇,却足以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作者简介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19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一生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大量中短篇小说和诗集,其小说作品以深邃的悲剧特质、无与伦比的自然描摹功力以及对时代的冷静观照著称,代表作包括《远离尘嚣》(1874)、《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5)等。弗吉尼亚·伍尔夫称他是“英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悲剧作家”,美国文学评论家卡尔·韦伯将之誉为“英国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
译者:张谷若(1903—1994),本名张恩裕,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一生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工作,译有古典文学作品约四百万字。20世纪30年代以成功译介托马斯·哈代的《还乡》一举成名,继而受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翻译委员会”负责人的胡适委托,翻译哈代《德伯家的苔丝》,译本受到钱锺书等大家的一致赞赏。数十年来,张谷若译“哈代三书”以其译文忠实精雅、注释详尽深入而享有盛誉,被公认为外国文学中译的三颗明珠。
试读:
五月后半月里,有一天傍晚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正从沙氏屯,朝着布蕾谷里的马勒村,徒步归去。(布蕾谷也叫布莱谷,和沙氏屯接壤。)他那两条腿,一走起来,老摇晃不稳,他行路的姿势里,又总有一种倾斜的趋向,使他不能一直往前,而或多或少地往左边歪。有的时候,他脆快俏利地把脑袋一点,好像是对什么意见表示赞成似的,其实他的脑子里,并没特意想任何事。他胳膊上挎着一个已经空了的鸡蛋篮子,他头上那顶帽子的绒头,蓬松凌乱,帽檐上摘帽子的时候大拇指接触的那个地方,还磨掉了一块。他往前刚走了不一会儿,就有一个年事垂老的牧师,骑着一匹灰色的骒马,一路信口哼着小调,迎面而来。
“晚安。”挎篮子的行人说。
“约翰爵士,晚安。”牧师说。
那个步行的男子又走了一两步之后,站住了脚,转过身来说:
“先生,对不起。上次赶集的日子,咱们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在这条路上碰见的,那回俺对你说‘晚安’,你也跟刚才一样,回答俺说:‘约翰爵士,晚安。’”
“不错,有的。”牧师说。
“在那一次以前,大概有一个月了,也有过那么一回。”
“也许。”
“俺分明是平平常常的杰克·德北,一个乡下小贩子,你可三番两次,老叫俺‘约翰爵士’[1],到底是什么意思?”
牧师拍马走近了一两步。
“那不过是我一时的高兴就是了。”他说,跟着迟疑了一会儿,又说,“那是因为,不久以前,我正考察各家的谱系,预备编新郡志,那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所以才这么称呼你。我是丝台夫路的崇干牧师兼博古家。德北,你真不知道你就是那名门将种德伯氏的嫡派子孙吗?德伯氏的始祖是那位英名盖世的裴根·德伯爵士,据《纪功寺谱》[2]上说,他是跟着征服者威廉[3]从诺曼底到英国来的。”
“从来没听说过,先生!”
“这是真事。你把下巴仰起一会儿来,我好更仔细端量端量你那个脸的侧面[4]。不错,是德伯家的鼻子和下巴,不过可比先前有些猥琐了。原来帮着诺曼底的爱错玛爵爷征服格拉摩根郡的,有十二位武士,你祖宗就是其中的一位。你们家的支派,在英国这一带地方上,到处都有采邑[5]。在司蒂芬[6]王朝,他们的名字都登在《度支档册》[7]上了。约翰[8]王朝,你的祖宗竟有一位,阔得把一处采邑捐给了僧兵团[9]的。爱德华第二[10]王朝,你祖宗勃伦曾应召到威斯敏斯特[11],去参加在那里开的大议会[12]。奥里佛·克伦威尔[13]时代,你们家多少衰微了一点儿,不过可还没到严重的程度。后来查理第二[14]王朝,你们家因为忠心保主,封过御橡爵士[15]。唉,你们家有过好些代的约翰爵士了;假使爵士也跟从男爵[16]一样,可以世袭,那你现在不就是约翰爵士了吗?古代的时候,爵士实际就是父子相传的啊。”
“真个的吗?”
“总而言之,”牧师态度坚决地拿马鞭子拍着自己的腿,下了断语说,“全英国像你们家这样的,真不大容易找得出第二份来哪。”
“可了不得!全国都找不出来吗?可是你看俺哪,一年到头,忙忙碌碌,东跑西颠,好像跟区里顶平常的家伙,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崇干牧师,关于俺这个新闻,人家已经知道了多久了?”
牧师说,据他所晓得的,这件事早已成了陈迹,很难说有什么人知道了。他自己考察各家谱系,是在刚过去的那个春天里有一天开始的,那时候,他正追溯德伯家历代的盛衰,刚好看见了德北写在车上的姓名,[17]因此他才寻根问底,去考察德北的父亲和祖父,一直考察到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疑问的时候。
“我起初本来打算,不要把这么一个毫无用处的遗闻琐事告诉你,以免搅得你心绪不宁。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的理智控制不了我们的冲动。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一点儿了哪。”
“不错,俺倒也听人说过一两次,说俺们这家人还没搬到布蕾谷的时候,也过过好日子。可是那时候,俺对这种话并没怎么理会,俺还只当是,他们说的好日子,不过是从前养过两匹马,这阵儿可只养得起一匹啦。俺家倒有一把银子古调羹和一方刻着花纹的古印。[18]可是,俺的老天爷,调羹和印算得了什么?……真没想得到,俺会跟高贵的德伯家一直是一家骨肉。人家倒谈过,说俺老爷爷有背人的事,不肯告诉人家,他是从哪儿来的。……牧师,俺莽撞地问一句,俺这家人这阵儿,都在哪儿起炉灶哪?俺这是说,俺们德伯家都住在哪儿哪?”
“现在你们家哪儿也没有了。以一郡的世族而论,你们家已经灭绝了。”
“这可糟糕。”
“不错——这就是那些弄虚作假的家谱上所说的,某家男系绝灭无后,其实不过是衰败了、没落了的意思。”
“那么俺们都埋在哪儿哪?”
“埋在绿山下的王陴。那儿的地下拱顶墓室里,你们家的坟一行一行的,坟上面刻着石像,罩着培白玉华盖。”[19]
“俺们的庄园宅第哪?”
“你们没有庄园宅第了。”
“呃?地也没有了吗?”
“没有了。虽然我才说过,你们家从前有很多庄园,因为你们家的支派很繁盛,但是现在可什么都没有了。从前本郡里,你们家的宅第园囿,王陴有一处,谢屯有一处,米尔滂有一处,勒尔台有一处,井桥也有一处。”
“俺们家还能不能有家道重新兴旺起来那一天哪?”
“啊——这我可说不上来。”
“先生,你看俺对这件事该怎么办才好哪?”德北停了一会儿问。
“哦,没什么办法,没什么办法。‘一世之雄,而今安在。’[20]你只有记住这句话,训诫鞭策自己就是了。这件事本来不过是对于我们研究地方志和家谱的人多少有点儿意思罢了,没有别的。本郡里面现在住小房儿[21]的人家,从前几乎也跟你们家一样声势显赫的,还有好几姓哪。再见吧。”
“可是,崇干牧师,既是这样,那你回来,跟俺去喝它一夸脱啤酒,好不好?清沥店有开了桶的好酒,可是比起露力芬店里的,自然还差点儿。”
“谢谢你,不喝了,今儿晚上不喝了,德北。我瞧你喝得已经不少了。”牧师说完以后,就骑着马走了,心里直疑惑,不知道把这一段稀罕的家史,对他说了,是不是不够慎重。
他去了以后,德北带着一味深思的样子,往前走了几步,跟着在路旁的草坡上坐了下去,把篮子放在面前。待了不久,一个小伙子在远处出现,也朝着德北刚才所走的方向走来。德北见了他,把手举了起来,他于是加紧脚步,走近前来。
“喂,小子,你把这个篮子拿起来,俺要你去给俺送个信儿。”
那位身材细瘦的半大小子,把眉头一皱,说:“约翰·德北,你是什么人,敢支使起俺来,还叫俺‘小子’?咱们谁还不认得谁!”
“真认得吗?真认得吗?这可得说是个谜,这可得说是个谜。你这阵儿听俺吩咐,把俺交给你的差事快快办去好了。……哼,傅赖,俺还是把这个谜对你说穿了吧,俺原是一个贵族人家的后人哪,今儿晌午后,就是刚才那会儿,午时以后,酉时以前,俺才知道的。”德北宣布这段新闻的时候,本来是坐着的,现在却把身子倒了下去,骄矜闲适地仰卧在草坡上面雏菊的中间。
那小伙子站在德北面前,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约翰·德伯爵士——那就是咱!”长身仰卧的男子继续说,“那是说,要是爵士也和从男爵一样的话——本来也就一样呵。俺的来历,都上了历史了。小子,绿山下有个王陴,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俺上那儿赶过绿山会。”
“啊,就在那个城的教堂下面,埋着——”
“那并不是个城,俺说的那个地方并不是个城;至少俺上那儿去的时候,那不是个城。那是个土里巴唧、不起眼的小地方。”
“你就不用管那个地方啦,小子,那不是俺眼下要谈的题目,俺要说的是,俺祖宗就埋在那一区的教堂下面,有好几百位,都穿着真珠连锁甲,装在好些吨重的大个儿铅棺材[22]里头。所有南维塞司这些人,谁家也没有俺们家老祖宗的骨殖那样大的气派,那样高的身份。”
“哦?”
“现在,你拿着这个篮子,上马勒村去走一趟。你到了清沥店的时候,叫他们马上打发一辆单马马车来,接俺回家。再告诉他们,在车底下带一小瓶一纳金[23]重的甜酒来,叫他们记在俺账上好了。你把这些事都办完了,再把篮子送到俺家里,告诉俺太太,叫她把要洗的衣裳先搁一搁,因为她用不着洗完了,叫她等着俺,俺回家有话告诉她哪。”
那小伙子半信半疑,站在一旁,于是德北把手放到口袋里,把他从来一直就没多过的先令,掏出一个来。
“你辛苦一趟,小子,这个给你吧。”
这么一来,那小伙子对当前情势的看法,就立时改变了。
“是,约翰爵士。谢谢你。还有别的事没有,约翰爵士?”
“你告诉俺家里的人,说回头晚饭俺想吃——呃——要是有羊杂碎,就给俺煎羊杂碎;要是没有,就预备血肠得了;要是连血肠也弄不到,呃,那么小肠也行。”
“是,约翰爵士。”
那小伙子拿起篮子,正要拔步前行,忽然听见铜管乐的声音,从村子那边传了过来。
“这是干什么的?”德北说,“不是为俺吧?”
“这是妇女游行会[24]呀,约翰爵士,你瞧,你闺女还是会员哪。”
“真格的——俺净想大事,把那件事全忘了。好吧,你上马勒村,吩咐他们套车来,俺也许坐着车,去视察视察她们的游行队。”
小伙子转身走去,德北在夕阳中的野草和雏菊上仰卧等候。那条路上,许久没再走过一个人影。在这青山环绕的山谷里,那轻渺的铜管乐声,就是唯一能听到的人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