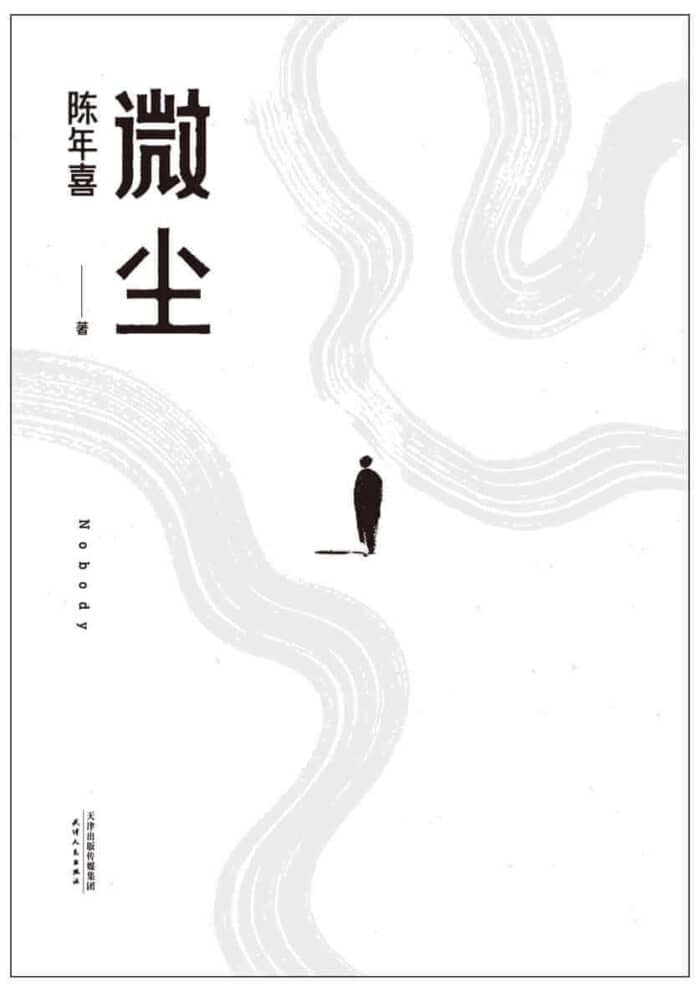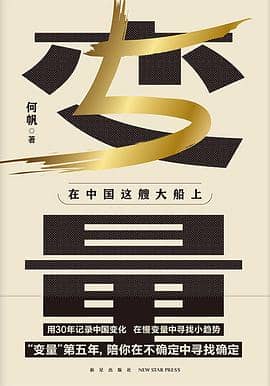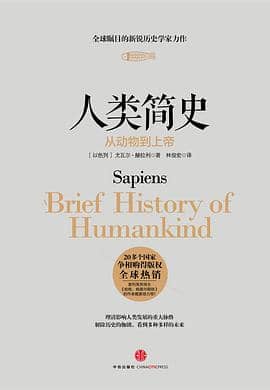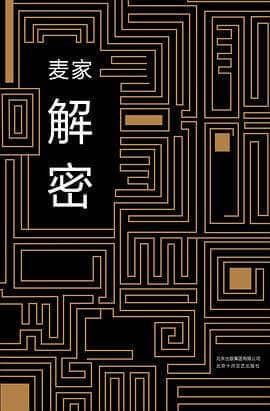作者:
陈年喜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生于1970年;
1990年,开始写诗;
1999年,外出打工,从事矿山爆破工作16年;
2015年,因颈椎手术另谋生路,参与四川卫视节目《诗歌之王》创作录制;
2016年,应邀到哈佛大学等名校诗歌交流,同年获第一届桂冠工人诗歌奖;
2017年,主演纪录片《我的诗篇》上映;
201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炸裂志》;
2020年,受邀做客央视节目《朗读者》。
陈年喜高中毕业之后便外出打工,爆破工是他至今做过时间最长的职业。
成长在秦岭脚下,从小浸酝于老家的秦腔、鼓书等传统文化,陈年喜将其视为自己的文学启蒙。
在矿山工作期间,陈年喜开始不间断写作,他灵感如泉涌,在炸药箱上、在岩石上、在床铺上,他笔下的诗篇和故事如泉水般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
2015年离开矿山后,陈年喜在贵州、北京等地辗转。
2020年,陈年喜确诊尘肺病。现在,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仍在继续写作。
部分媒体的报道:
铁骨深情的爆破工陈年喜在深山矿洞中抒发着“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人民日报》
陈年喜成了一座富矿,那些走南闯北掏空了的山脊,如同一个人被开采的一生。
——《南方周末》
工作时抱着风钻,思想却飘到很远,一些句子浮现出来,赶紧用笔记下。宿舍的床垫用的是废弃的炸药箱,床头放着笔,离开时卷起铺盖,密密麻麻,写了满床。
——GQ报道
兄弟,我读过了你的诗歌,听见了你的饿,因为我曾也在兰州候车,在车上挨饿。
——易中天
他就是我心目中好的写作者,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他的职业,尽管我很尊重工人或农民出身的写作者,但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文字和文学品质本身。”
——张莉 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内容简介:
我见过的不幸太多了,从来没有沮丧过。
——陈年喜
这本书收录了陈年喜21篇非虚构故事集。
书中写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的故事。
他们是爆破工、运石工、乡村木匠、农夫、农妇、小作坊老板……
而作家自己的故事,贯穿始终:在地下五千米开山炸石,在烟尘和轰鸣中养家糊口,在工棚和山野中写下诗篇,记录命运的爆裂和寂静。
他们虽历经生活的磨砺,却淳朴而硬扎,沉静地诉说关于亲情、爱情、死亡、欲望的生活主题……
这是一本生命的书,也是死亡的书,归根到底,是一本生活的书。
世界是什么样子?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的感觉里,除了绵长、无处不在的风,其余都是尘埃,我们在其中奔突,努力站稳,但更多的时候是东倒西歪,身不由己。
试读:
“我见过的不幸太多了,从来没有沮丧过。”做过十六年矿山爆破工的陈年喜,在书中写道。这一行业的劳动者,走遍荒山野岭,在烟尘和轰鸣中谋生。虽然工作艰苦而危险,但他们并不畏惧,以勇于战胜困难的精神,去憧憬、追求幸福的生活。
陈年喜以凝练的笔触,书写普通工人的亲情、爱情、友情,读来感动、感慨、感怀。他的语言非常节制,隐忍的风趣、含泪的幽默,让人回味沉思。他的叙述也很有特点,动用了小说写作手法,有“小说体散文”的明显特征。很少的字、句,却能把复杂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晰,不动声色地打破了散文写作的边界。
最令人赞叹的是,陈年喜摒弃了散文文体一贯存在的自我抒情,把“我”非常巧妙地“隐藏”起来,专注于在“说事”基础上说“人”。每篇文章都给读者以“出其不意”的感觉。讲述一件事情,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伴有历史感、岁月感和知识性,并且非常自然地糅进文章中,融为一体,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其中《一个人的炸药史》尤显水准,语言、叙述、描写俱佳。
同时,书中“人物素描”的文章,也令人印象深刻。《我的朋友周大明》,把人写“活”了,而且语言颇为老到,读起来引人入胜,颇有汪曾祺文字的滋味;文末写死亡,写得忧伤、感人,但又不颓废,让人欲哭无泪。
散文集《微尘》的每一篇文章,都犹如陈年喜在矿山巷道中爆破下的一块块岩石,外表粗粝斑驳,却又饱含温度,令人掩卷沉思。
武歆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自序
二〇一五年四月,在西安交大一附院,我接受了一场攸关生死的手术,在颈椎的第四、五、六节处植入了一块金属固件。至此,我不得不离开矿山,与十六年生死飘摇的爆破生活告别。
两年后,经人介绍,我到了贵州一家旅游企业做文案工作。同样是打工,性质与心境却有了种种不同,不同之一,就是一颗终日紧绷的心终于松懈了下来,像一只一直高速转动的陀螺,头上突然没有了呼啸的鞭影。更深层的是,中年日暮,身心俱疲,人生至此似乎再无多余念想。
然而,往事并不如烟,在异乡孤独的晨昏,在生活转动的一个又一个间隙,我总是常常回望那些或平淡或惊心动魄的过去,回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风雨、朋友与亲人。那些烟云般的往事,那些烟云里升腾跌宕的人影,在我醒来与睡去的光影里交织、缠绕,无论我怎样努力去忘却,它们都已深深镶嵌于我生命当中。有一天,我突然想,我该用笔去记录下它们。
大半生的漂泊与动荡,山南漠北,地下地上,一个人独对荒野与夕阳,我早成失语之人。然而,没有哪次写作可以像写下书中的这些文字这般欢畅,不需构思,不需琢磨,它们像爆破发生时飞散起来的石头和声波,碰撞飞舞,铺天盖地,完全将我湮没了。世事风尘,当这些尘埃再次升腾弥漫开来时,它已改变了当初的色谱与成分。记忆具有变异性、欺骗性,我需要努力地去把握,去最大程度地识辨和还原,与细节争辩,与时间对峙,如临深渊。这些文字间,少有喧声与跌宕,少有悲喜与歌哭,只有硝烟散去后的沉默、飘荡、无迹。同时,它也打开了另一条通道、另一扇门,有形的、无形的。
世界是什么样子?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的感觉里,除了绵长、无处不在的风,其余都是尘埃,我们在其中奔突,努力站稳,但更多的时候是东倒西歪,身不由己。祖先是,我们是,子孙们也将是。这些文字里,我努力记录下了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一本生命的书,也是死亡的书,归根到底,是一本生活的书。世界永远存在A面与B面,尘埃飘荡,有时落在这面,有时落在那面。
两年后的今天,开始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六月,骄阳与雨水在天,峡河在窗外的山脚下静静西流。世上之物,唯有流水是最真实的,它的渺小与盛大,一泻千里与涓涓无形,信马由缰与身不由己,它的黑夜与白昼,来路与去处,不能伪饰。
生命是另一条水流,欣与悲,真与伪,困顿与得意,跌宕与奔流,对事物的追赶与赋形,也是真实的,有河床和风物做证。
在那场重要的手术中,有一个情节让我永生难忘,在手术前一天,拥挤的医生办公室里,主治医生把一沓协议摆到我面前。它雪白、冰冷、威严,有三十多个空项。大部分内容医生早已交代,我也早有思量,但在选择材料一栏,我踌躇了又踌躇,国产件一万一千元,进口件三万八千元。这是一款用于固定椎体的小小金属件,它们的价格竟相去天壤,而且协议标示,进口件不在新农合报销范围。
没有人知道,我那一刻的犹豫是对未来生活无力无知的犹豫。对于弱小者来说,生活下去的无望,比死亡更让人恐惧。
医生说:“能用进口的就选择进口的吧,你还年轻。有身体就还有机会。”
爱人说:“用最放心的,开了大半辈子矿,也就这么一点点用到自己身上。”
那一刻我突然无限感慨:说不定它们是经过我或我的同行的爆破,走出地下世界的某块矿石,被运送到遥远彼岸,经过冶炼、加工,变成医疗用品,再渡重洋,带着资本的属性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它们无言,但我们早已认识。它们以这样的方式,作为对一个爆破者的回报。这是一个多么戏剧性的轮回啊!
写作与整理中,我常想,回到笔下的这些文字,就是另一块轮回的金属部件吧,我能做的是拒绝它金属本质之外的成分。
于我,这些文字,是时间风尘的证词,是对消失的、存在的事物的祭奠,是对卑微之物的重新打量。逝水流远,长忆当歌,献予逝者与生者,献予消失的、到来的无尽命运和岁月。
又一个年景即将走到尽头,生命的枝叶从身上纷落,如南山的秋景,少年成人,长者衰老。某天早晨醒来,想起一句话:“老兵不死,只有慢慢凋零。”突然泪目。是啊!文学不死,让所有人在命运里相遇。
这一年,许多人、许多事都发生了深切的变化,我们家也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从高山搬进城里,开启新的生活。
时间的意义布满生命和地理,它寒冷又温暖。我携文字来过了,并将继续前行。
山河表里潼关路,有字为证。
陈年喜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