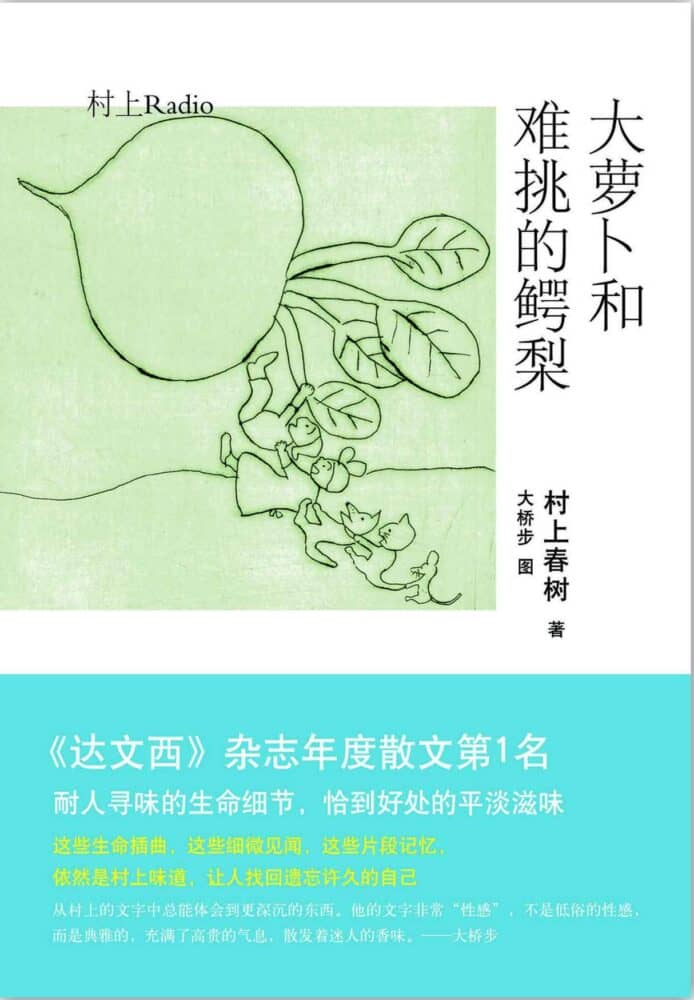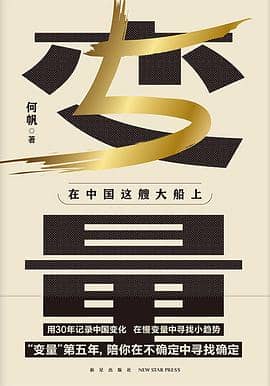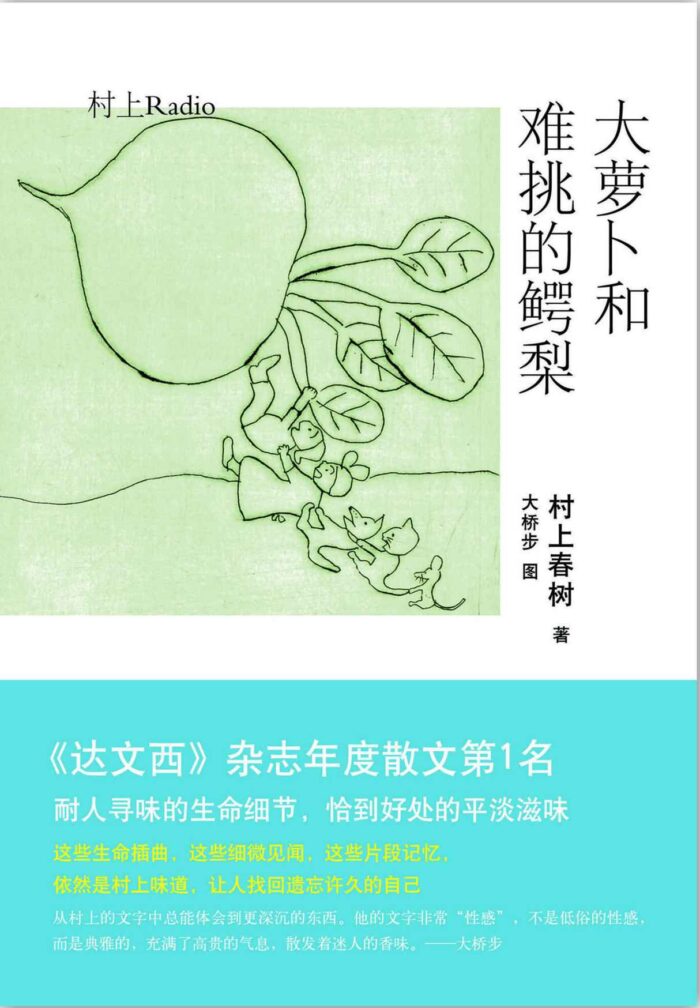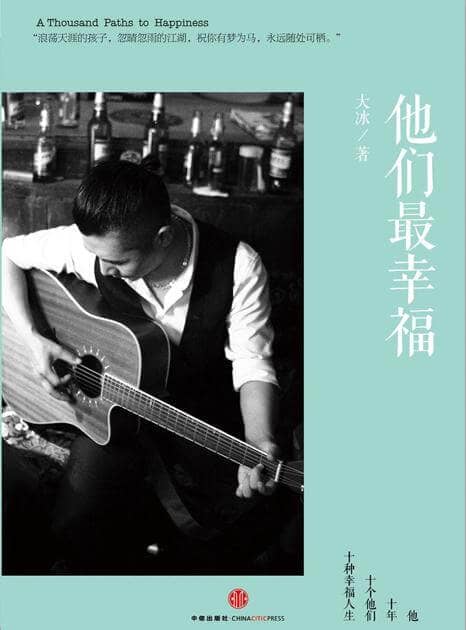作者:
[日]村上春树
1949年生于日本京都。凭处女作《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由此出道。后续著作不断,涵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纪实文学、随笔等多个类型。其中有闻名世界的《挪威的森林》、深度纪实的《地下》、被誉为“新千年日本文学的里程碑”的《1Q84》、谈及战争反思的《刺杀骑士团长》等。
作品以简明的文风与丰富的可解读性为特征,曾获得谷崎润一郎奖、每日出版文化奖、卡夫卡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等世界范围内的诸多奖项。
烨伊
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日语系。曾留学日本,并在当地孔子学院教授中文课程。现从事出版行业。凭着一点点执念走了一段不太短的路,没承想执念竟慢慢成了信念。
译著有《人间失格》《起风了》《银汤匙》《我和小鸟和铃铛》《原来我们都没长大》等。
Alichia
1998年生,2019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主要以怀旧和追忆的感情为表现的主题进行插画创作;经常从自然风景、文学作品、民艺、绘本中得到创作的灵感。
推荐语:
【阎连科】
村上春树的《弃猫》,以平实的笔墨写了父亲波澜起伏而又深水静湖的生命,在娓娓的文字背后,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和不言。这本小书真正对应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八分之一的可见在海面,八分之七的不见在海下。与其说《弃猫 当我谈起父亲时》写的是父亲,倒不如说是写了儿子与父亲遥远的距离。这种父与子的距离和距离的空白,才是村上不言的书写。
〇
【止庵】
在我读过的村上春树的作品中,这是最沉重的一篇,虽然篇幅无多。历史的分量,现实的分量,记忆的分量,作为个体活着的分量,都是弥足珍贵、值得书写的东西。
〇
【史航】
原来村上此生也有绕不过去的一段路。他在这条真相之路上一步一步虔敬从容地走着,比他跑步时的身影还动人。
〇
【李敬泽】
没有人知道一只被遗弃的猫是如何回来的。它在家里,但它自闭在它自己的内部,伤口愈合,但它长在了伤口中。
村上春树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父亲比为那只弃猫。《弃猫》只是一篇散文,但对村上来说,它就是一部书,关于他的生命之根本的书。
村上一直遥望着父亲,这个人是否杀过人?他经历了什么?
在这样的遥望中,村上形成了他对世界的态度,他的所有小说原来是从这里出发的,他无法信任、无法理解他的世界,他和父亲的联系在于,他也成为了那只自卡夫卡的海边归来的弃猫,永远在而不在,永远在自己的内部流浪。
这个小说家,他一直讲的就是弃猫的故事。他酷爱跑步,这或许也是下意识的身体反应,一个弃猫的奔逃。
〇
【祝羽捷】
回忆从“弃猫”开始,“弃猫”像一种隐喻,无论多么不愿意面对冷峻的现实,残酷的真相总会像猫一样找到回家的路,袭上人的心头,存在于意识内部。这本书简短有力,以儿子追寻已故父亲的经历为线索,从含情脉脉的亲情中揭开了战争的残酷,反思个体和集体之间的矛盾,喟叹历史和人类命运的偶然性。父亲吟诵的俳句,是平凡人生命中的浪漫,驱赶了生命的虚无感,是人性里不愿屈服的温暖。
〇
【荞麦】
从历史的洪流和死亡的缝隙中召唤出父亲。是年老后的村上对自己最遥远的回眺,对生之虚空的叹息。
〇
【蒋方舟】
有句话说“一个人衰老的标志就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在这部作品中,村上春树遁入了他父亲的身体里,以父亲的目光去看,以父亲的灵魂去经历,其中的伤感因为父子二人共享同样的记忆而加倍浓重。
试读:
有关我对父亲的记忆。
我对父亲的记忆自然有许多。毕竟自出生以来,直到十八岁离家,我一直与他以父子的关系,在不算宽敞的家中,在一个屋檐底下,天经地义
地共度了每一天。我和父亲之间——恐怕就像世上大多数父子一样——既有开心的往事,也有不那么愉快的回忆。但不知道为什么,如今仍不时
在我脑海中苏醒的、历历在目的影像,却不属于以上任意一种,只是极为寻常的日常生活的片段。
比如有过这样的事。
住在夙川(兵库县西宫市)的时候,我们曾到海边扔一只猫。不是幼猫,而是一只已经长大的母猫。为何要把只这么大的猫扔掉,我已经
不太记得了。当时住的房子是一座带院子的独栋,有足够的空间养猫。可能是这只流浪猫来我家后肚子渐渐大了,父母担心日后照顾不了它生的小箧,但具体的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总之和现在相比,遗弃一只猫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不至于因此被人指指点点。毕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谁会特意给一只猫绝育。当时我大概还在上小学低年级,可能是昭和三十年代1的头几年吧。家附近还留有战争中遭美军轰炸的银行建筑,已经是断壁残[1]昭和是日本裕仁天皇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时间为1926年12月25日至1989年1月7日。昭和三十年代,即1955年至1965年。垣了。那是战争的伤痕还未消失的年代。
总而言之,父亲和我在某个夏日的午后,去海边遗弃那只母猫。父亲踩着自行车,我坐在后面,抱着装猫的箱子。我们沿着夙川走到香栌园的海滩,将箱子放在防风林里,头也不回地匆忙回了家。我家离海滩大概两公里。那时还没开始填海,香栌园海滩还是热闹的海水浴场。那里的海水很干净,放暑假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和朋友一起去那里游泳。那时候的孩子随随便便就去海里游泳,家长基本都不会管。因此我自然越来越能游.想游多久就游多久。夙川里鱼很多,我还在河口捞到过一条大上鱼。
总之,父亲和我将猫放在香栌园海滩,说了句“再见”,便骑车回家。下了车,我想着“怪可怜的,但也没办法”,“哗啦”一声拉开玄关的门。没承想,明明刚扔掉的猫“瞄”地叫着,竖起尾巴亲切地来迎接我们了。原来它抢在我们前头,早就到了家。它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回来,我实在想不明白,毕竞我们是骑车直接回家的。父亲也无法理解。以至于一时之间,我们都无言以对。
我还记得父亲那时―脸的惊讶。但他神情中的惊讶不久就转为叹服,最后好像还松了口气。于是,那之后家里还是将那只猫养了下去,带着一种无奈——做到那个地步它还是找回家来,也就只好养下去吧。
我家里一直有猫。在我看来,我们一家和猫儿们关系融洽,过得不错。这些猫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没有兄弟姐妹,猫和书就是我最珍贵的伙伴。我最喜欢在檐廊上(那个时代,人们的房子大多都带檐廊)和猫一起晒太阳。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去海边将那只猫扔掉呢?为什么当年的我没有反对呢?直到今天,这些疑问—连同猫为什么先我们一步到家——仍然是我难解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