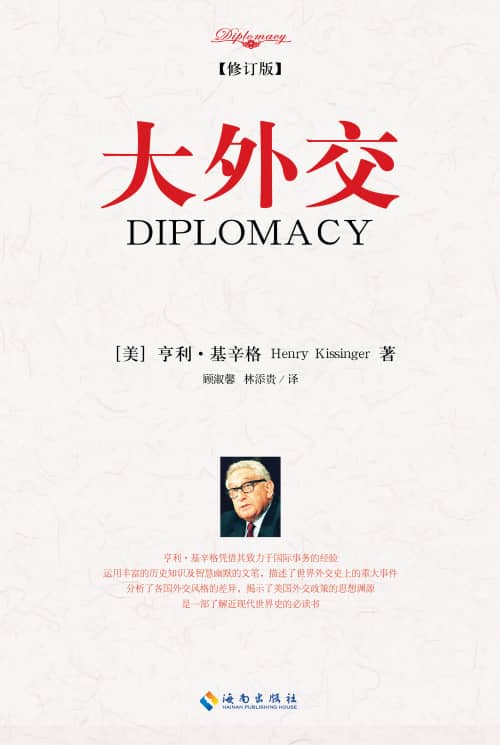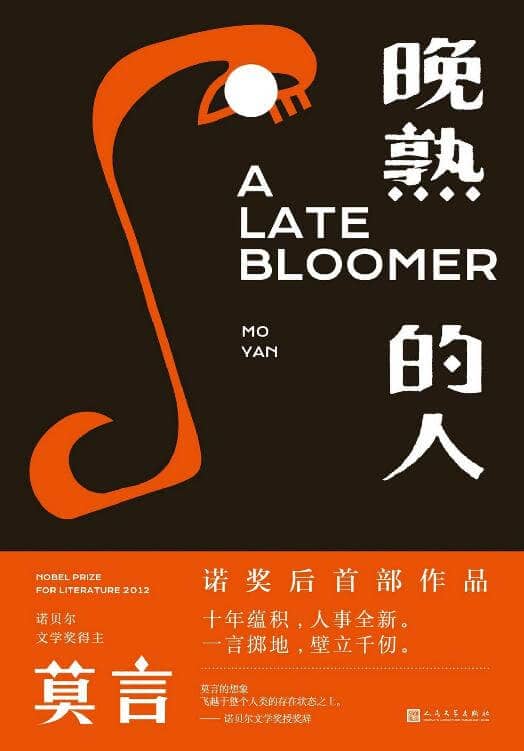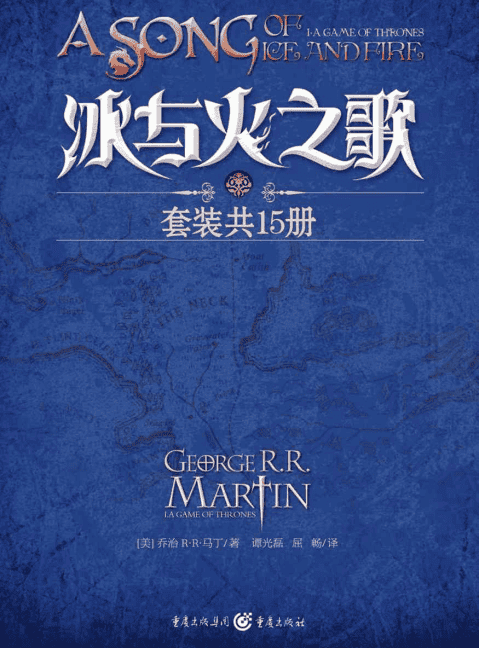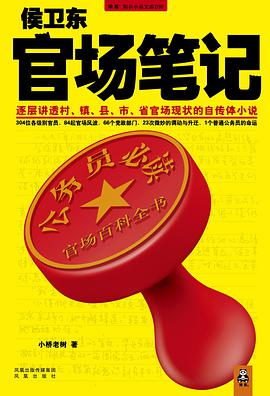内容简介:
纵观近三百年的历史,从现代国家制度之父红衣主教黎塞留,到罗斯福、斯大林;从德国的统一、德国的两次战败,到战后冷战的开始与结束;这本由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的《大外交(修订版)》旁征博引地论述了权利的均衡与外交的艺术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格局。
亨利·基辛格凭借其致力于国际事务的经验,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及智慧幽默的文笔,描述了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渊源。《大外交(修订版)》是一部了解近现代世界史的必读之作。
作者简介:
亨利·基辛格(英文: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犹太人、哈佛大学博士、教授,与越南人黎德寿一同为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后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之后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一位现实政治的支持者,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倡导缓和政策,使美苏之间紧张的关系得到缓解,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并在1972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会谈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促成了中国的开放和新的战略性的反苏中美联盟的形成。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006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基辛格名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论中国》、《大外交》、《基辛格越战回忆录》、《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白宫岁月》《复兴年代》等。
林添贵,国立台湾大学毕业,历任企业高级主管及新闻媒体资深编辑人,目前担任《自由时报》副总编辑,译作极丰,有《买通白宫》、《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密》、《季辛吉大外交》(合译)、《大棋盘》、《新皇朝》等,现客居美国,主持天林媒体投资集团。
顾淑馨
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硕士,从事翻译20年,译作数十册。近年主要作品有《竞争大未来》《与成功有约》《反挫》等。
试读:
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
最能左右国际关系,作风也最矛盾的国家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17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 Richelieu)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18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 balance of power)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19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
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不愿意介人海外事务,即使美国在海外的结盟与承诺均达到空前的范围与规模,这个立场仍不改变。
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民做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虽然自二次大战结束信守承诺之间摇摆。
认为美国只要做楷模及认为美国应主动出击的这两派学说都把以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但由于这种状态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此种高调在他国人听来,即使不被视为太天真,也难免让人觉得不切实际。然而,外国人的怀疑眼光从未浇熄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小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理想主义,其实也包括20世纪所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内。其结果是促使美国人相信,历史是可以超越的,如果全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方。
这两派的主张均是美国经验的产物。虽然共和国不止美国一家,但其他共和国均非刻意为实现自由的理想而缔造。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民是打着为全民自由与繁荣的旗帜,远走新大陆开天辟地。因此孤立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两个表面上如此相冲突的主张,正反映出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美国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自美国于1917年进人世界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的自我肯定,以至于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协议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呈现,从国际联盟及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 Kellogg Briand Pact)到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苏联的解体似乎证明了美国理想的正确性,却也使美国无从逃避她始终不愿面对的世界局势。在逐渐显现的国际新秩序中,民族主义又卷土重来。各国急于追求本身利益远胜于坚持崇高的原则,而且竞争多过合作。我们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此种历史悠久的行为模式已有改变,或是在未来数十年中会有所变化。
在逐渐显现的世界秩序中不同以往的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美国无法改变自有史以来便深自期许的使命,也不应希望有所改变。美国刚走人国际社会时,正值年轻力壮,也有实力让全世界顺从其对国际关系的理想安排。到1945年二次大战终了时,美国国力之强(全世界的总产值中,美国一度占了35%左右),仿佛注定她要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塑造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