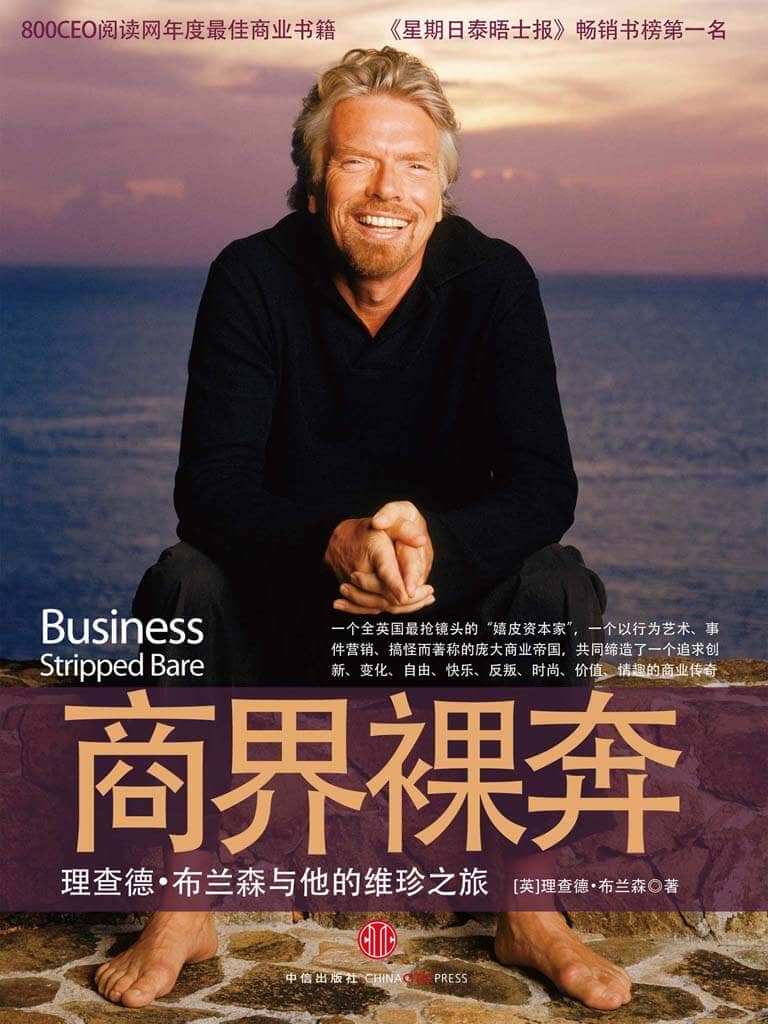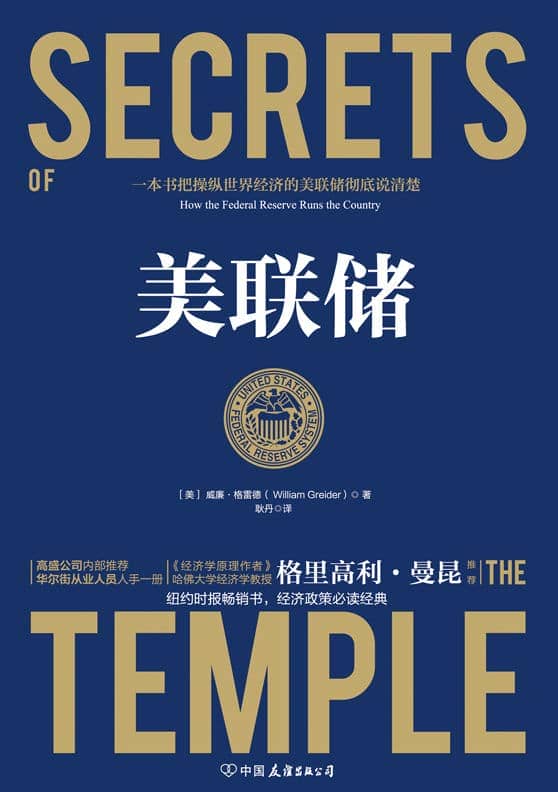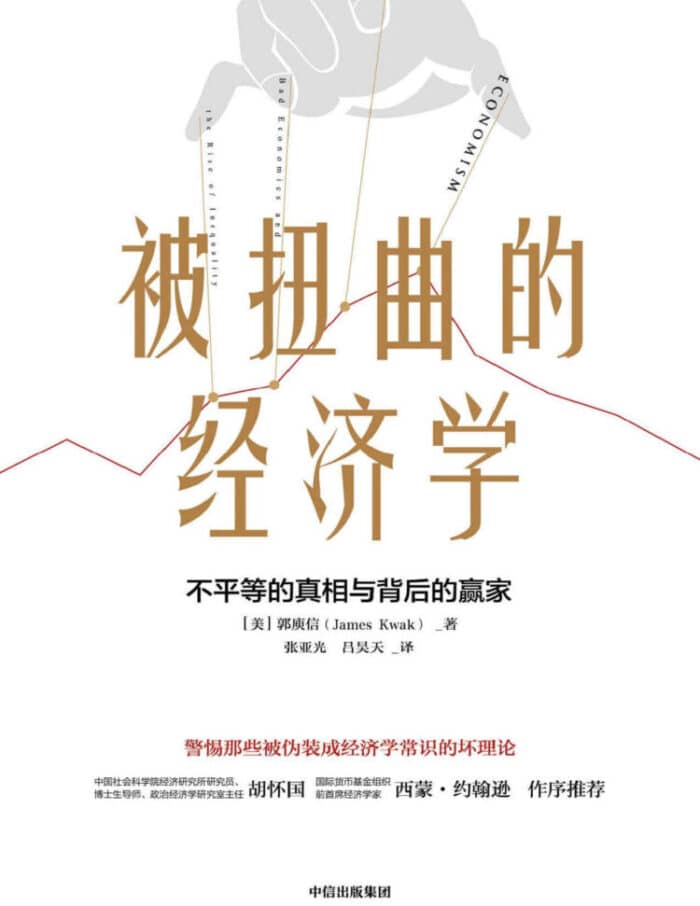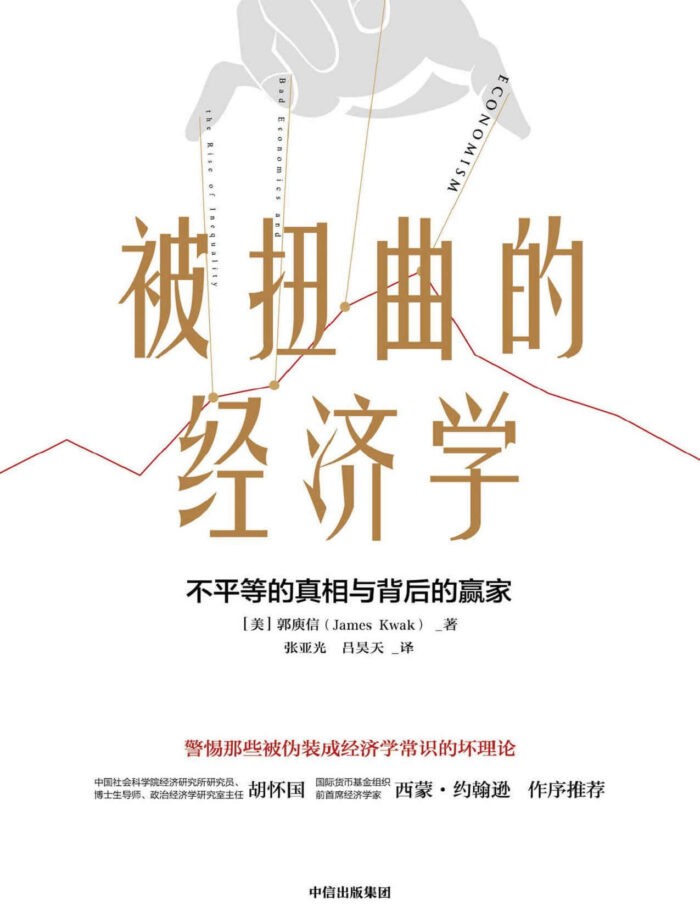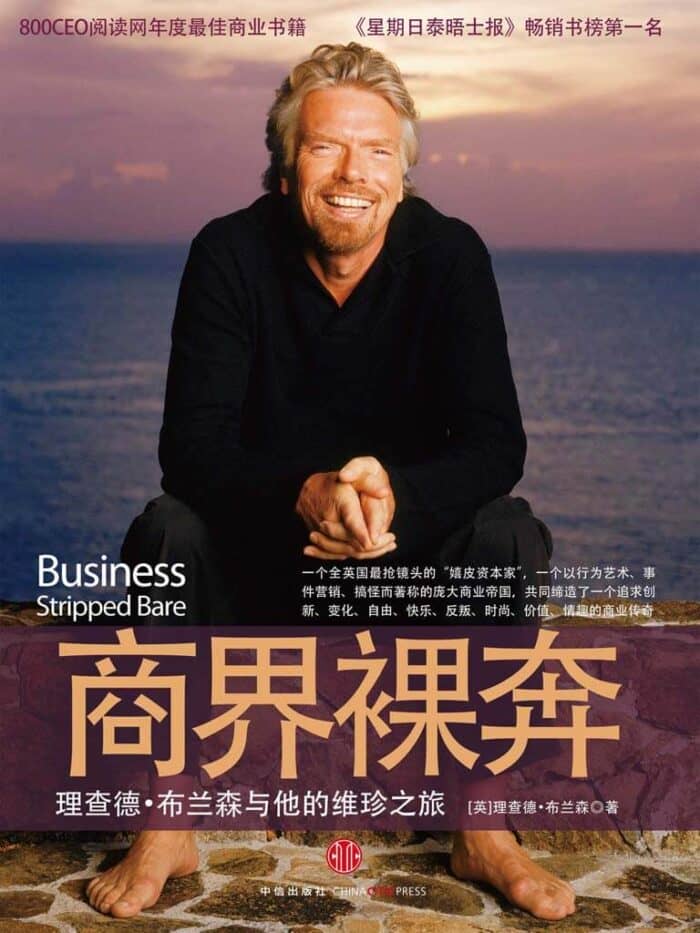内容简介: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作者简介: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主要出版著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等。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试读:
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变革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两极化。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出版的《2050年趋势巨流》(Megachange:The World in 2050)一书中的计算,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的20%。1《经济学人》的数据与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计算2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曾经出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进而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长期结论,在他看来,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把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作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3
对于西方人来说,面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
2013年1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年届103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出版《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在过去几年里,这位当世最高寿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从未踏上过这个陌生国家的土地,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他自己出资在芝加哥召开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之后又倾力完成了这部著作。在这本书里,科斯对中国经济变革给出了三个基本性结论:一是“最伟大”,他认同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点,认为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二是“非计划”,“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他的这三个基本性结论表明,在现有的制度经济学框架中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4
与上述声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见似乎更为尖锐。
2012年初,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准确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广为人知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崩溃。他的主要论据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5%,更多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投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这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前的情况非常类似。他在文章的结尾调侃:“世界经济已经饱受欧洲金融危机之苦,我们真的不需要一个新的危机发源地。”几乎同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也刊载了题为《2012年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中国的体制、法律、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问题会成为即将崩溃的原因。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长期悲观论颇为流行,不少自由派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耶鲁大学的黄亚生教授多次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在他看来,“如果以亚洲各主要工业国经济起飞的不同年份作为出发点来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足为奇。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5
经济学界的两极化分歧不但没有消解中国经济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显得更加迷人。当理论和数据都无法给予清晰判断的时候,我想起了约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于是,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与逻辑,也许是一次不错的探险。——这正是本书创作的起点。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每一个中国男孩,几乎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了解本国历史的。我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邻居家的旧书架上捞到一本泛黄毛边、繁体字版的《三国演义》。展卷阅读,罗贯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11岁的我给镇住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直到30多年后,在书堆里埋头日久的我才突然抬起头来,想找罗先生问几个问题:为什么天下大势必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为什么合了就必定会再分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
这些当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学术问题,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甚至将最后一个问题看作西方历史与东方历史的“区别点”。
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了城邦制,东方的春秋战国正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传授几何学;孟子出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是一位12岁的翩翩少年。公元前360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356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汉武帝(前156—前81年)进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时,西方的凯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公元184年,汉帝国陷入内乱,之后进入了将近四百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帝国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开始了“大分流”。中国在公元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而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时期,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2000年出现了欧元,实现了货币意义上的“统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欧元的存废又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魏斐德的问题正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
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你尽可以从地理条件、民族心理、宗教语言以及偶然性等角度来给出解释。魏斐德给出的答案很简洁,但在我看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他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6
统一的文化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荣光,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根据他的统计,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个文明社会,其中,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得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尽管统一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甚至连汤因比都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过他确定地认为:“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感激涕零。”7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这个词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别无选择。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长期统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治国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有卓越的智慧,由此,我得出了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四大利益集团格局图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它们分别呈现为——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中央集权与四大基本制度
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集权政体的“大厦”,它们的共性就是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这些制度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8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及至于近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上述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维持大一统、实行威权治理的基本理念无实质性更变,因此,制度创新的目标与手段依然共轨同辙,体现出鲜明的延续特征。对于面向未来的中国变革,此乃最为严峻的命题之一。
本书正是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做一次跨时空的平铺直叙。
在第一讲和第二讲中,我将讲述中国在完成大一统之前的两次重要变法——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管仲的“四民分业”思想、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制上的大胆试验,皆具开创之功,它们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极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
第三讲“汉武帝变法”是一个重点,在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变革中,中国完成了帝国模式的建设,汉武帝倡导“独尊儒术”奠定了全民思想控制的基本模式,他围绕产业、流通、货币及财税等核心经济命题,施行了史上第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其颁布的诸多经济政策为后世所借鉴仿效。第四讲的“王莽变法”,是一位儒生皇帝对汉武帝的极端化模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非常短命的古典社会主义试验。
第五讲和第六讲,分别讲述中华文明史上最繁荣鼎盛的两个朝代——唐朝和宋朝的政治经济变革。唐太宗以史上最小之政府造就最强之帝国,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然而130年后,制度上的缺陷使唐朝难逃“安史之乱”的劫难。宋太祖果断地削夺了地方藩镇的权力,化解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挑战,有宋一朝在经济制度上的创新为历代之最,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次转折性事件,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东西方文明也在此时分道扬镳。
第七讲“明清停滞”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后,中国会掉进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陷阱;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一次胆怯的被动行为,还是自信的主动决策;中国人在经济创新和科技创新上的能力退化是怎么发生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如何形成的。
从第八讲“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以“东亚病夫”的姿态被拽入全球化洪流,重新驶上积极变革的轨道,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输入式改革,其过程痛苦被动,耗尽一代精英的心血。晚清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结局,期间发生的两次“国进民退”事件值得后人警惕。
第九讲“两个民国”提供了两个从理念到模式均南辕北辙的变革样本,一个是极度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运动,另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陷入进退维艰的闭环型矛盾之中。
第十讲、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变革简史,1949年之后的20多年间,进行的是一场意识形态气息浓烈、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试验,它曾经取得过辉煌的经济成就,然而最终将中国拖进了一个停滞混乱的泥潭。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则又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两个阶段,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种种羁绊又让改革的长期前途显得扑朔迷离。
上述十二讲,始于遥远的公元前7世纪,止于当下的2013年,漫长的叙述宛如一次疲倦的旅行,对于写作者和阅读者都是一次智力、体力考验。在闭门创作的日日夜夜里,我常有与古人对弈复盘的感慨,有时一起欢愉,有时一起快意,有时一起沮丧,相与辩驳,东西参详,终于体会到钱穆所谓“对古人怀有温情与敬意”的心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尝言:“关于政治经济、经济发展、经济时代问题,都要理解决策者背后的思想模式和意识形态。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群人对环境的解释,以及对该环境如何调理出秩序,所提出对策背后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在这本书中,我放弃了批判者的姿态,而更希冀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也因此,我在十二讲之后,又增写“回到历史的基本面”一节,就“统一文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同时,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变革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判断。
在这本书中,我将提出两个也许会引起争议的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