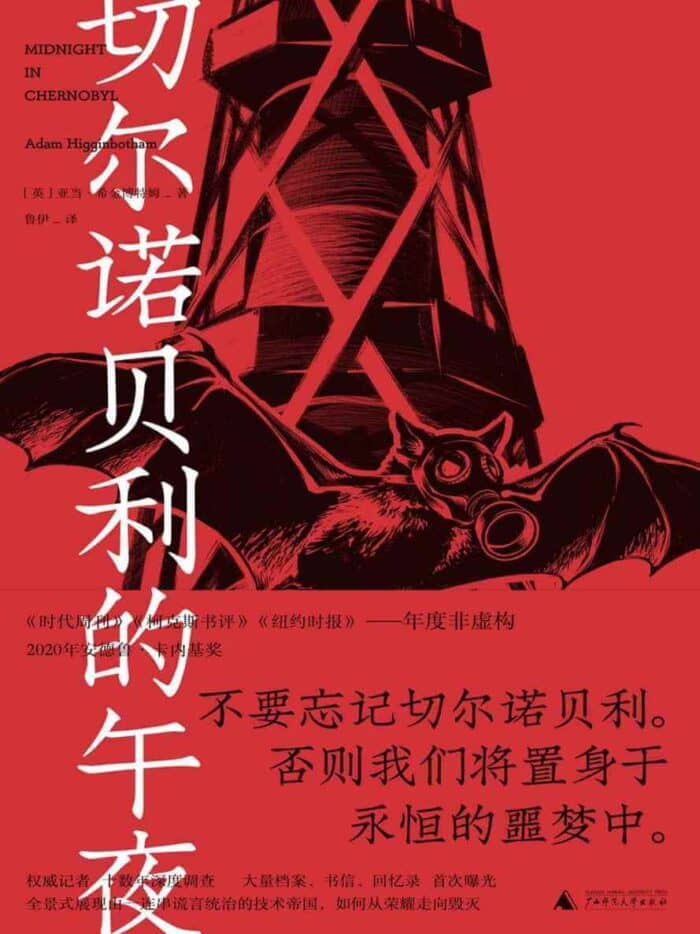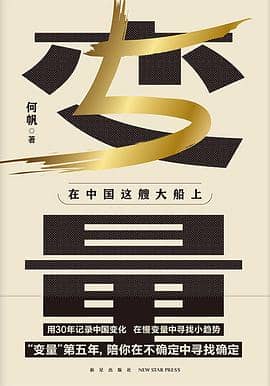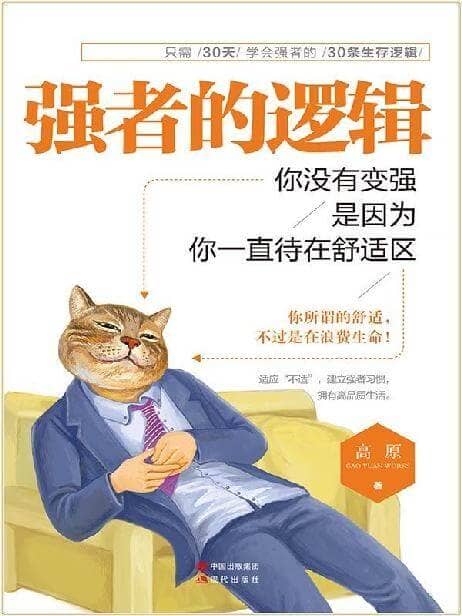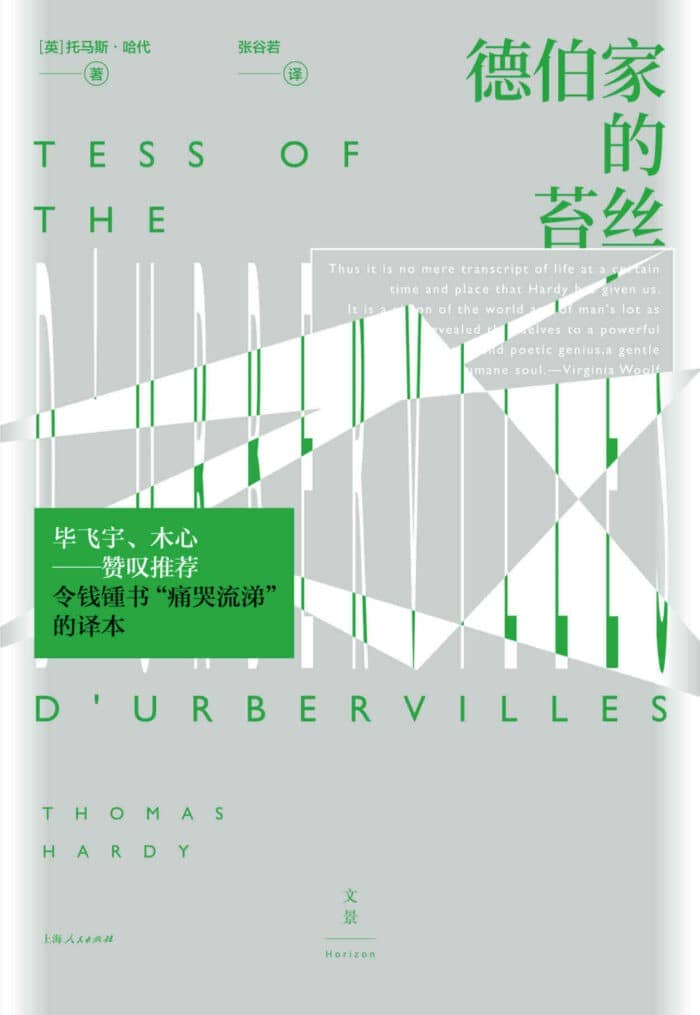作者:
亚当·希金博特姆(Adam Higginbotham)
1968年生于英国,《纽约客》《连线》《史密森尼》和《纽约时报杂志》主笔。
内容简介:
亚当·希金博特姆耗费多年心血,终于完成这部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权威力作。书中充分有力的调查,揭示了这场二十世纪最大灾难之一的真相是如何在政治鼓吹、重重保密和谣言四散的共同作用下被掩盖起来的。
.
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的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由此引发了历史上最恶劣的一起核灾难。自那以后的三十年里,切尔诺贝利逐渐成为整个世界挥之不去的噩梦:阴魂不散的辐射中毒的恐怖威胁,一种危险技术脱缰失控的巨大风险,生态系统的脆弱,以及对其国民和整个世界造成的伤害。然而,这场事故的真相,却从一开始便被掩盖起来,长久以来一直众说纷纭。
.
十多年中,亚当·希金博特姆进行了数百小时的采访,以此为依托,辅之以往来书信、未发表的回忆录和新近解密的档案文件,他将那些灾难亲历者所目睹的一切,化成客观、冷静而又发人深省的叙述。由此得到的,是一本惊心动魄的非虚构杰作,一个比苏联传奇更复杂、更人性,也更恐怖的故事。
试读:
引子
1986年4月26日,星期六,下午4点16分
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乌克兰1
亚历山大·洛加乔夫上尉爱辐射,就像男人爱他们的老婆。这个高大英俊的26岁男子,一头剃得极短的深色头发,双眸湛蓝如冰。当年参加苏联陆军时,还不过是个大男孩。这些年,军队把他训练得很好。在莫斯科城外的军校里,教官教给他关于致命毒剂和无防护辐射的相关知识。他去过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实验基地,也到过荒无人烟的东乌拉尔放射性追踪区(East Urals Trace)——一场秘密核试验失败后造成的污染,至今仍荼毒着那片土地。作为训练的一部分,他甚至登上过僻处北极圈内的禁地新地岛(Novaya Zemlya)。历史上威力最大的热核武器“沙皇炸弹”(Tsar Bomba),就是在那里试爆的。
如今,作为基辅地区民防部队第427红旗机械化团的辐射侦察指挥官,洛加乔夫深知如何保护自己和三名下属免受神经性毒剂、生物武器、γ射线和强放射性粒子的危害:照着教科书上的指示按部就班,信赖自己的放射量测定设备,在必要时求助于存放在装甲车驾驶座下的核生化防护包。但他也坚信,最好的保护还是来自心理上的保护。那些对辐射心怀恐惧的人是最危险的。而爱上辐射、接受辐射的广泛存在、理解辐射复杂多变的那些人,则能够在经历最猛烈的γ射线暴击后全身而归,健康如常。
那天早上,一列由三十多辆车组成的车队,快速穿过基辅市郊。春风拂过装甲巡逻车的车窗,带着草木的清香。被召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处理紧急情况的洛加乔夫坐在头车中,感觉一切都尽在掌握。他的手下前晚刚刚在每月例行的检阅仪式上列队走过阅兵场,各个都训练有素。在他脚下,摆着一排放射性物质检测装置,其中一台新装的灵敏性相当于老型号两倍的电子设备,正发出轻柔的杂音,显示周围一切并无异常。2
但他们当日上午晚些时候终于接近核电站时,很明显,一些不同寻常的事确实发生了。穿过标志着核电站外围的混凝土路标时,放射量测定仪第一次发出了警报声。洛加乔夫上尉下令停车,记下了上面的读数:51伦琴每小时。如果他们在那里再等上60分钟,所有人吸收的辐射量,将相当于苏联军队在战争期间允许吸收量的最大值。于是他们沿着从远方的核电站一路延伸而来的高压输电塔继续往前开。放射量测定仪上的读数再度升高,但随即又降了下来。
装甲车轰隆隆地经过核电站冷却水河道的混凝土堤岸,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的轮廓终于出现在眼前。洛加乔夫和他的手下沉默地注视着那里。20层楼高的建筑物,屋顶已经被掀开,整个上半部一片焦黑,分崩离析。落入眼帘的,是七零八碎的钢筋混凝土楼板和石墨砌块,以及从核反应堆堆芯抛射而出的亮闪闪的燃料组件金属封装。一团蒸汽云从废墟上袅袅升起,飘散入万里晴空。
然而,他们受命而来,要对核电站进行全面侦察。于是,装甲车开始以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逆时针绕着电厂综合体缓慢行驶。中士弗拉斯金大声报出新设备上的辐射读数,洛加乔夫随手标记在一张用圆珠笔和彩笔手绘的仿羊皮纸地图上:1伦琴每小时,2伦琴每小时,3伦琴每小时。他们向左转了个弯,读数开始急速上升:10,30,50,100。3
“250伦琴每小时!”中士喊道,双目圆睁。
“上尉同志——”他开口说道,手指向辐射测量仪。
洛加乔夫低头看向数字仪表盘,立时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2080伦琴每小时。一个根本不可能的数字。
洛加乔夫努力保持冷静,努力回忆教科书上的内容,努力克服自己的恐惧。但他接受的所有训练,此刻都跑到了九霄云外。上尉听见自己在恐慌中对着司机高声尖叫,担心装甲车会就此停驶:
“你干嘛往这边走?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的脑子有病吗?”他吼道,“如果这玩意儿不动了,不出一刻钟咱们全都得死翘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