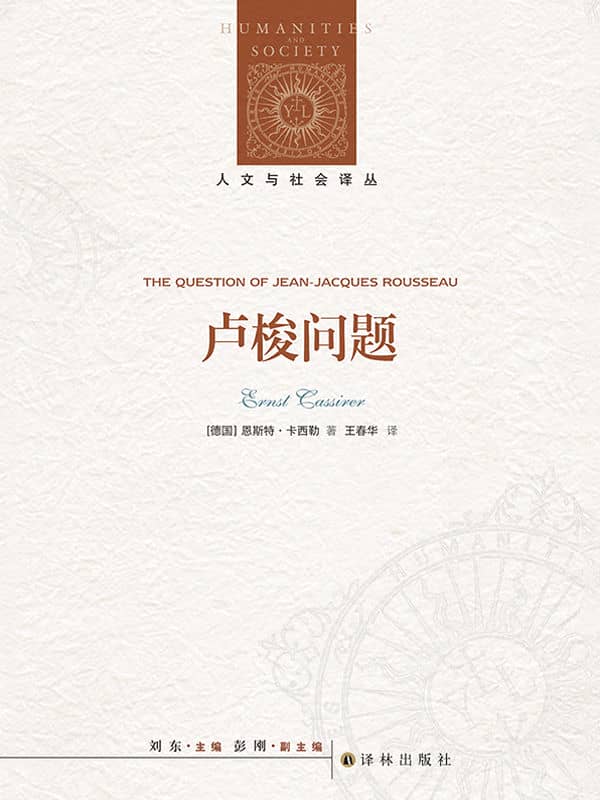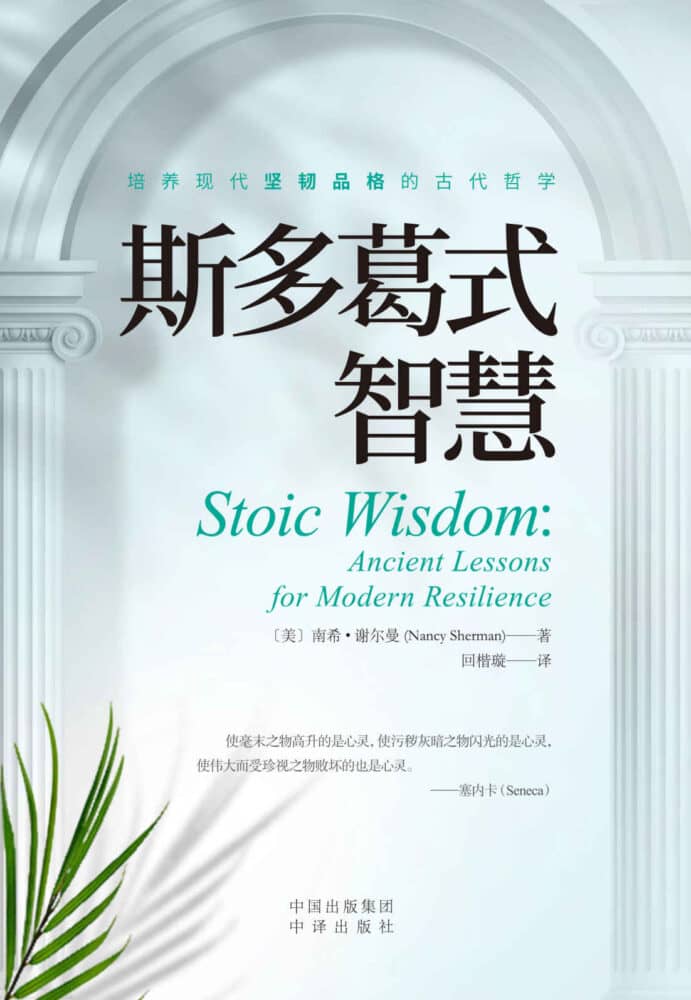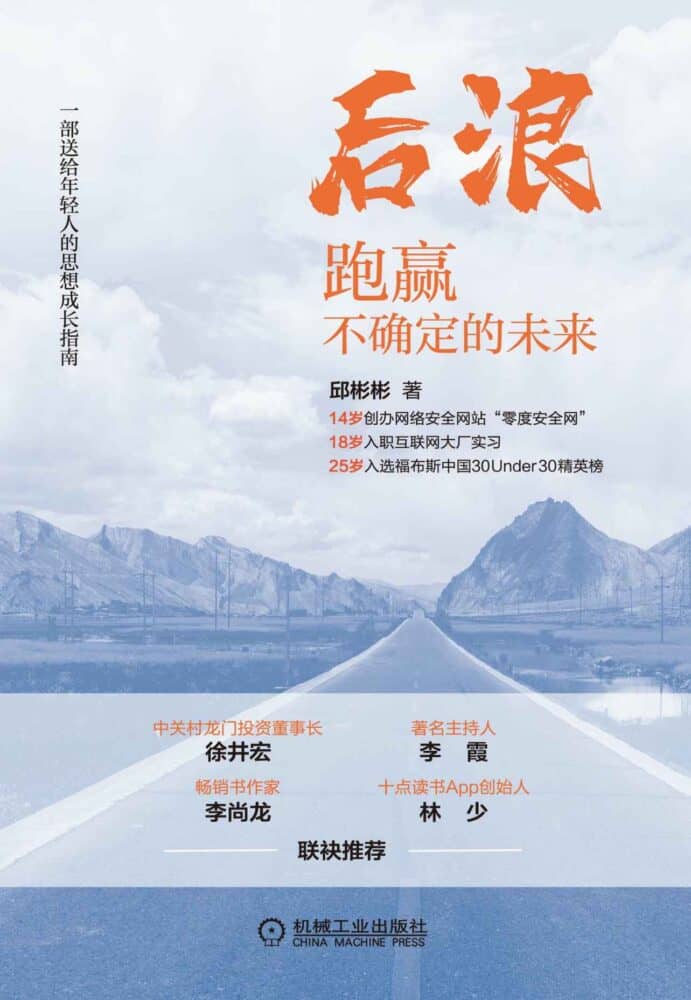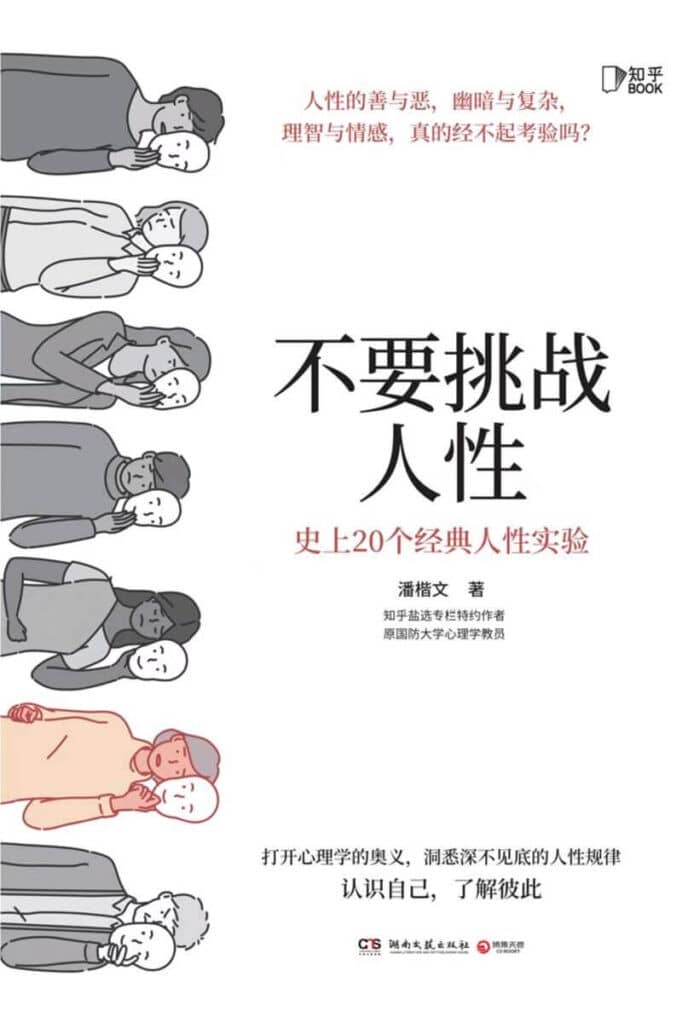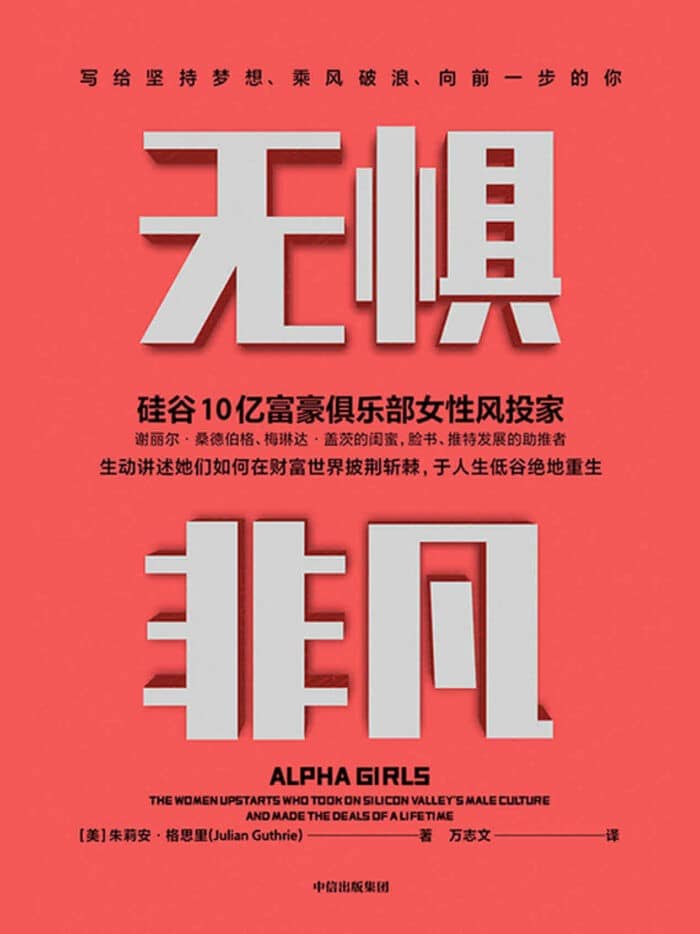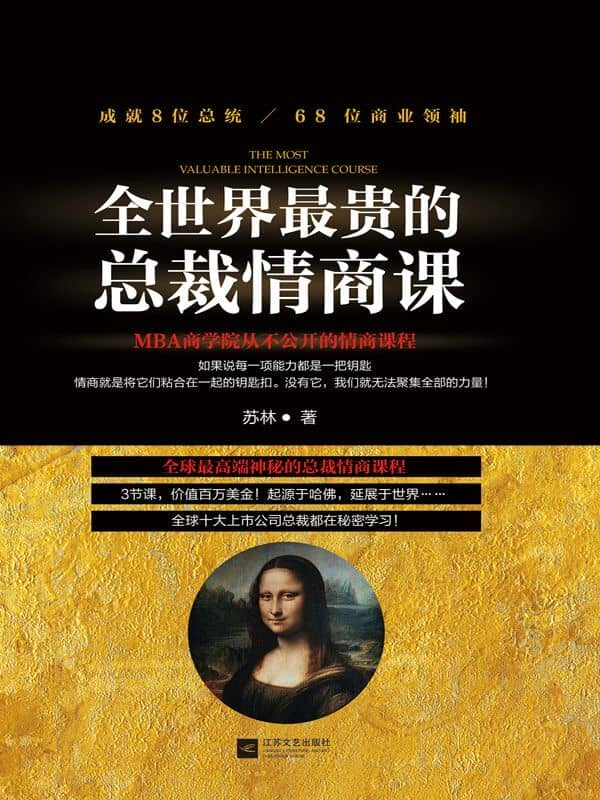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机缘巧合之下,科学家发现了来自外太空的一封中微子信件,也许这正是智慧生物的象征。我们不知道发信人是谁,该如何解读这封信的内容呢?如果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发信人呢?《其主之声》围绕谜团展开的故事,比众多冒险小说都更扣人心弦,尤其与未知的较量,激发了对世界本质、人类本性和生命为何存在缺陷等基本问题的思考。
作者简介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1921—2006),波兰著名作家、哲学家。当过汽车技工,终获医学博士学位,创立波兰宇航协会。代表作有《索拉里斯星》《未来学大会》《惨败》等。作品多聚焦哲学主题,探讨科技对人类的影响、智慧的本质、外星交流,以及人类认知的局限等。1996年被授予波兰国 家奖章“白鹰勋章”,波兰第一颗人造卫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莱姆是20世纪欧洲最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安东尼•伯吉斯称赞他是“当今活跃的作家中最智慧、最博学、最幽默的一位”,库尔特•冯内古特赞扬他“无论是语言的驾驭、想象力还是塑造悲剧角色的手法,都非常优秀,无人能出其右”。被译成52种语言,全球畅销4000余万册。
试读:
尽管下面这番话会让许多读者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我有责任把它们说出来。我从没写过这样的书;而且照惯例,数学家介绍自己的作品时不用附带一篇个性宣言,我本可以省却这麻烦。
由于情势超出控制,我被卷入了一系列事件中,我想在此谈论的正是此事。为什么我要用一种忏悔式的话语开始讲述,稍后便不言自明。谈到我自己时,必须选一个参照系,不妨就选择哈罗德·约维特教授最近为我写的传记吧。约维特称我有“最高水准的头脑”,因为我选择的课题永远是现有全部课题中难度最大的。他在书中写道,我的名字总是出现在旧的科学大厦崩塌、新的概念升起之处——比如数学革命、物理伦理学,以及“其主之声”计划。
阅读那本传记时,我看到某一处的主题是“毁灭”,在提及我有悖传统的偏向之后,我期待他做出更深入、更大胆的论断,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传记作者——这并不令我特别喜悦,因为剖析自我是一回事,被别人剖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约维特像是被他自己的敏锐吓到了,他又生硬地绕回去,将我描述为已被广泛接受的那副样子——一位执着而谦虚的天才,他甚至还抛出了几则关于我的老生常谈的趣闻逸事。
所以,我可以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了,和别人为我写的其他传记放在一起。这么做时我十分平静,还稍稍想象了一下,我很快就会被那些擅长奉承的肖像画家列入待画人物的名单。同时,我还注意到那个书架上已经没有多少剩余空间了。回想起我曾对伊沃尔·巴洛因说过,等这个书架填满,我就该死了。他以为这只是个笑话,我也并未反驳,但是我说这句话时是有些认真的,并非完全随口胡扯。所以,咱们回到约维特的书上,我又一次成功了,或者也可以说我失败了——六十二岁时,已有二十八本图书专门研究我这个人,但依旧无人能理解我一星半点儿。这么说公平吗?
约维特教授在描述我时所依据的规则不是他自创的。并不是所有公众人物都享有同样的待遇。伟大的艺术家们,没错,可能会被冠以偏狭小气之名,有些传记作家甚至似乎认为艺术家的灵魂必然是卑下的。但是,对于伟大的科学家,陈旧的刻板印象依然无可动摇。我们把艺术家看作被肉体拴住的灵魂;文学评论家可以自由地讨论奥斯卡·王尔德等人的同性恋取向,但是你很难想象,有哪个科学史研究者会用类似的方式谈论物理学的那几位奠基人。我们必须认为他们是刚正不阿的,是完美无缺的,而历史中的诸多事件不过是他们人生中的过眼云烟。政客可以是邪恶之徒,这不影响其出色政治家的身份,然而邪恶的天才——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邪恶与天才相互抵消了。今天的规则就是这样。
的确,有一群来自密歇根的精神分析学家试图挑战这种情况,但他们落入了过于简单化的谬误。物理学家们确实热衷于提出各种理论,而那些专家将之归咎于性压抑。精神分析学说旨在揭露每个人心中的那头猪,一头驮着道德心的猪;灾难性的后果是,猪在那位虔诚骑手的压迫下过得很不舒服,而骑手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他的使命不仅是驯服那头猪,还要让它彻底消失不见。这种观念认为我们心中有一头背负着现代理性的古老野兽——这是对各种原始神话的杂烩似的反映。
精神分析学家提供的是一种幼稚的、小学童式的真相,我们浮光掠影地从中学到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被吸引了注意力。有时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比如这里,对真相进行廉价的简化,其价值并不高于一句谎言。又一次地,我们眼前呈现出魔鬼与天使,或是摩尼教里的野兽与神;又一次地,人类宣称自己并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每个人都不过是一块战场,注入其体内、使之膨胀的两股力量在这战场上角逐,在皮肤之下此消彼长。因此,精神分析的主要问题是见识肤浅却自命不凡。它用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向我们解释人类的本质,这一整出关于“存在”的戏剧,其张力只存在于两者之间:兽性,文明之力对兽性的净化。
所以,我真的应该感谢约维特教授,感谢他用经典的方式描绘我,而不是借鉴密歇根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研究方法。不是说我对自己的评价要高于他们对我的评价,而是漫画像与肖像真的有所不同。
也不是说我认为传记的描述对象要比传记作家更了解自己。传记作家们所处的位置更便利一些,因为他们对有些内容拿不准是由于缺乏信息,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只要描述对象还活着并且愿意配合,他就可以为作家提供所需的信息。而描述对象本人,他对自己的了解也无非是一些假设罢了,这些假设作为其思维活动的产物或许具有重要性,却不一定能填补那些信息缺失之处。
只要有充足的想象力,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人生书写成一系列各不相同的版本。这就像是许多集合组成的一个并集,而交集中的唯一元素是那些板上钉钉的事实。年轻人,甚至聪明的年轻人,由于不谙世事缺乏经验,会认为我的这一想法是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他们错了,因为这个问题无关道德,而是关乎认知。世上有多少种不同的哲学观念,一个人就会对自己有多少种不同的认识——这些看法可能是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形成的,有时候甚至在同一时期,人都会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