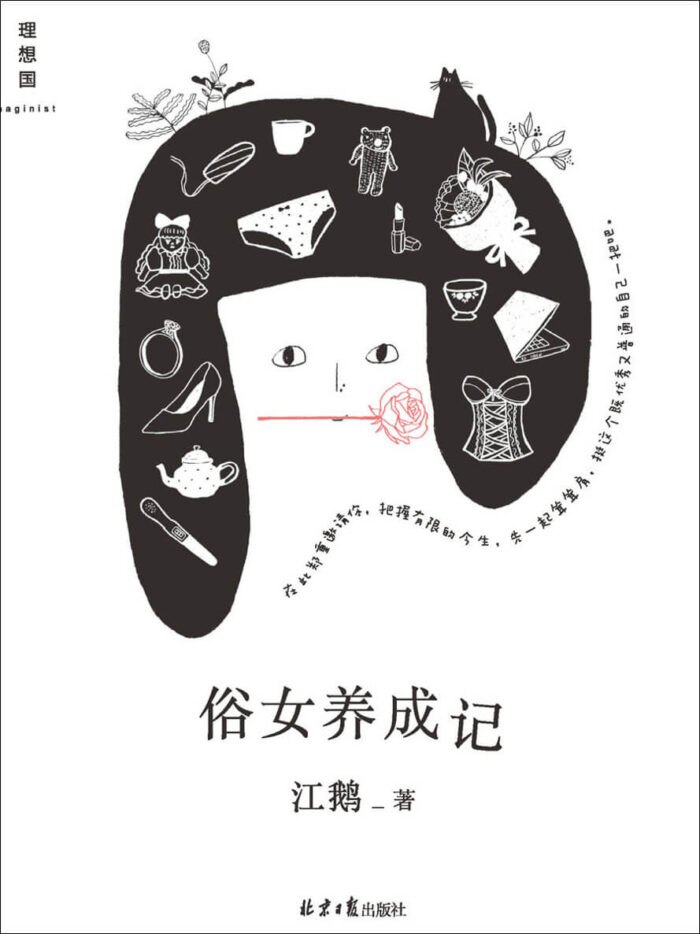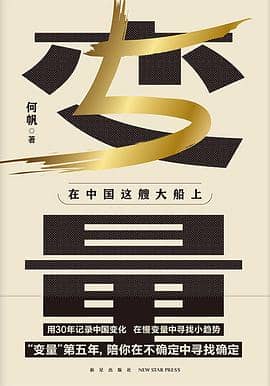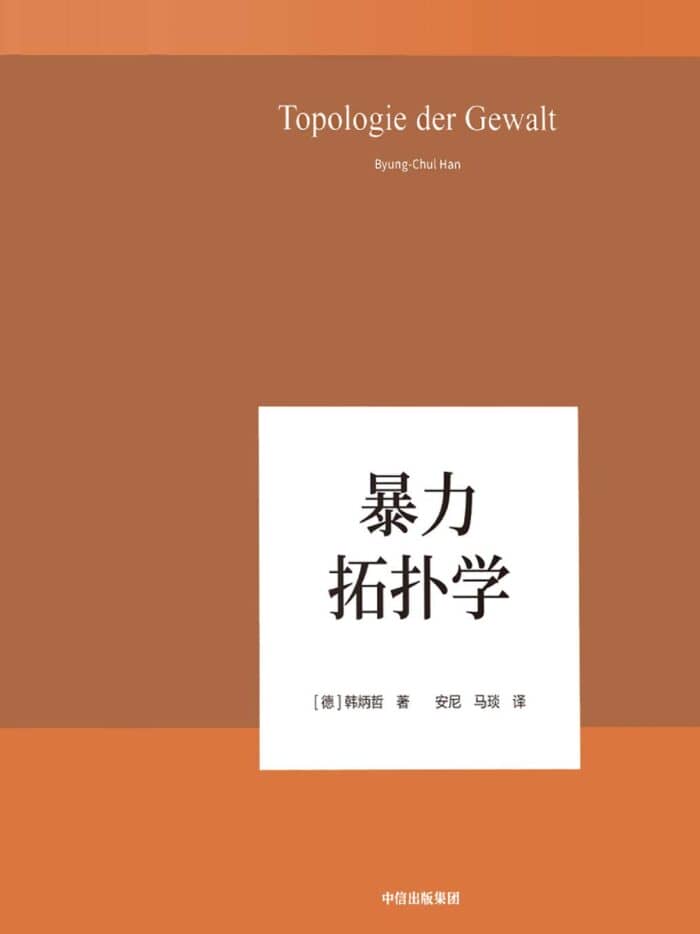作者:
江鹅
一九七五年生,台湾辅仁大学德文系毕业,来自台南,住在台北。人类图分析师兼自由写作者,经营脸书粉丝页“可对人言的二三事”与“Irene人类图解读”。著有散文集《俗女养成记》《俗女日常》。
据《俗女养成记》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打破了华视十三年来的最高收视纪录,在第55届 台湾电视金钟奖上一举斩获“最佳迷你剧集奖”“最佳迷你剧集女配角奖”与“最佳戏剧类节目剪辑奖”三项大奖。获第6届豆瓣电影年
内容简介:
《俗女养成记》是台湾作家江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故事集,以清爽利落的文字写一个台南普通女孩的成长故事:与阿嬷的趣味日常、中药房里跟屁虫的生活、学钢琴、午后一个人的科学实验、爱的教育、女性意识初启蒙,还有孩童的内心小剧场等等。在各种可与不可对人言的人生细碎里,写出了一个女孩如何一点点长大,慢慢窥见并进入成人的世界,检视那些发生在自身的,关于亲情、爱、婚姻、尊卑伦常、人情世故等诸多教养与束缚,一步步变得自知自明,自如自在,真实而舒展。
生命再怎么难免哭泣,没有一刻不盼望着欢喜。大人与小孩,一起守护家的温暖热闹,也一起应付时代的荒谬。二十八篇轻盈舒展又机趣可爱的散文,不仅召回了记忆中的童年时代,也展现了思想与情感的今昔对比,从一个更开阔的视角去理解在这个时代和环境下成长的女性。《俗女养成记》不仅是一个普通女孩的成长史,也是所有在时代的新与旧之间认真生活的当代女性真实写照,不再追随那张优秀又好命的女人蓝图,选择一种更为安乐自在的活法。每一个人的成长既有时代印痕,又有生命自身的逻辑,回首过往是记录成长,也是厘清来路,与这个普通的自己握手言和。
试读:
你可能不认识江鹅,也可能怀疑这个看起来飞禽走兽的笔名没问题吗?……然而江鹅真的会写。
所谓的“会写”意思是,她不管写什么,似乎都自成一派天圆地方星罗棋布的格局,江鹅的文字跟人一样,简洁而颀长,开阔而清洁。写一碗红豆汤,写一丸汉药,写一块垫板,写水银泻地的夏日午后,再小再琐碎,都能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她的警句有时简直是开口就喷一把匕首:“让女人认知现实,这是济世。”“‘乖’分成两种,‘自然乖’和‘用力乖’……‘自然乖’在长辈眼里只能算及格,做人要想拿高分,全靠‘用力乖’。”“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应付时代的荒谬。”然而我们又说好春不在繁枝,文字的好处练得出来,其余令人欢喜赞叹之处却学不来,例如那种胡闹中见真肃的黑色幽默,以及她显然花费许多时间力气,不断与环境拉扯调校出来的平衡感,那平衡表面非常安稳,其实却是时时警醒又危危颤颤的生活姿势,像一枚法相庄严却以荒唐角度悬落在崖边的奇石。
江鹅前半生是在职场练出三头六臂的城市OL,并不以写作为务,可能连业余参与都很少,但在如今这个新的传播环境,这些毫不妨碍她的天分出彩。尽管可能会被大多数读者视为无来历的素人,但我很确定这只野生自来鹅(到底为什么要自称鹅!)并不输正途功名出身有产销履历认证的有机鹅……在这书里她写我们三四十岁人的时代记忆,写家常饮食,写台南,写阿嬷阿公,写六年级女生的妥协而唐突,其实都是写过的事,但经过她的手偏偏就多那一点绵里藏针利落痛痒。如果你对这类写作曾有拿腔拿调自溺自恋自怜的印象,那么就非常宜于读读这本书,可明眼目,清心肠,健精神:这个中药房的小孙女果然得到药家真传。
自序:普通女人
季节对的时候,在超市里面能买到进口酪梨,比台湾的小一点皱一点,味道也浓厚一点,我很喜欢。几年前灵机一动,想到可以把酪梨籽种起来,将来结果就有得吃,不必枯等超市供货,于是我按着网路搜寻来的步骤,充满爱心与期待地为酪梨籽插上竹签泡水,日日换水照看。两个多月过去,嫩枝翠芽地到了该种盆的时候,我又上网查询种植教学,却意外发现一个事实:这样种出来的酪梨树不会结果。
那我岂不是白忙一场?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不会结果,我绝不会花那些工夫,问题是枝干已经长出来了,虽然细弱,却是它勤勤勉勉花了许多时间,从什么也看不见的黑暗里,按着生命的设定,奋力冒出来的。理智叫我趁早丢了那株酪梨苗省事,但情感上却好像看见另一个自己,一条落在普世期盼值之外的生命,霎时间感慨起来,临时换了主意找来土和盆,给了它一条前途未卜的活路。
我们这一批和十大建设差不多时间出生,和台湾经济一起从尘里土里乒乒乓乓长出来的女孩,应该要养成的样子都差不多。要聪明伶俐却听从爸妈和老师说的话,照顾好自己的功课并且主动帮忙家务,待人温文可亲自己却坚毅果敢,从事一份稳当的工作并且经营一个齐备的婚姻,最好玲珑剔透却又福厚德润,懂得追赶新时代的先进也能体贴旧观念的彷徨。大部分的人,像期待每一棵随手种下的酪梨树都能丰收结果似的,期待这些女孩都将理所当然成为优秀又好命的女人,和大家一样。
结果当然是每一个女孩最终都长成不够圆满的女人,没有一个一样。一样的只有我们经常觉得自己作为女人,总有哪里不够成材,对父母,对家庭,对子宫卵巢,对自己,人前或人后,自愿或受迫,总有我们抱歉的对象。这个事实说出来有点荒谬,活在其中不是那么容易察觉,但是一旦认真想起来却再也无法回头。
前年我开始长出白发,不多,就是在整片黑发里面夹杂着几根,刚好让人一看觉得“啊,这人有白头发了”的少少量。一开始我还认认真真地拔,不喜欢那些白色的发丝,忽然从整片黑色里面冒出头来,隐约招摇着没名没分的突兀。拔了几次发现左支右绌,歪着腰对镜翻找大半天,站直以后梳子一拨又滑出来三四根,头发要白不是我可以拦阻的态势,要白就白吧,放弃努力以后反而觉得它们长得慢些。
那张优秀又好命的女人蓝图,我勉力跟着长了大半辈子的,我看也就这样算了,长成了的部分没让我容易多少,长不成的那些显然这辈子就不干我的事。两年前我还常常盼着,有人可以在生活里告诉我“没关系”,不料盼着盼着倒是发现,有什么好讲的本来就没关系。一九七〇年代出生的女孩,长成一个现在随处可见的六年级女性,无论是听着别人的话还是自己摸着路走来,都是货真价实地花了半辈子,才活成如今这样一个和大家一样,既成材又不成材的普通女人。
年过四十开始赞许自己普通得理直气壮,这一点我倒要归到成材的那一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