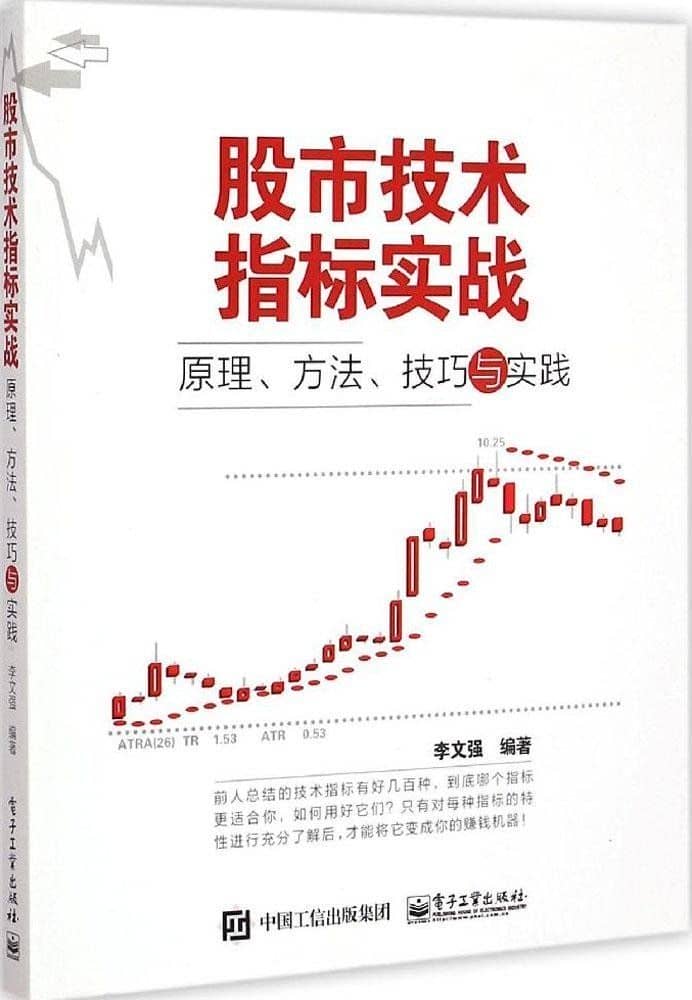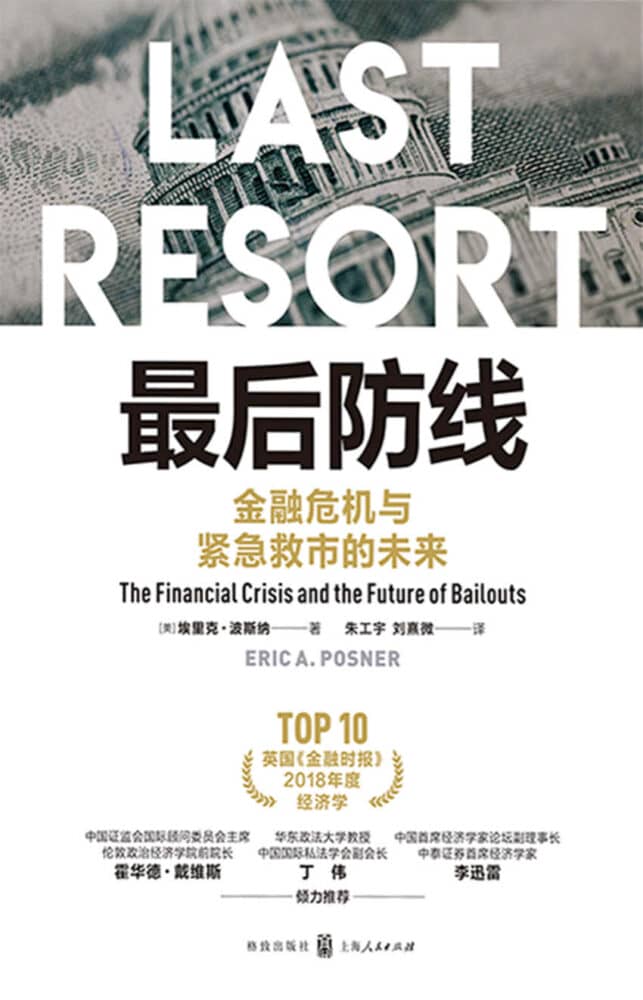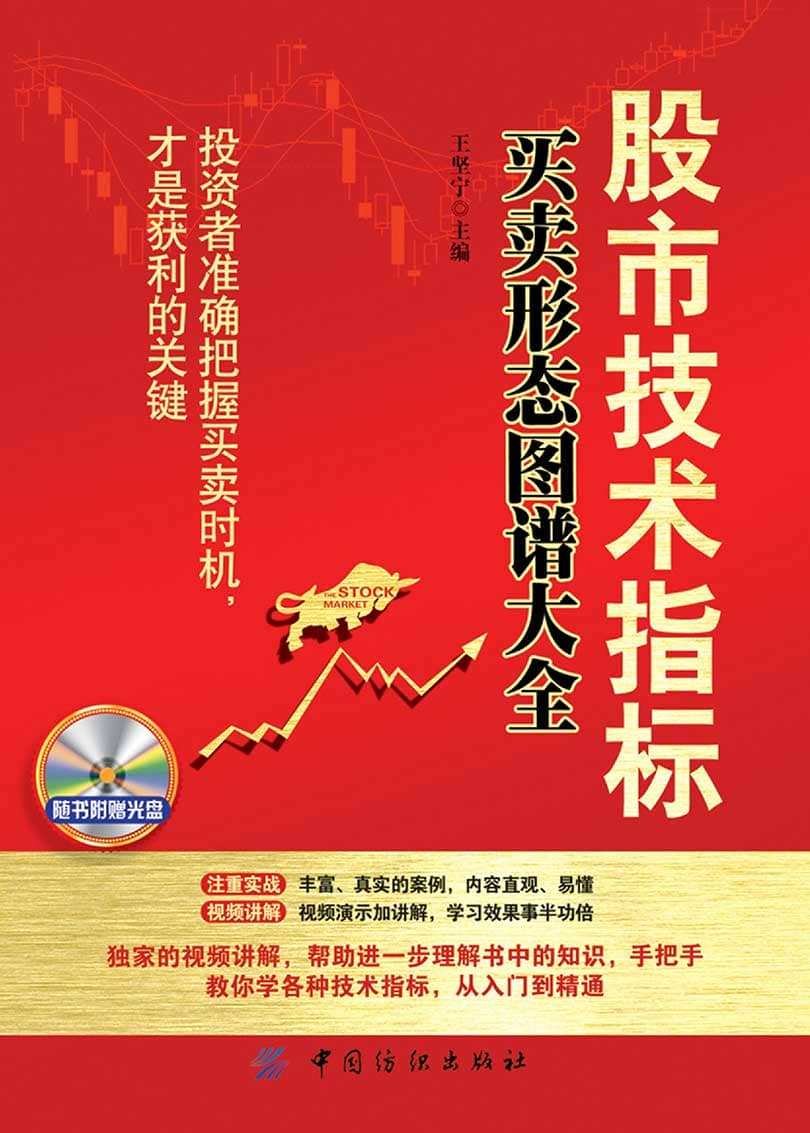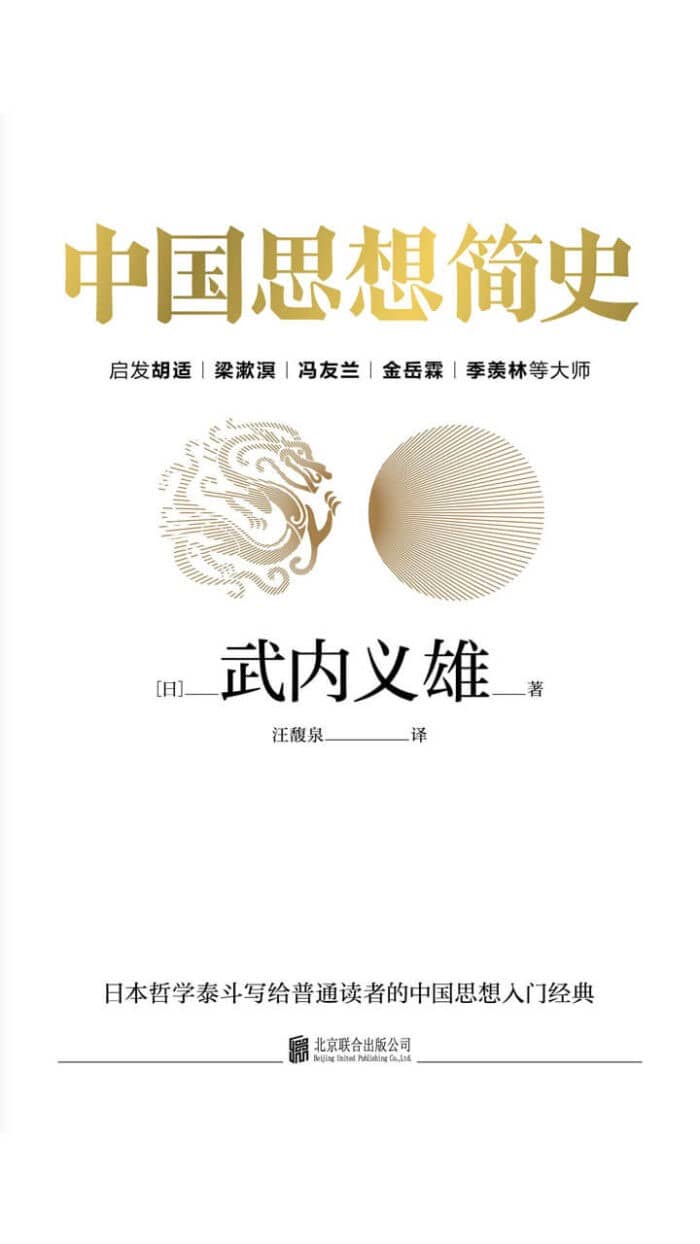内容简介:
《众妙之门》书名源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句:“如果我们将知觉之门洗涤致净,万物便会以其无限的原貌出现在我们眼前。人们若将自己封闭起来,便只能从洞穴的狭窄细缝中窥探事物。” 也与《老子》的“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有着异曲同工之意。
《众妙之门》是赫胥黎记录自己服用一种从美洲仙人掌中提取的麦司卡林后的视幻体验,以及一些神秘经验造成的影响:“我想,我见证了亚当被造出来那个清晨所见的一切──每时每刻都有奇迹,以赤裸裸的方式显现。”是其亲临天堂、地狱般神秘领域的第一手经验记录,开启了现代知觉、灵性、极限探索的先河,深刻影响了西方当代文化。《天堂与地狱》是《众妙之门》的续篇,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艺术经验的感官极限与非常态的心智体验。
作者: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2),英国作家、学者,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
赫胥黎出生于赫赫有名的赫胥黎家族。他本人早年入读伊顿公学,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贝列尔学院。最初志向是当医生,后因眼疾改事文学。家学渊源和个人禀赋使得他在20世纪的欧美学术圈被认为是现代思想的领导者,位列当时杰出的知识分子行列,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赫胥黎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诗歌、哲学著作和游记等,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现代文明各个重要方面。代表作有《美丽新世界》《加沙的盲人》《旋律的配合》《岛》等。他晚年时对艺术、心理学、哲学,尤其是神秘主义颇感兴趣。
【译者简介】
陈苍多(1942— ),台湾澎湖人,台湾师大英语研究所硕士,曾任台湾政治大学英语系教授。师承余光中,译作有《天地一沙鸥》《谈笑书声》等两百余种。还著有散文随笔《烟斗与高跟鞋》等。
试读:
一八八六年,德国药理学家路易斯·莱温首先发表了有关仙人掌的有系统研究,同时他自己的名字也在以后与仙人掌结合在一起。“南美仙人掌” (1) 成为科学之中的新名词。对于原始宗教,以及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而言,“南美仙人掌”自从邈远的时代以来,一直就像一位熟悉的朋友。其实,不仅仅是朋友而已。借用早期到新世界一游的某位西班牙人的话:“他们吃一种根,称之为球顶仙人鞭,敬之如神祇。”
以后,杰出的心理学家,诸如杨施 (2) 、哈夫洛克·霭理士 (3) 以及韦尔·米切尔 (4) ,开始对“球顶仙人鞭”的有效成分“麦司卡林” (5) 进行实验,于是人们就明白为何那些西班牙人对这种东西敬如神祇了。是的,所有这些心理学家,虽然没有像那些西班牙人那样把这种东西当偶像崇拜,但他们全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麦司卡林”是一种很独特的药物。如果适量服用,会比任何药物更强烈地改变意识的特性,但较不会有毒性。
自莱温与哈夫洛克·霭理士以后,对于“麦司卡林”的研究时断时续。药剂师不仅分解了生物碱,并且也学会如何以合成的方式制造生物碱,不再依赖一种沙漠仙人掌的时断时续的稀少收成。精神病医生开始服用“麦司卡林”,希望能以第一手的方式更加了解病人的精神过程。虽然心理学家比较不那么幸运,研究的主题太少,研究的环境太狭窄,但是,他们也观察到这种药物有一些较显著的效果,并加以记录。神经学家与生理学家则发现了这种药物对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至于哲学家方面,至少有一位职业哲学家服用了“麦司卡林”,希望可能了解一些古代的谜,诸如心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以及脑与意识之间的关系。
情况一直到两三年前才有了改变:人们观察到一种也许具有高度意义的新事实。 (6) 事实上,这个事实一直暴露在每个人面前,已有几十年之久,只是并没有人注意到。后来,一位现在在加拿大工作的英国年轻精神病医生,才惊觉于“麦司卡林”和肾上腺素的化学构造非常相似。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麦角酸——取自麦角的一种极为有效的迷幻药——与其他的酸之间有一种结构上的生物化学关系。然后,人们又发现,因肾上腺素分解而产生的肾上腺色素,会造成很多症状,就像“麦司卡林”中毒时所出现的症状。但是,肾上腺色素也许会在人体之中自然产生。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制造出一种化学成分,只要微量的这种化学成分就可以造成意识的重大改变。其中一些改变就像在二十世纪最独特的灾难——精神分裂——之中所出现的改变。“精神分裂”这种精神失常是归因于一种化学方面的失常吗?而化学方面的失常又归因于那种影响肾上腺的心理苦恼吗?这样认定会失之轻率与仓促。我们最多只能说,我们是拥有某种表面上的证据。同时,人们也很有系统地追踪着线索;侦探们——生物化学家、精神病医生、心理医生——都在跟踪着线索。
由于一连串极为幸运的情况,我于一九五三年的春天直接抓住了线索。一位“侦探”有事到加州。尽管“麦司卡林”方面的研究已有七十年之久,但是这位“侦探”所能支配的心理材料却极为不充足,所以他急着要加以补充。我当时在场,很愿意——其实是很渴望——当实验品。于是,在一个明亮的五月早晨,我将十分之四克的“麦司卡林”溶于半杯水中,吞服了下去,然后坐下来等待结果。
我们两个人住在一起,彼此影响,彼此有所反应;但在所有的情况中,我们总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殉道者手牵手走进竞技场;他们各自被钉上十字架。情人拥抱着,拼命地努力要把隔离的狂喜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单一的自我超越,但是并没有用。就本质而言,每种具体化的心灵都注定要在孤独之中受苦与享乐。感觉、感情、洞察力、幻想——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私密的,除了经由象征,并以间接的方式进行之外,都是无法传达的。我们能够结合有关经验的信息,却永远无法结合经验本身。从家庭到国家,每种人类的群体都是由宇宙岛 (7) 所形成的一种团体。
大部分的宇宙岛都在相当程度上彼此相像,足以容许推论性的了解,甚至容许彼此的感情移入。如此,在记得自己的丧失与屈辱时,我们都能够同情那些处于相似情况中的别人,能够设想自己是处于他们的境地中(当然,经常是就一种稍微特殊的意义而言)。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宇宙之间的沟通是不完全的,或者甚至是不存在的。心智就是它自身的所在,而疯狂的人和非常有天赋的人所居住的地方,很不同于平常男人和女人生活的地方,所以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共同的记忆空间,作为了解同类感觉的基础。话语说出来了,却无法启发。符号所指涉的事物和事件,属于彼此排斥的经验领域。
看我们自己就如同别人看我们——这是一种最为有用的资质。几乎同样重要的一种能力是:看别人就如同他们看他们自己。但是,如果别人属于一个不同的物种,住在一个十分不同的宇宙呢?例如,正常的人如何可能知道疯狂的真正感觉呢?又例如,我们并不可能再诞生,成为一个看见幻象的人、一个灵媒 (8) ,或一位音乐天才,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去造访那种对布莱克 (9) 、斯威登堡 (10)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11) 而言是原乡的世界呢?一个极端瘦长型和头脑型的人,如何能够设想自己是一个极端矮胖型和消化型的人呢?或者,除了在某些限定的领域之内,又如何可能跟一个极端强壮型和肌肉型的人有同样的感觉呢?对于纯粹的行为主义者而言,我想这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些人在理论上相信那些他们实际上知道是真实的事情——即有一种内在的世界可以经验,就像有一种外在世界可以经验一样。对这种人而言,这些问题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存有”而更加严重,有的完全不能解决,有的只能在异常的情况下解决,而解决的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如此,很确定的是,我将永远不会知道:成为约翰·福斯塔夫 (12) 爵士或成为乔·路易斯 (13) 是什么感觉。另一方面而言,我总是认为,借由催眠或自我催眠,也就是借着有系统的静坐沉思默想或服用适当的药物,我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意识模式的,以至于能够从内心知道看见幻象的人、灵媒甚至神秘主义者在说些什么。
我读到了有关服用“麦司卡林”的经验方面的数据,所以事先就预期:服了这种药物后,我至少会有几小时之久进入布莱克和AE (14) 所描述的那种内在世界。但是,我所期望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本来期望:闭着眼睛躺着,会看到一些幻象,包括多彩的几何图形,生动的建筑物,镶有很多宝石,非常可爱,还有一些风景,有着壮丽雄伟的形体,再有就是一些象征性的戏剧,永远在“终极启示”的边缘颤动着。但是,很显然的,我并没有考虑到我心智的独特性,也没有考虑到我的性情、教育与习惯等事实。
我不是很高明的视觉型的人,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是如此。字语,甚至诗人丰富的字语,都不会在我心中激起图像。在似睡未睡之际,都不会有似醒非醒的幻象在我脑中出现。当我回想什么事情时,记忆并不会像生动的事件或东西那样呈现出来。借着意志的努力,我能够激起一种不很生动的意象,包括昨日下午所发生的事情、兰加诺人在毁桥之前如何检视一番,以及“湾水路”的情况:唯一看得到的巴士是绿色的,体积很小,由老迈的马匹拉着,一小时走三里半的路。但是,这种意象几乎没有实体,完全没有自身的自发生命。它们与那些被知觉到的真实东西的关系,就像荷马笔下的幽魂与血肉之躯的人的关系——这些血肉之躯的人是到地狱去探访这些幽魂。只有当我体温很高时,我的心智意象才会呈现独立的生命。在那些拥有强烈想象能力的人看来,我的内在世界想必透露出很奇异的单调、有限又无趣的意味。我就是期望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一个贫乏的世界,但却是我自己的世界——转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