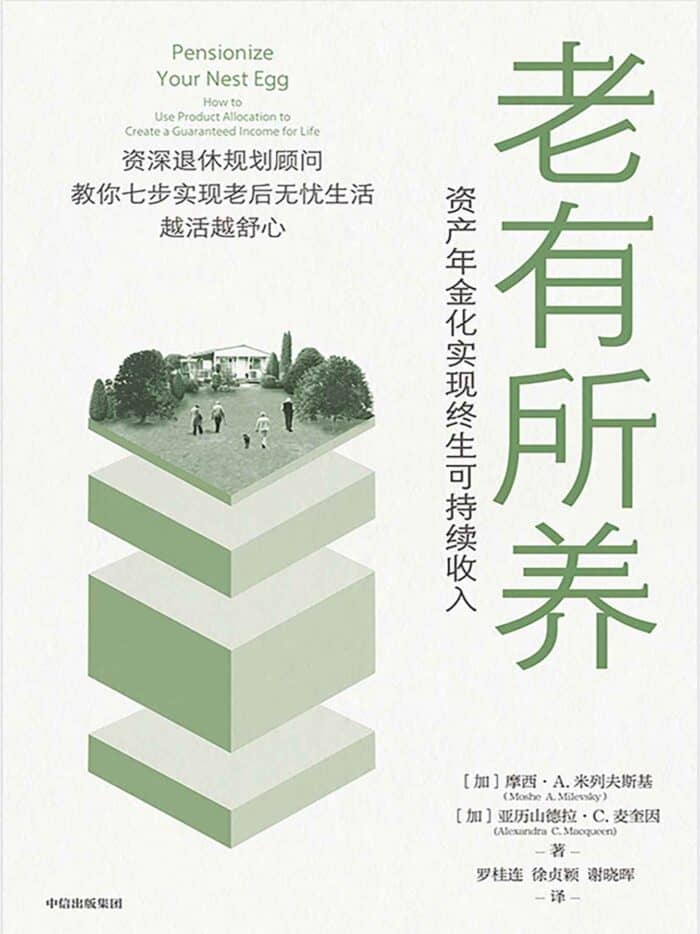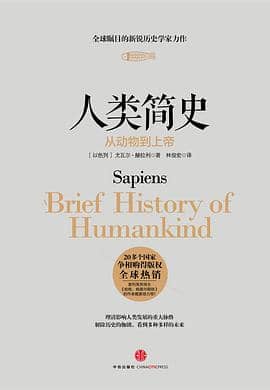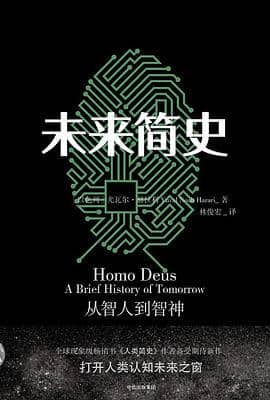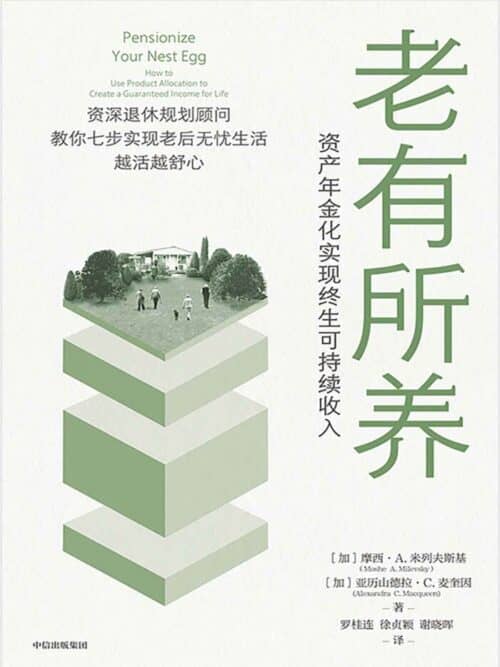作者:
凯瑟琳·布(KatherineBoo)
美国知名记者、作家,曾在《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担任编辑和调查记者,2003年成为《纽约客》专职作者。
从业三十年来,始终关注在社会边缘挣扎求生的弱势群体,是美国报道当代社会问题蕞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曾获普利策奖、麦克阿瑟天才奖、美国国家杂志奖等重要奖项。其报道以调查广泛、行文优美、同理心丰沛见长,并促发了一系列改善举措。
《美好时代的背后》为其代表作,出版之后受到众多媒体好评,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笔会奖、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奖等奖项。
简介:
在这里,人像垃圾一样被严格分类,正义像垃圾一样彼此交易,生命更像垃圾一样不值一文。
在这里,所谓体面的生活,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源于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
在孟买国际机场旁写着“永远美丽”的广告牌背后,贫民窟安纳瓦迪的居民不时梦想着更美好的生活。
垃圾回收者阿卜杜勒梦想有个不嫌弃他身上味道的老婆,两人一起到除安纳瓦迪以外的任何地方安家;他的母亲泽鲁妮萨则梦想在安纳瓦迪有个更干净的家,要有一扇可以排放油烟的小窗户,要铺着像广告里那样美丽的瓷砖;厕所清洁工拉贾·坎伯梦想能有钱换一副心瓣膜,好保住来之不易的工作,继续供养全家;热衷于调解邻里纠纷、从中捞取好处的阿莎梦想成为安纳瓦迪蕞有权有势的人物,让自己的女儿成为贫民窟头一个女大学生。
在都市的繁华表象之下,他们就像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努力地为梦想奔走。然而,他们掌握不了任何东西,一个普通日子里的微小变动便足以让他们的生活天崩地裂。
我告诉真主安拉,我非常非常爱他。不过,我也告诉他,由于世界的运作方式,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阿卜杜勒
目录:
序幕玫瑰之间
部分底层居民
安纳瓦迪
阿莎
苏尼尔
曼朱
第二部分自焚这桩买卖
幽灵屋
被称为窗户的洞
崩溃
师父
第三部分几许荒凉
底层的逆袭
被出卖的鹦鹉
一顿好眠
第四部分兴起与坠落
九个夜晚的舞蹈
闪闪发亮的东西
审判
冰的裁决
黑白之间
学校、医院、板球场
后记
致谢
试读:
让我们暂时定格在鱼唇警察和阿卜杜勒在警察局相遇的这一刻。接着倒带,看阿卜杜勒从警察局和机场倒着跑出来,朝着家跑去。看身穿粉红花罩衫的残疾女人被火焰吞噬,火焰逐渐化为乌有,只留下地上的火柴盒。看几分钟之前的法蒂玛,随着一首嘶哑的情歌拄着拐杖跳舞,她秀气的五官完好无损。继续倒带,回到七个月前,停在二〇〇八年一月一个平常的日子。自一个小贫民窟出现在拥有全球三分之一贫穷人口的国家中最大的城市以来,这几乎是充满希望的一季。如今发展建设和金钱流动,已经让这个国家头脑发热。
黎明在狂风中到来,这在一月并不罕见,这是风筝绊在树上和伤风感冒的月份。阿卜杜勒家由于地板空间有限,不够让全部的家庭成员躺下来,阿卜杜勒因此睡在沙砾遍布的广场,这里多年来一直充当他的床。他的母亲小心翼翼地跨过阿卜杜勒的弟弟们,然后弯下身来,伏在他的耳边。“醒醒,你这傻瓜!”她充满活力地说,“你以为你的工作是做梦吗?”
出于迷信,泽鲁妮萨注意到,家里赚钱最多的日子,有时就在她辱骂过大儿子之后。一月的收入,对他们家逃离安纳瓦迪的最新计划至关重要,因此她决定把咒骂当成例行公事。
阿卜杜勒几乎没有怨言地起床,因为他母亲只能忍受她自己的牢骚。更何况,这段缓缓行进的时光,是他最不憎恨安纳瓦迪的时刻。黯淡的阳光在污水湖上投下闪闪银光。鹦鹉在湖的另一头筑巢,在喷气式客机的噪音中仍可听见它们的叫声。在有些由宽胶带和绳子粘捆在一起的棚屋外头,他的邻居们正用湿破布仔细擦洗身体。穿制服、系领带的小学生们,正从公共水龙头处拖运一桶桶水。一支懒洋洋的队伍从公厕的橘色水泥砖延伸出来。就连山羊也睡眼惺忪。在这亲密温馨的时刻过后,他们随即展开对微小市场利益的积极追求。
建筑工人陆续前往一个拥挤的路口,这是监工人员挑选临时工的地方。年轻女孩们开始把金盏花穿成花环,好在交通繁忙的机场大道上兜售。年长的妇女把布块缝在粉红色和蓝色相间的棉被上,一家公司会给她们论件计酬。在一家闷热的小型塑模工厂,袒露胸膛的男人扳动机件,把彩色珠子变成挂在后视镜上的装饰品—笑盈盈的鸭子和粉红色的猫,脖子上戴着珠宝,他们想不出谁会在哪个地方购买这些东西。阿卜杜勒蹲伏在广场上,开始整理两个礼拜以来购买的垃圾,脏兮兮的衬衫贴在他一节节的脊椎骨上。
对待左邻右舍,他普遍采用的态度是:“我越是了解你,就越讨厌你,你也会越讨厌我。因此,就让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吧。”然而,即使像这天早晨一样自己埋头干活儿,他还是能够想象,安纳瓦迪的居民们都在他身旁一起努力。
安纳瓦迪坐落于距萨哈尔机场大道近两百米处,新旧印度在这段路上彼此冲撞,延迟了新印度的发展。开着SUV的司机朝着从贫民窟某家鸡店骑自行车出来的一排送货男孩猛按喇叭,他们每个人载送三百颗鸡蛋。在孟买众多的贫民窟当中,安纳瓦迪本身并无特别之处。每间屋子都歪歪斜斜,因此不太歪斜的屋子看起来就像正的,污水和疾病看起来就像生活的一部分。
这座贫民窟在一九九一年由一群民工建成,卡车把他们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运来维修国际机场跑道。工作完成后,他们决定在机场附近诱人的建设前景中待下来。在一个几无闲置空地的地区,国际航站楼对街一小片潮湿的、群蛇遍布的灌木地,似乎是不错的居住之处。
其他穷人认为这块地太过潮湿,不宜居住,泰米尔人却着手干活儿,砍倒窝藏群蛇的灌木,挖出较干燥地区的土壤,填入泥泞之中。一个月后,他们的竹竿插在地上时,终于不再扑通倒下。他们把空水泥包装袋挂在竹竿上当作掩护,一个聚居区便形成了。附近贫民窟的居民给它取名安纳瓦迪—意为“安纳之地”,泰米尔人尊称老兄为“安纳”。事实上,对泰米尔移民的各种贬称,流传得更为广泛。然而,其他穷人目睹了泰米尔人用血汗将沼泽打造成结实土地的过程,如此的劳苦赢得了某种敬重。
十七年后,在这一贫民窟里,根据印度官方基准,几乎没有人可以被算作穷人。相反,安纳瓦迪居民属于一九九一年以来摆脱贫穷的约一千万印度人口之列。当时,约莫就在这个小贫民窟建成之时,中央政府接受了经济改革,安纳瓦迪居民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现代史中最激励人心的成功故事之一,一个仍在继续发展的故事。
的确,贫民窟的三千居民中,仅六人有固定工作。(其他人,就像百分之八十五的印度劳工,都属于非正规、无组织的经济体系。)的确,有些居民必须诱捕老鼠和青蛙,油炸后当晚餐吃;有些居民甚至吃污水湖畔的灌草丛。这些可怜人为他们的邻居们做出难以计算的贡献—让那些不炸老鼠、不吃杂草的贫民窟居民感受到他们自己有多么上进。
机场和酒店的垃圾在冬季喷涌而出,这是观光旅游、商务旅行和上流社会婚礼的高峰期。二〇〇八年的大量排放,则反映出空前高涨的股市行情。对阿卜杜勒来说更好的是,在夏季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的建设使全球废金属价格飙涨。这对一个孟买垃圾交易商来说是件开心的事,虽然这并不是路人对阿卜杜勒的称呼。有人就直呼他垃圾。
今天早晨,阿卜杜勒一边从他的破烂堆中挑拣平头钉和螺丝钉,一边努力注意安纳瓦迪的山羊,这些羊喜欢瓶罐残留物和标签底下的糨糊味。阿卜杜勒通常不在乎这些羊在旁边嗅来嗅去,可是近来它们拉出的都是液态粪便,相当恼人。
这些山羊归一个家里经营妓院的穆斯林男人所有,他认为他手下的妓女都在装病。为了扩大经济来源,他饲养山羊,以便在斋月结束时的宰牲节庆典上出售。然而,这些羊和那些姑娘们一样令人头痛。他拥有的二十二只羊,已经死了十二只,幸存的几只则有肠道疾病。这个妓院老板将此怪罪于经营当地酿酒店的泰米尔人施展的巫术,还有人怀疑是山羊的饮用水源有问题,也就是那片污水湖。
深夜,建设现代化机场的承包商会往湖中倾倒东西。安纳瓦迪居民也把东西倒在那里;最近一次,是十二只山羊的腐烂尸体。那一池水,让睡在浅滩的猪狗从水里爬出来时,肚子染成了蓝色。不过,除了疟蚊,还有一些生物在湖中幸存下来。随着清晨将近,一个渔夫涉水而过,一只手推开烟盒和蓝色塑料袋,另一只手用网子在水面泛起涟漪。他将把捕获物拿到默罗尔市场磨成鱼油,这种保健产品如今在西方极受重视,因此需求骤增。
阿卜杜勒起身甩动痉挛的小腿时,吃惊地发觉天空像机翼一样呈现褐色,阳光透过污染的雾气,显示午后的来临。整理垃圾时,他总习惯性地忘记时间。他的小妹妹们正在和“独腿婆子”的女儿们坐在一张轮椅上嬉戏,这个轮椅是用一张破塑料躺椅镶上生锈的自行车轮子组合而成的。已经放学回家的九年级学生米尔基摊开四肢靠在家门口,摆在腿上的数学课本连一眼都没看。
米尔基正不耐烦地等着他的好友拉胡尔,这个住在仅隔几户人家远的印度教男孩已成为安纳瓦迪的风云人物。这个月,拉胡尔做了米尔基梦寐以求的事:打破贫民窟世界和有钱人世界之间的隔阂。
拉胡尔的母亲阿莎是幼儿园老师,和当地的政客与警察有微妙的关系。她设法帮儿子弄到洲际酒店几个晚上的临时工作,就在污水湖对岸。拉胡尔这样一个长着大饼脸和龅牙的九年级学生,因此目睹了上流城市的富裕。
终于,拉胡尔走过来了,穿着一套由这个好运气带来的奖金购买的衣服:休闲低腰短裤,闪闪发亮、回收重量可观的椭圆扣环皮带,拉到眼睛的黑色绒线帽。拉胡尔称之为“嘻哈风”。前一天是“圣雄”甘地遇刺六十周年,印度精英分子过去认为,在这个国定假日搞豪华派对颇为庸俗。然而,当时拉胡尔却在洲际酒店的一场疯狂盛宴中干活儿,他知道米尔基非常想知道当时的每一个细节。
“米尔基,我真的没骗你,”拉胡尔咧嘴笑着说,“在我负责的大厅,有五百个穿得很少的女人,好像她们出门前忘了把下半身穿上!”
“啊,那时候我在哪里啊?”米尔基说,“快跟我说,有没有名人?”
“每个人都是名人!那是一场宝莱坞派对,有几个明星在绳子后面的贵宾区,不过,约翰·亚伯拉罕就在我附近,穿着黑色厚大衣在我面前抽烟。他老婆碧帕莎据说也在,不过我不确定那真的是她,还是只是某个美女明星,因为万一经理看见你盯着宾客看,他就会把你开除,没收你全部的薪水—他们在派对开始前跟我们说了二十次,好像把我们当白痴!你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餐桌和地毯上,当你看见一个脏盘子或一条脏餐巾,必须赶紧拿走扔进垃圾箱里。噢,那间大厅真漂亮。我们先铺上厚厚的白地毯,厚到你踩上去立刻就会陷下去。然后他们点起白色蜡烛,让房间变暗,像迪斯科舞厅一样;厨师在一张桌子上摆了两只用加味冰块雕成的大海豚,其中一只海豚的眼睛是樱桃……”
“笨蛋,别管海豚,跟我说说那些女人,”米尔基抗议道,“她们穿成那样,就是要让别人看的吧?”
“说真的,你不能看啦,就连待在有钱人的厕所都不行,你会被保安人员撵出去。不过,工作人员的厕所倒是很好,有印度式或美式供你选择。”爱国的拉胡尔选择在地上有排水孔的印度式厕所小便。
其他男孩也到侯赛因家门外,和拉胡尔会合。安纳瓦迪居民们喜欢谈论酒店和酒店里可能发生的奢靡活动。一个被药物搞得昏头昏脑的拾荒者曾指着酒店说:“我知道你们千方百计想谋害我,你这狗娘养的凯悦!”不过,拉胡尔的叙述别有价值,因为他不说谎话,或至少二十句话当中只有不超过一句谎话;加上他性格开朗,因而他的特权并未引起其他男孩的痛恨。
拉胡尔大方地坦承,与洲际酒店的正职人员相比,他不过是无名之辈。许多服务生都是大学学历、身材高大、浅肤色,拥有闪闪发亮的手机,梳头发时,甚至能用来当镜子。有些服务生嘲笑拉胡尔涂成蓝色的、长长的拇指指甲,然而在安纳瓦迪,这可是男子气概的象征。他剪了指甲后,他们又取笑他的说话方式。安纳瓦迪对有钱人的敬语“沙巴”(sa’ab),在城里的富人区不是妥当的称呼。他向朋友们报告:“那里的服务生说,这让你听起来很不入流,像流氓一样。‘阁下’(sir)才是正确的说法。”
“阁—下。”有人说道,把sir的r发成长长的卷舌音,随后,大家都开始念这个词,一同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