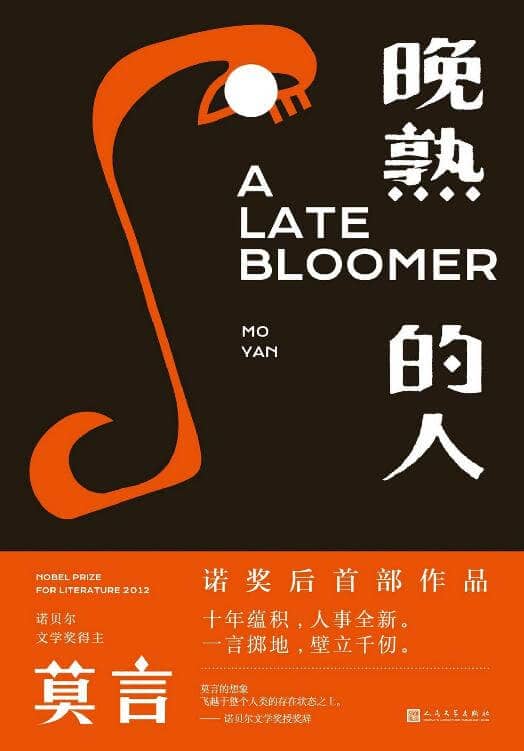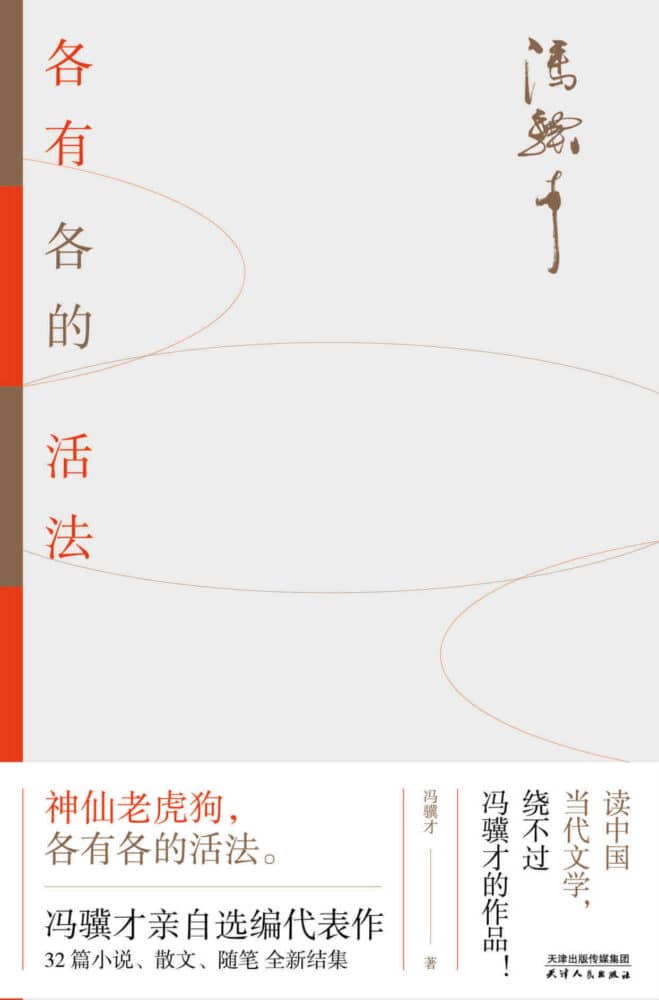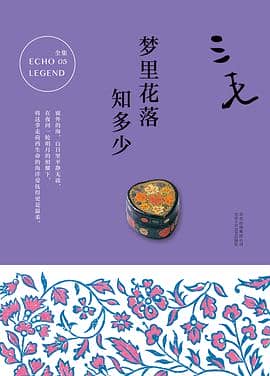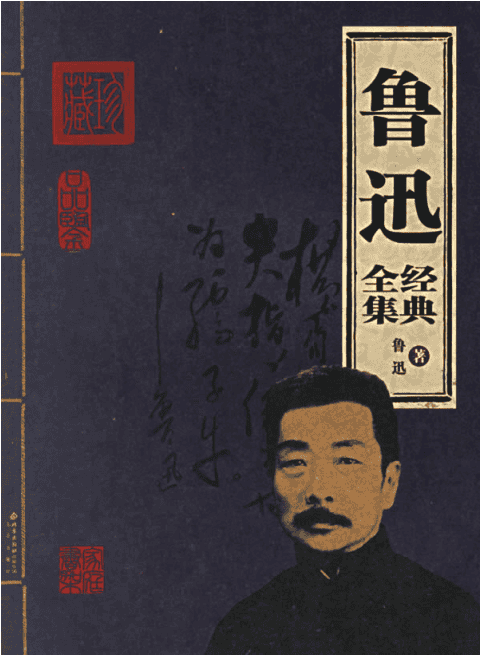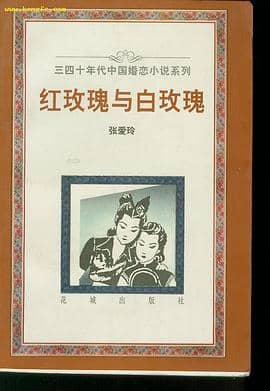作者:
余华,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第七天》等。其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2014年)、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文学奖(2018年)、意大利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纳文学奖(2018年)等。
简介:
关于一个人和他一生的寻找
以及一群人和一个汹涌的年代
………………………………………………………………
“文城在哪里?”
“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
◆在溪镇人ZUI初的印象里,林祥福是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哪怕后来成了万亩荡和木器社的主人,他身上的谦卑和沉默依旧没有变。他的过去和一座谜一样的城联系在了一起,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找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他原本不属于这里,他的家乡在遥远的北方。为了一个承诺他将自己连根拔起,漂泊至此。往后的日子,他见识过温暖赤诚的心,也见识过冰冷无情的血。ZUI终他徒劳无获,但许多人的牵挂和眼泪都留在了他身上。
目录:
《候场》无目录
试读:
在溪镇有一个人他的财产在万亩荡。那是一千多亩肥沃的田地河的支流犹如蕃茂的树根爬满了他的土地稻谷和麦子、玉米和番薯、棉花和油菜花、芦苇和竹子还有青草和树木在他的土地上日出和日落似的此起彼伏一年四季从不间断三百六十五天都在欣欣向荣。他开设的木器社遐迩闻名生产的木器林林总总床桌椅凳衣橱箱匣条案木盆马桶遍布方圆百里人家还有迎亲的花轿和出殡的棺材在唢呐队和坐班戏的吹奏鼓乐里跃然而出。
溪镇通往沈店的陆路上和水路上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叫林祥福的人他们都说他是一个大富户。可是有关他的身世来历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外乡口音里有着浓重的北方腔调这是他身世的唯一线索人们由此断定他是由北向南来到溪镇。很多人认为他是十七年前的那场雪冻时来到的当时他怀抱不满周岁的女儿经常在雪中出现挨家挨户乞讨奶水。他的样子很像是一头笨拙的白熊在冰天雪地里不知所措。
那时候的溪镇那些哺乳中的女人几乎都见过林祥福这些当时还年轻的女人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总是在自己的孩子啼哭之时他来敲门了。她们还记得他当初敲门的情景仿佛他是在用指甲敲门轻微响了一声后就会停顿片刻然后才是轻微的另一声。她们还能够清晰回忆起这个神态疲惫的男人是如何走进门来的她们说他的右手总是伸在前面在张开的手掌上放着一文铜钱。他的一双欲哭无泪的眼睛令人难忘他总是声音沙哑地说
“可怜可怜我的女儿给她几口奶水。”
他的嘴唇因为干裂像是翻起的土豆皮而他伸出的手冻裂以后布满了一条一条暗红的伤痕。他站在他们屋中的时候一动不动木讷的表情仿佛他远离人间。如果有人递过去一碗热水他似乎才回到人间感激的神色从他眼中流露出来。当有人询问他来自何方时他立刻变得神态迟疑嘴里轻轻说出“沈店”这两个字。那是溪镇以北六十里路的另一个城镇那里是水陆交通枢纽那里的繁华胜过溪镇。
他们很难相信他的话他的口音让他们觉得他来自更为遥远的北方。他不愿意吐露自己从何而来也不愿意说出自己的身世。与男人们不同溪镇的女人关心的是婴儿的母亲当她们询问起孩子的母亲时他的脸上便会出现茫然的神情就像是雪冻时的溪镇景色他的嘴唇合到一起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仿佛她们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
这就是林祥福留给他们的最初印象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
有一人知道他不是在那场雪冻时来到的这个人确信林祥福是在更早之前的龙卷风后出现在溪镇的。这个人名叫陈永良那时候他在溪镇的西山金矿上当工头他记得龙卷风过去后的那个早晨在凄凉的街道上走来这个外乡人当时陈永良正朝着西山的方向走去他要去看看龙卷风过后金矿的损坏情况。他是从自己失去屋顶的家中走出来的然后他看到整个溪镇没有屋顶了可能是街道的狭窄和房屋的密集溪镇的树木部分得以幸存下来饱受摧残之后它们东倒西歪可是树木都失去了树叶树叶在龙卷风里追随溪镇的瓦片飞走了溪镇被剃度了似的成为一个秃顶的城镇。
林祥福就是在这时候走进溪镇的他迎着日出的光芒走来双眼眯缝怀抱一个婴儿与陈永良迎面而过。当时的林祥福给陈永良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脸上没有那种灾难之后的沮丧表情反而洋溢着欣慰之色。当陈永良走近了他站住脚用浓重的北方口音问
“这里是文城吗”
溪镇通往沈店的陆路上和水路上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叫林祥福的人他们都说他是一个大富户。可是有关他的身世来历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外乡口音里有着浓重的北方腔调这是他身世的唯一线索人们由此断定他是由北向南来到溪镇。很多人认为他是十七年前的那场雪冻时来到的当时他怀抱不满周岁的女儿经常在雪中出现挨家挨户乞讨奶水。他的样子很像是一头笨拙的白熊在冰天雪地里不知所措。
那时候的溪镇那些哺乳中的女人几乎都见过林祥福这些当时还年轻的女人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总是在自己的孩子啼哭之时他来敲门了。她们还记得他当初敲门的情景仿佛他是在用指甲敲门轻微响了一声后就会停顿片刻然后才是轻微的另一声。她们还能够清晰回忆起这个神态疲惫的男人是如何走进门来的她们说他的右手总是伸在前面在张开的手掌上放着一文铜钱。他的一双欲哭无泪的眼睛令人难忘他总是声音沙哑地说
“可怜可怜我的女儿给她几口奶水。”
他的嘴唇因为干裂像是翻起的土豆皮而他伸出的手冻裂以后布满了一条一条暗红的伤痕。他站在他们屋中的时候一动不动木讷的表情仿佛他远离人间。如果有人递过去一碗热水他似乎才回到人间感激的神色从他眼中流露出来。当有人询问他来自何方时他立刻变得神态迟疑嘴里轻轻说出“沈店”这两个字。那是溪镇以北六十里路的另一个城镇那里是水陆交通枢纽那里的繁华胜过溪镇。
他们很难相信他的话他的口音让他们觉得他来自更为遥远的北方。他不愿意吐露自己从何而来也不愿意说出自己的身世。与男人们不同溪镇的女人关心的是婴儿的母亲当她们询问起孩子的母亲时他的脸上便会出现茫然的神情就像是雪冻时的溪镇景色他的嘴唇合到一起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仿佛她们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
这就是林祥福留给他们的最初印象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
有一人知道他不是在那场雪冻时来到的这个人确信林祥福是在更早之前的龙卷风后出现在溪镇的。这个人名叫陈永良那时候他在溪镇的西山金矿上当工头他记得龙卷风过去后的那个早晨在凄凉的街道上走来这个外乡人当时陈永良正朝着西山的方向走去他要去看看龙卷风过后金矿的损坏情况。他是从自己失去屋顶的家中走出来的然后他看到整个溪镇没有屋顶了可能是街道的狭窄和房屋的密集溪镇的树木部分得以幸存下来饱受摧残之后它们东倒西歪可是树木都失去了树叶树叶在龙卷风里追随溪镇的瓦片飞走了溪镇被剃度了似的成为一个秃顶的城镇。
林祥福就是在这时候走进溪镇的他迎着日出的光芒走来双眼眯缝怀抱一个婴儿与陈永良迎面而过。当时的林祥福给陈永良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脸上没有那种灾难之后的沮丧表情反而洋溢着欣慰之色。当陈永良走近了他站住脚用浓重的北方口音问
“这里是文城吗”